7月31日,《和平北京朝陽》在微網誌上釋出通知稱,吳義凡因涉嫌強奸被朝陽市警察局依法刑事拘留。正在進一步調查案件。據報道,吳儀凡此前曾多次誘騙女性發生性關系,包括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系。
有消息稱,各大社交平台的網友們都仿佛新年籠罩着大觀。這一事件的發酵過程也向我們表明,面對各種性别霸權言論和嚴峻形勢,女性正變得越來越有發言權,願意戰鬥。
事實上,這種鬥争也發生在學術界。長期以來,女性一直被貼上不擅長科學研究、更擅長文科、不擅長科學、記憶力更強、但不擅長邏輯思維的标簽......然而,持這種觀點的人并沒有進一步思考,是否正是因為這種先入為主的刻闆印象和大衆觀念,女性在科研領域面臨更多的限制,更大的阻力?
"從1901年到2016年,有911人獲得諾貝爾獎,其中隻有48人是女性,其中16人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14人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科學記者安吉拉·賽尼(Angela Sayni)在她的書《科學為女性做錯了什麼》(What Science Have Wrong For Women)中說。
"皇家學會于1660年在倫敦成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學機構之一,但直到1945年才選出正式的女性會員。Sayni繼續說道。
作為回應,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科學史教授隆達·希賓格(Ronda Schibinger)打趣道:"近三百年來,皇家學會中唯一永恒的女性存在是儲存在社會解剖學儲藏室中的女性骨骼。"
從任何角度來看,在科學發展史上,女性即使不是完全缺席,至少也不是唯一敢于發聲的人。對于這種現象,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這是由于男女之間的天賦差異,或者是職業的差異:以理性、客觀、進步為特征的科學事業無疑屬于男性,而"情感、主觀、情感"的女性更适合家庭、教育或服務職業。
另一方面,在男性科學研究領域(例如,皇家學會一次),研究人員隻能看到并且隻能承認男性的研究成果,而女性以另一種形式取得的成就和貢獻被選擇性地忽視并排除在所謂的"科學"之外。
從18世紀到19世紀,英國植物學和人體工程學的發展足以說明這個問題。女性科學愛好者被限制在其他領域,隻留下植物學去探索;在《花神的女兒》一書中,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阿特金森學院婦女研究中心聯合創始人安·席德爾(Ann Schiddle)使用翔實的證據來挽救女性在促進植物學和傳播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并說明所謂的"科學"對女性的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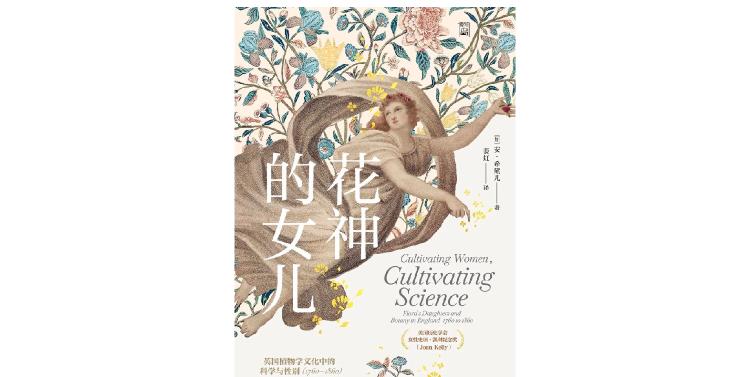
《花神的女兒》,作者:Ann Hildelle,翻譯:江紅,版本:Rolling Studios|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年5月.
"花神的女兒":
植物學是好妻子和好母親的點綴
在歐洲啟蒙運動期間,"科學"成為流行休閑文化的一部分,如時尚,國際象棋和茶點。而女性,就像時尚、象棋、茶點的消費者一樣,也接受過成為科學知識消費者的訓練,許多書籍和雜志都緻力于"美女"來普及當時的科學知識。
科學倡導者向女性推薦天文學,實體學,數學,化學和自然科學作為她們的道德教育和體育活動。她們相信,科學可以治愈她們的輕浮,讓她們遠離危險的餐桌,學習科學的女性會更健談,更成功。
在衆多科學中,女性學習的最佳場所無疑是植物學。
一些作家在美學上認為,植物學符合女性的美麗,優雅或嬌小的氣質,紳士雜志的一位記者宣稱"照顧外來植物不僅僅是女性更特殊的職責......女人柔韌、纖細的玉手可以比男人笨拙的手做得更好......這種精細的工作與紳士的關懷程度是很難實作的";
其他人則從教育的角度認為,植物學是實作虔誠和健康的方法,也是遠離膚淺活動的一種方式,使女性更适合"在田野,樹林和父親的花園裡學習......這也更有利于他們的體育鍛煉";
其他人則将植物學比作探索昆蟲和動物,認為植物學沒有殘酷的殺戮和解剖學......
這些研究植物學的女性被安·希爾代爾稱為"花神的女兒"。
倫勃朗于1634年創作了這幅油畫,其中花神的形象被打扮成他心愛的妻子。
花神弗洛拉是自然,生育和春天的象征,無論是在古羅馬文學還是在宗教神話中。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稱她為"花之母",并稱贊她的美麗,性和生殖能力。Flora在他的作品中代表了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主流觀念:女人與自然和身體有關,而男人與文化和精神有關。
同樣,18世紀和19世紀英國女性生活的社會環境也将她們與物質自然,生殖和母性以及自然與女性氣質,謙遜和純真的品質聯系起來,這為女性參與各種植物活動鋪平了道路。
在父母,老師和社會評論員的鼓勵下,Flora的英國女兒積極參與植物學并積極發展自己的興趣。他們閱讀植物學書籍,參加相關的公開講座,與博物學家交流,收集本地蕨類植物,苔藓和海洋植物,繪制植物繪畫,制作标本集進行深入研究,并了解顯微鏡的使用。當然,一旦有更重要的家務等着他們完成,他們必須立即把植物放在手裡。
以夏洛特女王的名字命名,Strelitzia reginae。
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王後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她熱愛花卉和園藝,接受過專業的植物學指導,共同贊助了邱園(皇家花園,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着名的植物園之一),擁有一個獨特的标本博物館,以及林奈學會(為紀念植物學家林奈而成立的協會,稍後将詳細介紹)的主席應邀幫助夏洛特女王管理标本并指導女王和公主的植物學。甚至還有一個以夏洛特女王命名的淺灘,一種剛剛被引入英國的鶴,"向今天英國女王的植物學激情和知識緻敬"。"
瑞典博物學家卡爾·林奈的肖像。
就連法國思想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為女性寫了一本名為《植物學通訊》(Botany Communication)的書。在書中,他寫了八封信,訓示一位年輕的母親學習植物學,這樣她就可以教她的小女兒。這些信件對英國植物學文化尤為重要。出版商将其翻譯成英文,使其"對美麗的英國女性和未受過教育的男性來說可讀"。"
但在當時的英國圖書市場上,除了盧梭或一些著名的男性植物學之外,更多與植物學相關的書籍或雜志都是由女性作家撰寫的。他們特别擅長科普或入門書寫作,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科普模型,在家庭氛圍中呈現植物學,母親和孩子之間的對話,或者以姐妹般的信仰講述植物學。植物學寫作已成為一些沒有結婚,獨立生活或與丈夫離婚并不得不撫養孩子作為成年人的女性的重要而穩定的經濟來源。
在18世紀,英國公開寫作的女性人數達到了曆史最高水準。據估計,僅在19世紀90年代,就有三四百名女作家出版了宗教書籍,辯論文章,小說,兒童文學,歌劇和科普書籍。盡管他們看似豐富的主題,但他們的寫作主題仍然受到當時性别意識形态的限制。為了被男性作家所接受,女性作家往往把重點放在"專屬女性故事和體裁"上,将灌輸道德故事融入到自己的叙事中。
最安全,最被接受的女性寫作方法之一是以"母親教育者"的身份發言。當時,英國試圖"為新的家庭模式創造一個新的母親形象,通過改變女性來改變國家。"母親"被提升到社會文化的優先地位,賦予了"教育者"崇高的地位。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植物學寫作中母子對話的形式廣受歡迎。母性和家庭意識問題為女作家提供了社會、知識和經濟來源,使她們能夠大聲疾呼,并在教育系統和公共領域發揮更重要的社會作用。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在這種氣候下,女性被允許在植物學上寫作,因為她們被排除在其他主題的寫作之外。女性作為母親獲得的高地位是以犧牲她們作為獨立的精神個體和有的愛的對象的地位為代價的。
女性和男性:
由性别塑造的植物學
同時,即使在"适合美女"、"溫文雅"的植物學等領域,女性的禁區和争議也無處不在。
植物學在英國的普及是由于瑞典博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建立的人工分類系統。Linnaeus的分類方法基于易于識别的植物花卉,即生殖器官。這種分類方法又稱林奈系統,以植物生殖器官為分類的核心标準,以雄性(雄性器官)的數量和比例為"大綱",以雌性(雌性器官)的數量和比例為次要"目标"。根據花朵的特征,可以找到植物的歸屬感。這種簡單直覺的方法大大降低了植物學家觀察花草樹木的門檻。
但基于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分類,不可避免的是,原來中性植物學引入了無限的性别想象。特别是這一理論的創始人林奈,在他的陳述和理論上一向嚴謹,但他對植物的性關系有着豐富的想象力,甚至還加了葉子來戲劇化當時的性政治。在他的口中,男性男性作為人類男性性器官是活躍的,而女性則像人類的女性性器官一樣被被動接受。
照片 紀錄片"植物王國"。
在将林奈系統引入英國後,英國植物學家和詩人伊拉斯谟·達爾文(進化論創始人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的祖父)完美地繼承了這一理論,并寫下了"臭名昭着"的詩歌"植物之愛"。除了植物的紀律,這首詩更多的是喚起愛的沖動。通過與人類的類比,他用植物世界取代了人類的性,構思了"花花公子求美,得到植物之愛"的情節,充滿激情和性幻想。
雖然達爾文在《植物之愛》中對女性的自由描寫,但他的女性同行卻不敢效仿。在當時的英國,仍然有人認為,即使僅僅傳達性知識也不符合女性倫理,林奈将植物學與性聯系起來顯然是别有用心的。
牧師詩人理查德·波爾韋爾(Richard Polwell)在他的詩歌《無性戀的女人》(The Asexual Woman)中譴責女性植物學家是"新哲學中的堂吉诃德",女性作家公開展示自己的性取向,違反道德。在他的詩中,他寫道:
植物學使他們欣喜若狂,他們的胸膛高聳入雲,
(他們)還在采摘禁果,和夏娃的母親在一起,
驚歎于青春萌芽的花朵的心跳,
或者,在不回避植物的蕩婦的情況下,
解剖它的器官,被欲望玷污,
無辜地凝視着挑逗的粉末。
是以,盡管林奈的性分類系統簡單而受歡迎,但英國出版商、教師、父母和翻譯家對他的學說保持高度警惕,并對如何翻譯他的作品存在分歧。
橡皮擦達爾文植物園的插圖。
威廉·威瑟林(William Withering)是林奈學說最早的英語翻譯者之一,他認為翻譯需要深入,易于了解,以便女性可以快樂地閱讀。但是,除了普通大衆和他自己的女兒之外,他應該如何處理書中他所面對的女性讀者的性描寫呢?如何把握細節和生動程度?玄克的副本是否對植物王國中的一夫多妻制授粉提出了淫穢的解釋?在凋零的眼中,女性顯然不恰當地(或應該)謙遜和純潔,毫無顧忌地向她們展示植物性愛。是以,他将與性相關的術語和标題翻譯成英語,并避免所有與性相關的單詞。在不了解林奈理論的讀者眼中,很難找到書中女性和男性的重要位置。
這種做法一方面阻止了沒有拉丁語閱讀能力的女性植物學家學習"真正的"林奈學說,另一方面,即使是熟悉林奈理論的女性植物學家也不敢寫作,将自己束縛在一個有限的、允許的表達領域。結果,不懂拉丁語或缺乏古典教育的人(包括大多數英國女性)無法進入林奈植物學的核心領域。
當時著名的女性植物學家伊麗莎白·肯特(Elizabeth Kent)在書中寫道,"女孩的自然探索不被鼓勵,甚至被禁止":在年輕時,老師們将天真與無知混為一談,讓她們遠離書籍,因為它們的内容"要麼令人厭惡,要麼激勵女孩談論問題......滿足這種好奇心是不好的";随着年齡的增長,年輕女性害怕面對科學術語和拉丁語,因為她們"擔心被稱為學校的可怕名字"。
直到19世紀20年代,植物學才在一個更專業的領域取得了豐碩的進步,越來越多的植物學家放棄了林奈對植物生殖器官的分類,并采用了由巴黎的Yusu和日内瓦的Decando建立的"自然系統"分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轉變首先發生在能夠閱讀進階期刊的群體中,在公衆眼中,林奈成為兒童,初學者和女性更容易獲得的理論。
埃斯科拉·皮奧斯,弗洛拉,賽勒斯和丘比特圍繞着林奈半身像。
當植物學發展成為一門學科時,
女性很難進入大廳
"英國的漂亮女孩熱情地參與植物學研究,這為她們赢得了最大的尊重,并顯着提高了科學的聲望。雖然她們可能沒有為這一主題做出傑出貢獻,但至少使它成為一種流行和時尚趨勢——盡管人們普遍認為婦女不适合接受學術和專業教育訓練,但這一科學分支能夠取得如此顯著的成果,這一事實得益于如此多的婦女的參與, 這有力地證明了女性與生俱來的寬容和寬容。"
查爾斯·阿博特,貝德福德郡植物學,1798年
女性對植物學的寬容是慷慨的,并沒有改變植物學對女性的平等接受和歡迎。從1760年到1830年,性植物學文化為女性打開了大門,但從那時起,同樣的性别态度阻止了她們繼續參與植物學研究。他們首先被推入,然後被趕出。
19世紀初,科學和文化内部開始出現分歧,公衆與專家、人氣和學術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到20世紀30年代,與科學和文化中的紳士禮儀和娛樂相關的活動不再被接受,社會反而支援"嚴肅,實用,非娛樂的科學文化"。務實文化的發言人聲稱:"科學角色的專業化是政治需要,國家應該支援科學 - 不是因為它可以培養一個識字的階級或與優雅的文化相容,而是為公民社會帶來物質效用。"
植物學教授約翰·林德利的肖像,1848年。
這樣,曾經為了培養出"更優雅的淑女、更成功的母親"而向女性敞開的植物學之門,顯得不合時宜。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第一任植物學教授約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在1829年的就職演說中明确表示,植物學在英國受到诽謗,被嚴重低估,正是因為"植物學被視為女性的消遣,而不是頭腦冷靜的男人的職業"。"
林德利對"科學"和"溫柔技能"的區分在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英國引發了一場革命,植物學從中成為"紳士的學科",并開始了"去女性化"的過程。許多學科的曆史重複了19世紀植物學文化的模式:不同的群體區分不同的實踐方式,讓專業研究人員脫離愛好,劃分參與者的層次,講道和水準适當的演講,等等。
精英們的自我認同和科學實踐是排他性的,她們在女性和植物學文化的曆史叙事中具有侵略性和侵略性。
男性的"專家文化"剝奪了早期女性情感和經驗的權威價值。如信、對話等"親切的風格",原本最受推崇的女作家寫作模式,甚至是公認的模式,也引領了英國出版市場的潮流,伴随着成千上萬的英國兒童長大,為條件有限的植物學愛好者提供介紹;好奇的人憎恨這種寫作,當被迫閱讀這種模棱兩可的東西時,一個喋喋不休的老婦人或一個博學的處女成為虛構溝通中更權威的基礎知識大師。"
在浪漫文化中,科學女性受到批評,在科學文化中,女性被排除在研究植物園之外。
艾格尼絲·伊比松(Agnes Ibison)是所有偉大的人之一,并非沒有女性植物學家以嚴謹的科學方式探索新的植物學理論。她結合觀察和實驗,在顯微鏡和解剖學的幫助下研究植物。她還在植物生理學方面取得了許多發現,并在各種科學期刊上發表了50多篇文章,其中一些已被翻譯成瑞士,法國和意大利的科學期刊。1810年,《柯蒂斯植物學雜志》(Curtis Journal of Botany)的主編以她的名字命名了沿海蜂蜜茶樹,并稱贊她發表了幾篇"關于植物生理學的非常原創和啟發性的論文"。
即便如此,Ibison的科學研究之路仍充滿困難,男性當局對其進行了冷落和壓制。她渴望自己的原創研究被認真對待,她的想法被人知道,但她年紀大了,遠離大都市,沒有正式的導師,因為女性身份更不可能加入科學社會。她不得不獨自戰鬥。
Ibison多次寫信給詹姆斯·史密斯爵士,介紹他的研究成果,希望得到他的推薦和幫助,但史密斯一再無視她的要求。當林德利寫了一篇論文讨論推薦法國植物學家的理論時,Ibison發現自己在12年前就注意到了,并發現他的觀點與他自己的觀點相似。作為回應,她歎了口氣:"理論家的名字是多麼容易有偏見!"
花神弗洛拉(Flora)裝扮着大地(摘自《林奈系統的新插圖》)。
感受到性别歧視,Ibison在為學術期刊撰稿時故意改名寫作,誤以為他是"先生",直到第三篇文章才澄清錯誤。100年前,在18世紀初,是男性使用女性化名為《女性雜志》撰稿,普及他們的數學知識。
現在,200年過去了,女科學家的處境似乎有所改善,至少女性可以在與"嚴謹的科學寫作"相同的領域與男性競争,并且已被證明有助于讓女性有機會在專業和非女性化的科學文化中以平等的方式參與主流科學。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着承認一個由男性主導、男性建構的科學體系,該體系使用男性模型來建構遠離家庭、母性和情境思維以及其他被性别化為"女權主義"的文化因素的科學。
這樣,女性就不能以"女性"的身份,而隻能作為"中立"甚至"男性"的地位進行學術研究。
與此同時,曾經困擾和制約女性參與英國科研和取得成就的障礙并沒有完全消失,女性仍然以某種隐蔽但有效的方式被囚禁。例如,似乎婦女在社會和文化優先事項中處于優先地位,"婦女的堕落導緻國家的堕落",婦女被推入家庭和母親工作的陷阱,受到贊揚和贊揚,然後這種工作的價值和意義随後在法律上和經濟上被忽視, 或者說,女性适合讀文科,男性适合科學的結論是根據這種社會現實的後果反過來推導出來的。
"花神的女兒"的曆史還在繼續。
編寫|肖淑軒
編輯|張偉;王青
校對|張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