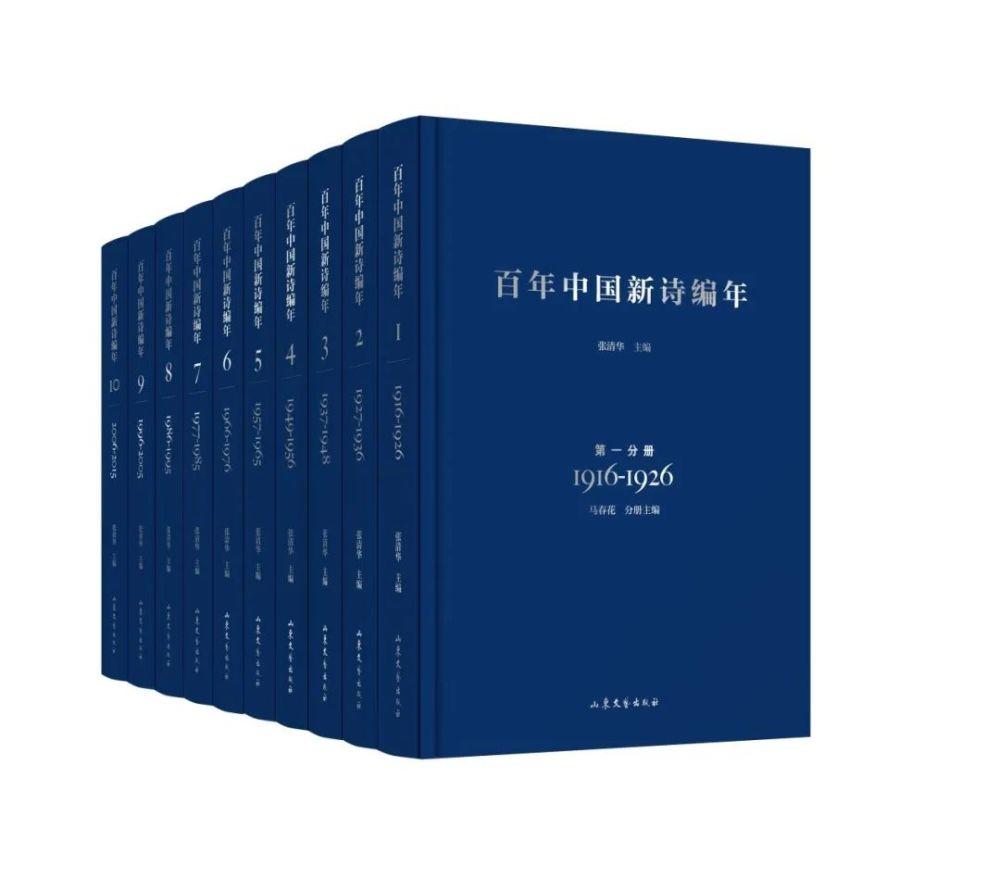
《百年中國新詩編年》
張清華 主編
出版社:山東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2年1月
2022年1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主編的《百年中國新詩編年》(全十卷)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編年”以十年左右時間跨度為一卷,描繪了百年中國新詩起于青萍之末而浩大于風雲際會的壯闊程序,共收錄1200餘位詩人、3000餘首中國新詩。“編年”通過大規模的資料搜集、考辨、鈎沉、整理和編排,依寫作或初發表的時間先後為序進行排列,進而形成一個狀貌相對完整、内容相對豐腴的中國新詩地理圖志,以努力接近百年新詩真實發展狀況的學術體例,呈現新詩創作的豐富性與多元性。《百年中國新詩編年》各卷收錄詩歌标準統一,入選内容、編次一仍其舊,以原發刊物為底本,作者修訂、校閱、編選本為校勘本,不同版本詩歌改動較大則作腳注,以“編者注”的形式說明。“編年”各卷序言由分卷主編撰寫,各卷末按詩歌編錄順序附詩人小傳,全集格式統一,另有主編所作全集總序。
全集總序《實驗與選擇,變奏與互動》從百年新詩的“寫作資源與外來影響”“象征主義、現代性與新詩内部動力的再生”“曆史與超曆史、限定性與超越性”“邊緣與潛流,現代性的迂回與承續”“平權與精英,百年的分立與互動”“經典化、邊界實驗,以及結語”六個問題出發,對新詩百年來的變革動力與内在機制充分探讨。下為總序第一部分節選。
《實驗與選擇,變奏與互動 ——百年新詩的六個問題》總序
文/張清華
“風起于青萍之末”,這是中國人古老的思維;而從現代意義上,加勒比海上的風暴,據說有可能是緣于一隻蝴蝶的翅膀的扇動。這兩者的表述雖然接近,但前者顯然是神秘主義或形而上學的思維,而後者卻是出于科學的推測。
大約在1916年,新詩出現了最早的雛形。在192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胡适的《嘗試集》中,開篇第一、二、五首的末尾落款所标出的年代,是“五年某月某日”,也就是1916年的某個時候。第三、四首沒有标出時間,但按照此書排列的時序,大約可推斷這兩首也是寫于1916年。由此我們大概可以得出所謂“新詩”誕生的最早時間。胡适曾言,在更早的1910年之前,自己也曾嘗試寫詩多年,在美國留學時與任鴻隽(叔永)、梅光迪(觐莊)等人還多有唱酬之作,但大約都不能算是“新詩”了,雖然比較“白”,但在形式上并未有突破。
遍觀《嘗試集》第一編,所見十四首中,唯有第五首《黃克強先生哀辭》,算是散句湊成,其他篇什基本都是五言、七言,偶見四言的順口溜,個别篇章如《百字令》算是俗化的長短句。“新詩”到底“誕生”了沒有,還不好說。然而,随着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刊出了胡适的《鴿子》《人力車夫》《一念》《景不徙》四首,以及沈尹默的三首、劉半農的兩首,沒人再否認“新詩”的誕生了。若照此說,那麼“新詩”誕生的時間點,應該是1918年了。
好壞則自然另說。胡适在《嘗試集》之《自序》中,不厭其煩地記錄了他的詩所遭到的批評與譏刺,悉數搬出了他之前與任、梅諸友之間的不同觀點,且“劇透”了他的《文學改良刍議》最早的出處,是1916年8月19日,他寫給朱經農的信中的一段話,所謂“不用典”等“八事”。筆者此處不再做前人都已做過的諸般考據,隻是接着開篇的話說,新詩并非誕生于一場多麼壯觀而偉大的革命,而是一個很小的圈子中的個人好惡與趣味所緻;其文本也不是多麼了不起的驚人之作,而是一個小小的帶有“破壞性”的嘗試。連最好的朋友也譏之為“如兒時聽蓮花落”,“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誠望足下勿剽竊”國外“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1]
何為“青萍之末”?不過是三兩私友的唱酬和激發,催生了一種新文體的萌芽,由此引出了一場百年未歇的詩歌革命,這算得上是一個明證了。然這還不夠生動,還有更妙的因由——曆來讀者都忽略了一點,在這篇《自序》中,胡适開門即交代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他為什麼開始寫詩。适之說,他自“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也就是1906年開始“做白話文字”,在第二年,也就是1907年開始讀古詩,産生了最初的寫詩沖動,是緣于這樣一個常人難以說出口的理由:
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以後我常常做詩,到我往美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2]
筆者提醒諸君的不是别的,正是适之先生作詩的緣起,是因為——“腳氣病”。如果從福柯的角度看,這算是一種看取曆史的方法;如果從中國人古老的思維看,便是起于“無端”,所謂“起于青萍之末”的偶然了。
但細想這偶然中豈無必然?如果說舊詩是止于高大上和沒來由的“萬古愁”,那麼新詩便是起于矮窮矬且鑽心癢的“腳氣病”。這其中難道沒有某種寓意,某種“現代性寓言”的意味和邏輯嗎?
終于為“百年新詩”找到了一個有趣的起點。胡适所引發的曆史轉換是全方位的,資訊十足豐富。由此開始新詩的道路、方法、性質和命運是對的——雖然我們也會隐隐擔心,他随後到美國留學,有沒有把這難治的腳氣病帶給異國的同窗和朋友。
一、寫作資源與外來影響:“白話”與“新月”的兩度生長
“威權”坐在山頂上,
指揮一班鐵索鎖着奴隸替他開礦……
最初的嘗試是令人疑慮的,由“腳氣病”所緣起的白話詩的味道,并不能夠“與人以陶醉于其欣賞裡的快感”,而僅在于“與人以放膽創造的勇氣”。[3]很顯然,即便是受益于胡适的放膽所帶來的新風的人,也不太願意承認他努力的價值。但假如我們持曆史的态度,就不應輕薄沈尹默、劉半農、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這些人所做工作的價值。事實上,在《嘗試集》中也有着類似《威權》這樣的作品,其中的“威權”的意象,被意外而又詩意地人格化了,它坐于山頂,驅役着一群帶鎖鍊的奴隸。“他說:‘你們誰敢倔強?/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這是否是在不經意間,也彰明了詩的品質呢?該詩後來的自注中說:“八年六月十一日夜……陳獨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後,某報館電話來,說日本東京有大罷工舉動。”這首詩中的資訊量顯然很大,不隻表達了對于統治者的憤怒和睥睨,更關鍵的是,還顯露了“現代詩”慣常的轉喻與象征的筆法。《嘗試集》中這樣的妙筆雖少,但卻不是無。
這就涉及新詩最早的關鍵性“起點”的問題。有人強調了周氏兄弟的意義,朱自清說:“隻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鐐铐,周啟明氏簡直不大用韻。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4]這十分關鍵,他啟示我們,胡适等人雖屬留洋一派,但寫作靈感主要卻是來自傳統古詩的熏染,是從“樂府”等形式中脫胎,故其作為新詩的革命性還是相對保守的;而周作人的《小河》卻是起筆于象征主義,是來自西方的影響。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由此我們可以來深入探查一下新詩之誕生,與中外特别是外來資源之間的内在關系。這其實構成了新詩最初的關鍵的道路問題。
顯然,最早的一批新詩作者,主要是來自留美和留日的一批寫作者:胡适、康白情留美;沈尹默、郭沫若和周氏兄弟留日;劉半農是先留英後改留法,但他彼時尚未曾受到法國詩歌的影響。如果比較武斷地下一個判斷,就是這批最早的寫作者,尚停留于形式選擇的猶疑中,暫未找到一個比較理想的“作詩法”。事實上,包括《小河》在内的寫法,基本還是散文化的“描述”。盡管康白情在其《新詩底我見》的長文中,也早已注意到了“詩與散文的分别”,也強調了“詩底特質”是“主情”,但實在說,這并不構成真正的“排他性”,即便白話詩人們意識到了“把情緒的想象的意境,音樂的刻繪寫出來”[5],他們作品的質地卻仍然難以脫離散文的窠臼。究其實質,概在于其思維與想象的陳舊與匮乏。是以,截至1919年秋,郭沫若開始在《時事新報·學燈》大量發表作品為止,新詩尚處一個“青萍之末”的萌芽狀态,“風”并沒有真正刮起。
如何評價初期白話詩,包括評價郭沫若,不是本文的意圖。此問題見仁見智,實難有定論。筆者想提出的一個問題是,接下來新詩在1920年代的迅速發育,主要是基于兩個重要的影響來源,或者說,是由兩個不同的背景資源,導緻新詩出現了兩個明顯不同的美學趣味和取向,而這一分野幾乎影響和決定了新詩接下來的道路。這兩個來源,一個是英美一脈,上承胡适,接着就是留美歸來(1925)的聞一多,以及留美始、留英歸(1922)的徐志摩,他們構成了“新月派”的主陣容;再一個就是稍後留法歸來(1925)的李金發、先留日後留法而歸(1925)的王獨清,以及留法的艾青(1932年歸國)、戴望舒(1935年歸國)等,他們所形成的“象征主義—現代派”一脈。夾在中間的,是留日的一批,留日的穆木天,雖然與創造社關系密切,但他主攻的乃是法國文學,是以又比較認同象征主義詩歌。至于創造社的核心成員,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田漢等,則基本屬于浪漫主義一脈,除了稍晚些的馮乃超表現出傾向于象征派的趣味,其他人基本沒有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
這三個陣營,或者說三個文化群落,因為留學背景、所受影響、文化認同、藝術趣味的差異,而展現出了不同的追求,并且顯形為差異明顯的美學流向,由此構成了新詩發展重要的源流與動力。
……
作者簡介
張清華
張清華,山東博興縣人,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研究中心主任,北師大教學名師。兼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詩歌學會學術委員會執行副主任。曾出版《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等學術著作15部,《海德堡筆記》《懷念一匹羞澀的狼》《隐秘的狂歡》《形式主義的花園》《一隻上個時代的夜莺》《春夢六解》《鏡中記》等詩集與散文随筆集多部。曾獲華國文學傳媒大獎2010年度批評家獎,《十月》詩歌獎,陳子昂詩歌獎,昌耀詩歌獎等多項。曾講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