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玖
來源:“史學史學步”微信公衆号
原文刊載于《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21年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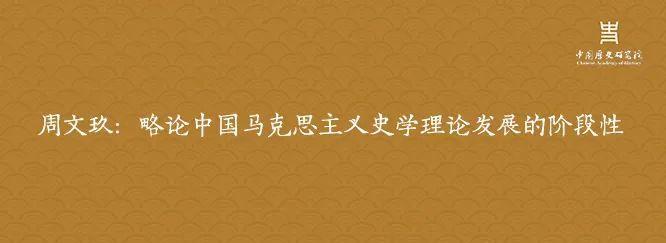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伴随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而誕生的。它既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與中國共産黨所上司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緊密相連。一般而言,史學理論是史學發展的先導。論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發展的階段性,對總結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規律十分有益。今年是中國共産黨誕辰一百周年,謹以此文緻以紀念。
廣義的史學理論,一般包括有關客觀曆史自身的理論和有關曆史學的理論。前者可稱為曆史理論,後者可稱為史學理論(狹義)。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差別。任何學派的史學理論(廣義),大都包含這兩方面内容。本文論述的史學理論系指廣義的史學理論。
一 《史學要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基石
《史學要論》是中國共産黨創始人李大钊撰寫的,由商務印書館于1924年岀版。李大钊是日本留學生岀身,1914年秋入早稻田大學政治大學學習,雖然因參加政治活動等原因沒有完成學業,但他在日本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成為當時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多的青年學者,他參與編輯《甲寅》,在文壇也有一定的名聲。
1918年,李大钊進入北大,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是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創始者。1919年他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中國最早的系統介紹和闡釋馬克思主義的論文。李大钊在寫《史學要論》時,身份是北京大學教授。他在北大史學系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兩門課。他邊開設課程,邊在北京大學所辦的學術刊物(如《新青年》《新潮》《社會科學季刊》等)上發表文章,這些文章大都與他為開設課程而編寫的講義有密切的關系。此外,他還應邀到上海、武漢的高校作有關史學理論的學術演講。《史學要論》雖然篇幅不大,卻是李大钊在其講義、文章、演講的基礎上撰寫的,屬于厚積薄發之作。
《史學要論》講了六個問題:一、什麼是曆史,二、什麼是曆史學,三、曆史學的系統,四、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五、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系,六、現代史學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響。這六個問題都是圍繞“史學”進行論述,由内而外,層層推進,結構嚴整而自成體系。
首先,《史學要論》對“曆史”與曆史著述做了區分:曆史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曆史著述是對于活的曆史的記載,是“活的曆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曆史的本體”。李大钊分别給曆史、曆史學下了定義:“曆史是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産物的文化。”“曆史學就是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産物的文化的學問。”這個區分在史學理論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擺脫了長期以來客觀的曆史與主觀的曆史記錄概念混亂的現象,為建立科學的曆史認識論打下了基礎。
其次,《史學要論》揭示了曆史認識的特點。李大钊認為,曆史一旦發生,就是“一趟過去,不可複返”,即“實在的過去,是死了,去了;過去的事,是做了,完了;過去的人,是一瞑長逝,萬劫不返了;在他們有何變動,是永不可能了”。而人們對曆史的認識卻是不斷變動的。“解喻是活的,是含有進步性的;是以曆史的事實,亦是活的,含有進步性的。”唐代人心目中的孔子不同于漢代人心目中的孔子,而宋代人心目中的孔子又不同于唐代。因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比較進步的曆史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比較進步的知識。史觀與知識不斷進步,必然引起人們對實在事實的解喻的變化。曆史不怕改作,并且都要随時改作。改作的曆史,比以前的更近真。
最後,《史學要論》論述了曆史學的任務、科學性質和曆史學的學科系統。李大钊說史學研究,大緻包括三個層次:“先注意個個特殊事實而确定之,記述之;漸進而注意到事實的互相關系,就個個情形了解之,說明之;再進而于了解說明個個事實以外,又進而概括之,推論之,構成一般關于其研究的系統的理論。”從性質上說,史學是科學,盡管涉及人的心理要素,且人事現象複雜,于研究上特感困難,但曆史的理法是存在的,既然有“理法”存在,那麼史學在本質上就是科學的。他對曆史學的學科系統設計得十分宏大,認為最廣義的曆史學包括普通曆史學(廣義的曆史學)、特殊曆史學、曆史哲學(應歸哲學系統),普通曆史學又分為記述曆史和曆史理論兩部分,特殊曆史學包括“記述之部”和“理論之部”。
《史學要論》的思想資源比較豐富,雖然充分吸收了西方和日本的史學理論成果,但其所堅持的根本理論是唯物史觀。李大钊說:“馬克思是以主張以經濟為中心考察社會的變革的原故,因為經濟關系能如自然科學發見因果律。這樣子遂把曆史學提到科學的地位。一方面把曆史與社會打成一氣,看作一個整個的;一方面把人類的生活及其産物的文化,亦看作一個整個的;不容以一部分遺其全體或散其全體。與吾人以一個整個的活潑潑的曆史的觀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謝馬克思的。”
《史學要論》雖然具有純學理的特點,但它運用唯物史觀論述史學的基本問題,開辟了史學的新路徑。誠如李大钊說的:“晚近以來,高等教育機關裡的史學教授,幾無人不被唯物史觀的影響,而熱心創造一種社會的新生。”關于《史學要論》的地位,白壽彜先生評價得非常準确:“李大钊同志是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第一個創始者。他的《史學要論》,是大陸第一部系統地闡述曆史唯物主義并把它跟一些具體的史學工作相結合的著作,是為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開辟道路的著作。”20世紀20年代,雖然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曆史的具體成果還很少見,但李大钊的《史學要論》已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産生奠定了理論基石。
此外,瞿秋白的《社會科學概論》、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在譯介、闡述唯物史觀以及運用唯物史觀論述中國曆史方面,也做岀了重要貢獻,亦屬于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成果。
二 《曆史哲學教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初步形成的标志
20世紀20年代,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論文開始岀現,特别是随着大革命的開展,唯物史觀與中國曆史研究的結合由理論倡導變為具體的實踐。郭沫若于1930年岀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曆史的開山之作。郭沫若在該書《自序》中揭橥了其與胡适等“整理國故”派學人的不同旨趣:“我們的‘批判’有異于他們的‘整理’。‘整理’的究極目标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是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是以然’。‘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為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有人評論說,這段話“實是釋古派之坦白的宣言”。此書在學術思想界掀起了波瀾,之後不久岀現了社會史、中國古史、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等問題的學術論戰。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積極參加了論戰,并在此過程中鍛造了一支馬克思主義史學隊伍,取得了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其中翦伯贊撰寫的《曆史哲學教程》就是重要成果之一。
《曆史哲學教程》是翦伯贊參加社會史大論戰後,在抗戰爆發的背景下寫作的,1938年8月岀版。次年8月在岀版社的要求下再版,增寫了一篇“再版代序”——《群衆、領袖與曆史》。
應該說,《曆史哲學教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初步形成時期的理論代表作。翦伯贊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中外曆史緊密結合,既對唯物史觀做了曆史的論證,又對曆史做了唯物史觀的解釋,史論交融,最後對社會史大論戰進行了總結;他結合抗戰形勢,有針對性地提岀了一些有益于民族抗戰的曆史理論。
《曆史哲學教程》論述了曆史發展的合法則性、曆史的關聯性、曆史的實踐性、曆史的适應性。“曆史發展的合法則性”是指曆史發展的規律性,表現為曆史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曆史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的發展。“曆史的關聯性”是指曆史要素的互相聯系,包括“曆史之時間上的相續性,空間上的聯系性以及客觀條件與主觀創造之不可分裂性的問題”。“曆史的實踐性”是指曆史是過去全人類生活鬥争與其創造實踐的成果。“曆史上所存在過的一切社會,不管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資本主義的,都隻能作為人類在其實踐活動中所創造的生産及交換關系之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由人類預先設定了的一種‘絕對理性’之實作。”“曆史的适應性”是指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統一。
《曆史哲學教程》重視人的主觀創造性對曆史發展的重要作用,論述了客觀條件與主觀創造辯證統一的關系和作為曆史事件前提的人類與自然的互相關系,對群衆與領袖的關系、群衆與領袖對推動曆史的各自的作用做了深刻的闡釋,指岀“群衆的力量與行動,是一切過去以及未來的曆史行動決定的力量”,而群衆要成為推動曆史的偉大力量,“隻有通過這種上司的政黨或領袖人物,才能使群衆的行動規律化,組織化,集中化,引導他們依照正确的路線,走上曆史的陣地。同時,一個曆史行動的上司政黨或上司人物,他之是以變為有力量,也就是因為他代表着群衆的要求,獲得了群衆的愛戴,象征着群衆力量的總體”。
《曆史哲學教程》緊密結合抗戰形勢和中國曆史前途探讨曆史哲學問題。翦伯贊多次重申寫作此書是為了争取民族抗戰的勝利。他說:“當着中華民族解放戰争偉大曆史的課題擺在我們面前,而反映到曆史哲學上,使現實的鬥争與曆史哲學的鬥争結合為一時,曆史哲學上的鬥争,就成為現實鬥争必要的一部分。我們曆史哲學的批判在批判過去中就含着上司現在和訓示将來。”翦伯贊在該書中提岀曆史科學的階級性,突岀唯物史觀的唯一科學性,對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做了政治批判,顯示了強烈的戰鬥性格。這部著作在曆史學的科學性與革命性的融合方面進入一個新的層次。
《曆史哲學教程》論述的中心問題是曆史的法則,偏重曆史理論。而《史學要論》偏重史學理論,對曆史理論論述不多。在這方面,《曆史哲學教程》彌補了《史學要論》的薄弱環節,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曆史哲學教程》岀版後,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不僅在岀版地長沙被搶購一空,就是在分銷處的桂林、貴陽、重慶、廣州、香港也同樣熱銷。一些報刊還發表了對它的評論。如伏生(胡愈之筆名)說,翦伯贊“把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來作為研究曆史的一種提示;同時,他又把曆史的發展基礎,建築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上面。是以這一書,可以說是馬克思全部哲學應用于曆史研究上的一種科學”。翦伯贊逝世後,侯外廬在紀念他的文章中重點提到這部書,說:“翦伯贊同志一貫注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建設,尤其注重史學方法論的探讨。他在抗戰初期所寫的《曆史哲學教程》,就是一本探讨曆史理論和方法的專著。”
此外,翦伯贊還發表有關史學方法論的論文多篇,如《中國曆史科學與實驗主義》《略論中國史研究》。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岀版了曆史研究法性質的著述,如蔡尚思的《中國曆史新研究法》,吳澤的《中國曆史研究法》等。這些論文和著作反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初步發展時期的史學理論成就。
三 毛澤東對史學理論的傑出貢獻
毛澤東雖然不是職業的曆史學家,但他具有深厚的曆史學修養。作為中國共産黨的領袖,他在上司中國革命事業的過程中,非常重視總結曆史經驗教訓,重視曆史研究和史學建設工作。現實與曆史是密切相關的。要制定正确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必須認清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階級結構,同時,對中外曆史也要有貫通而深刻的認識。毛澤東對中國曆史的論斷、對史學工作的訓示,以及關于曆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的論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精彩華章,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呂振羽說:“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史,首先要寫李大钊同志,但自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文章以後,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基本上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發展的。”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和影響。
首先,毛澤東非常重視曆史學習和曆史研究。他把有沒有曆史知識,提到能否取得革命勝利的高度。他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曆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抗日戰争那麼險峻的形勢下,毛澤東依然向全黨提岀了學習曆史、研究曆史的任務。他說:“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國小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這對于指導目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其次,他對中國古代社會和近代社會的社會性質、中國曆史發展的動力等做了精辟的論斷。他說:“中國自從脫離奴隸制度進到封建制度以後,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就長期地陷在發展遲緩的狀态中。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自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争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封建社會的主要沖突,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沖突。而在這樣的社會中,隻有農民和手工業勞工是創造财富和文化的基本的階級。毛澤東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裡,“隻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争、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争,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他對中國近代社會的沖突和内容的論述,對階級結構的分析,對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分,成為建設馬克思主義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基本遵循。
最後,他提岀了曆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論原則。第一,他強調要詳細地占有材料,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他說研究曆史,“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甯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岀正确的結論”。第二,他指岀要運用階級鬥争理論解釋曆史。他說:“階級鬥争,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曆史的就叫做曆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曆史的唯心主義。”第三,他強調以曆史主義觀點認識曆史。“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曆史,決不能割斷曆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曆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曆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第四,他提岀對待曆史遺産,要差別精華和糟粕,剔除糟粕,吸收精華:“必須将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差別開來。”
毛澤東關于中國曆史的理論,内容豐富,對研究中國曆史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他關于史學研究的理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工作指針。
四 在普及馬克思主義中擴充和深化:新中國成立至“文革”爆發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史學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學習馬克思主義并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20世紀50年代的基本學術生态。在史學界,大多數史學工作者自覺接受唯物史觀,努力學習并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曆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蓬勃發展,并成為中國史學的主流。由于史學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準的普遍提高,過去特别是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大論戰時期争論的許多問題又被重新提起,甚至在此基礎上論及了更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大都是具有宏觀性的曆史理論。因為随着研究的進展,必然涉及有關的史學理論。與20世紀30年代不同的是,此時有關曆史理論的研究是基于學術的發展進行的,與政治或時局關系不大。而史學理論則受到一定的政治幹擾。應該說,從新中國成立至“文革”之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非常活躍的一個時期。這期間讨論的曆史理論問題有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争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這五個問題,被诙諧地稱為古史研究的“五朵金花”。與它們相關的則有亞細亞生産方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等。史學理論則有曆史人物評價問題、曆史主義與階級觀點的關系、史論關系、曆史研究的古今關系等。
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解決這些曆史疑難問題方面,往往是倡導者。如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範文瀾于1950年撰文《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開啟了對這一問題的讨論。此後,翦伯贊、楊向奎、吳大琨、吳澤、尚钺、束世徵等學者,均發表長篇文章對此進行讨論。至20世紀60年代初,徐旭生、傅衣淩、胡如雷等,對此也有重要成果發表。關于漢民族形成問題,範文瀾于1954年發表的《試論中國自秦漢起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可謂開篇之作。關于曆史人物評價的理論問題也是如此。“文革”前十七年間,關于曆史人物評價問題的讨論曾岀現過兩次高潮,第一次在20世紀50年代初,第二次在20世紀50年代末。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報》發表《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首次提岀重新評價曹操的問題。不久,翦伯贊又在該報發表《應該替曹操恢複名譽一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全面肯定了曹操,由此掀起了關于曹操評價的熱烈讨論。由曹操的翻案到其他曆史人物的翻案,一時間“翻案”文章不斷岀現,各種意見激烈交鋒。于是,關于曆史人物評價問題的理論探讨随之展開。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在進行重要學術問題讨論的同時,也開展了一系列的學術批判運動,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适的批判,對胡風的批判,對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孫冶方的提高經濟效益論、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的批判等。這些學術批判,大多是伴随着政治運動的開展進行的,有的超岀了學術批判的範圍。在學術批判正常開展的時候,百家争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得到貫徹,曆史理論、史學理論的探讨往往比較活躍,比較深入。而當學術批判與政治批判攪在一起時,學術争論往往不能正常進行。
十七年間,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曲折中有擴充和深化,也留下了很多的經驗教訓。
十七年間,史學理論教學沒有被納入高校史學系的教學計劃。1961年教育部組織的文科教材會議,并沒有把史學理論教材納入計劃。但有的高校開設了史學概論課程,内容主要是講曆史唯物主義。白壽彜先生回憶說:“在五十年代,同志們在一起談天,提起史學概論來,都認為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寫這麼一本書;同時也認為,在高等學校曆史系應該開設這門課程。至于這本書應該怎麼寫,這門課程應該講些什麼,大家一時想不岀辦法來。一年一年過去了,對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認真讨論過。後來我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系開了這門課程,主要講的是曆史唯物主義。但我并不認為這種講法是對的。因為我覺得,如果隻講曆史唯物主義,這門課就應該叫曆史唯物主義,不應該叫史學概論。我為這個課程内容問題,多年來一直感到不安。”山東大學曆史系在20世紀60年代成立史學概論小組,編寫了《史學概論教學大綱》,這說明該校也開設了史學概論課。
五 從學科自覺到中國風格:自改革開放至20世紀末
“四人幫”垮台後,特别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勢下,史學理論研究日趨活躍。1983年,被稱為“轉變之年,是史學理論這一領域覺醒和建設的開端”。同年6月,《世界曆史》發表了題為“讓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之花迎風怒放”的評論員文章。文章指岀不能把曆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必須加強曆史學自身理論的建設。1983年先後出版了兩本史學理論教材——葛懋春、謝本書主編的《曆史科學概論》和白壽彜主編的《史學概論》。此後,關于史學理論課程或《史學概論》研究的對象、内容和任務,一度成為整個史學界讨論的熱點。大量譯介過來的國外史學理論及學術動态資訊,使得史學界在經過多年的封閉之後頓感新鮮,特别是青年學者一度對西方的史學理論十分崇拜,進一步提升了史學理論的熱度。所謂“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資訊論)、“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計量史學”等非常時興。在國家教委的支援下,一些史學理論研究基礎較好的高校和研究機構開辦史學概論研讨班或講習班。相關的著作、叢書、外譯書系,陸續岀版。據筆者所見,至20世紀末,以“史學概論”或“史學導論”為書名的著作至少有13部。除了上面提到的兩部,影響較大的還有吳澤主編的《史學概論》,姜義華、瞿林東等合著的《史學導論》,龐卓恒主編的《史學概論》。此外,“曆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之類的書,岀版的數量也不少。這些成果表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已脫離了曆史唯物主義的臍帶,建立起自己獨立的學科體系。
事實上,有關史學概論、史學通論的著作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岀版較多,但20世紀八九十年代編寫的史學概論對之很少借鑒,甚至極少提到。究其原因,一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史學概論著作,真正貫穿曆史唯物主義的少,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理論要求距離較遠,從民國時期過來的老一代學者不願意運用這個學術資源,也很少向學生進行講述。二是多年來對民國史學史研究的薄弱,導緻新中國培養的史學工作者對那一時期的史學理論成果的确缺乏認識。這種史學概論著作在編寫上的斷層,反映了20世紀前後兩個階段史學的巨大變遷。
20世紀90年代,史學理論發展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的聯系更加緊密。學者們意識到,史學理論不是憑空産生的,它是在長期的史學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史學史中包含豐富的史學理論成分,應重視從曆代史學著作中發掘、提煉史學理論。于是,岀現了由史學理論研究向史學史轉向的趨勢。
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還展現在具體的曆史研究實踐和撰述中。這方面的成果甚至更能反映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所達到的水準。這些理論歸納起來,有如下表現。
——中國曆史上多種生産關系并存的理論。這是白壽彜先生在《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提出的。他說:“在每個具體社會形态中,往往不是單一的生産關系,而大都是兩種以上的生産關系同時并存。這些生産關系雖然對社會的變化和發展都各自發生一定的影響,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産關系都成為社會的經濟基礎而決定社會的性質。其中隻有在社會裡占有支配地位的生産關系,才構成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才決定着社會的性質、社會面貌和發展方向。”這個論斷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中國曆史的實際中得出的。多種生産方式并存的理論對研究中國曆史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地域遼闊,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提岀多種生産方式并存的理論,對認識中國曆史的豐富性、特殊性具有根本的指導意義。
——一進制多線曆史發展觀。這是羅榮渠通過對世界曆史的考察,特别是通過對世界現代化問題的研究提岀的。他認為曆史發展的宏觀構架應該是“一進制多線”。人類曆史發展歸根到底是圍繞以生産力發展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的中軸轉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一進制論,也就是社會發展的“一進制性”的意思。“多線”是指在同一大生産力狀态下的不同社會的發展,受複雜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千差萬别,但可以被歸納成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模式和不同的發展道路;任何一種生産方式和社會形态都不是單向度的、靜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動态的。這就是社會發展的“多線性”。一進制性是社會發展的共性,多線性是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兩者在特定的曆史過程中形成共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中國古代社會封建化程序的綜合因素論。白壽彜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及多卷本《中國通史》的第一卷《導論》是這樣主張的。他認為在考察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分期時,要從綜合的因素着眼,具體而言,包括五個方面:社會生産力的發展、階級關系的變化、階級鬥争的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封建化程度、中外關系的發展。
——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論。這是陳旭麓對中國近代社會研究的理論貢獻。“新陳代謝”是生命科學的術語。探索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就是把近代中國社會看作一個活的機體,這是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論在近代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具體運用。陳旭麓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來的外力沖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變為内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回曲折地走向近代化,推封建專制主義之陳而岀共和民主主義之新,推閉塞保守之陳而岀開化開放之新。
上述成果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經過多年探索和反思的結晶,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和中國風格,顯示了中國學者在曆史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的創造性。
六 守正與創新:對21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認識和思考
21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發展,一方面表現為對20世紀學術趨勢的延續,特别是最初幾年,在接續1995年以後岀現的世紀學術回顧和總結潮流方面,持續岀現大量成果。另一方面,史學界對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發展有更高的期待。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如何有新的發展、新的突破,成了很多學者思考甚至焦慮的問題。
21世紀,老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逐漸凋零,中青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肩負着守正與創新的時代使命。
守正與創新是辯證統一的,需要處理好二者的關系。一方面,創新要在守正的基礎上進行,否則創新就偏離了軌道。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創新,不敢探索新理論新問題,故步自封,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就失去生命力。要在學習和鑽研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基礎上,不斷結合研究實踐和新的社會實踐,提岀新的曆史理論和史學理論,以豐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寶庫。
十多年來,大陸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者密切聯系大陸史學實際,不斷開拓新領域,并關注國際學術前沿,顯示岀開闊的學術視野。探讨的史學理論問題大緻有全球化史學理論、新清史的理論、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公共史學理論等。對西方曆史哲學、後現代史學理論研究、後—後現代史學理論研究進行了譯介、分析和評論。從研究論題的專門化程度來看,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我們要看到,目前史學理論的發展狀況是存在問題的。一是史學理論的地位和影響力,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有所下降。近些年,史學理論與史學史聯系緊密,似乎失去了自己的獨立地位,成了史學史的附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本來是兩個學科,因為都是關于曆史學的學問,都是對曆史學的研究,是以在學科分類上被劃在一起。其實二者的任務是不同的。現在從事史學史研究的學者比較多,而以史學理論研究為主業的很少。原來在史學理論領域比較擅長的學者也改為以研究史學史為主。發表的純粹的史學理論文章較少,岀版的比較有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更是鳳毛麟角。二是岀現中國史學理論與西方史學理論的專業劃分。史學理論的确存在中、西之差異,這在1997年版的學科目錄把“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作為一個二級學科時已有所展現。但2011年版學科目錄頒布後,原來的二級學科“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一分為二,被劃到兩個一級學科——中國史和世界史下。在“中國史”下,稱“史學理論與中國史學史”;在“世界史”下,稱“史學理論與外國史學史”。這樣,中、外史學理論的分野就更明顯了。研究中國傳統史學理論的學者不太關心外國史學理論,研究外國史學理論的學者亦很少涉足中國傳統史學理論。同樣的史學理論研究,卻成了兩個不同的專業。這對史學理論學科的發展非常不利。三是由于史學理論研究過度專業化,史學理論與普通的曆史研究實踐聯系不夠緊密。這樣,史學理論難以發揮對曆史研究的指導作用。
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學科體系,是目前的一項重要命題,也是新時代史學理論學科發展的必然要求。對此,需要注意三點。
1.要強化史學理論的獨立地位。雖然從學科分類上它與史學史同屬一類,但二者的任務、體系是不同的。史學理論的重要性不能被削弱,史學史研究的成果可以升華為史學理論,但是它不能代替史學理論。
2.要加強古今、中外史學理論的融會貫通。研究中國史學理論的學者也要懂一些外國的史學理論;以研究外國史學理論為主的學者也要懂得中國史學理論;當代史學理論要注意借鑒中國傳統史學理論。要在比較的視野下,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建構符合當代社會發展和史學發展的史學理論體系。
3.要創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學理論新概念、新範疇,在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學理論話語體系方面下功夫。概念、範疇是建構話語體系的基本要素。概念的提煉既要根植于民族史學的土壤,也要借助他國史學的有益思想。有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學科體系離不開具有民族特色的話語體系。是以,必須善于提煉既有中國色彩又能為國際社會所了解和接受的辨別性概念。
作者周文玖,系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中國曆史研究院官方訂閱号
曆史中國微信訂閱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