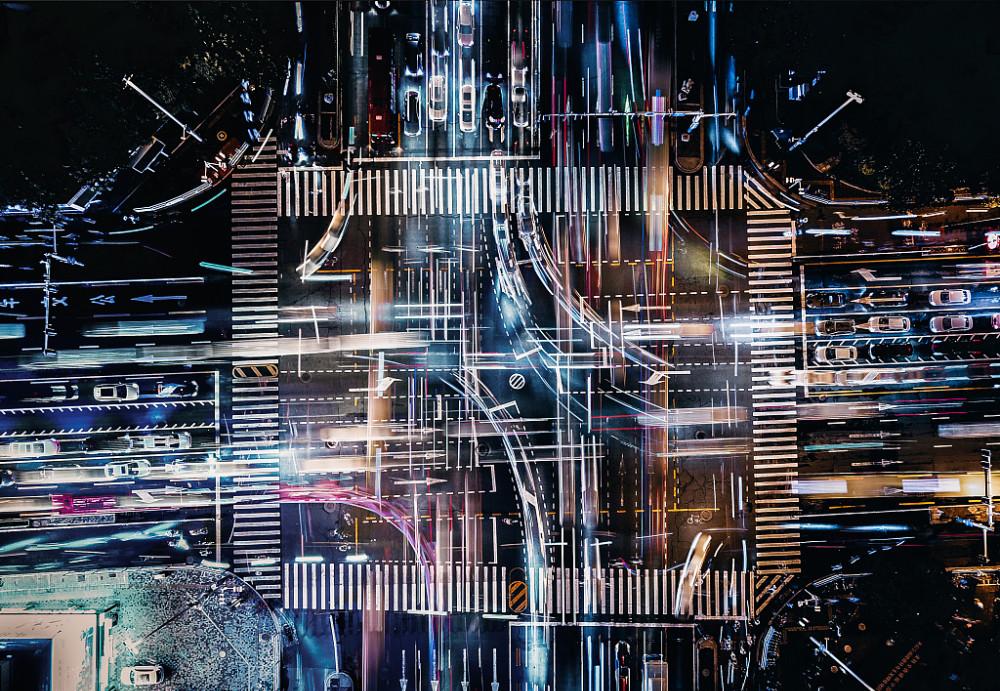
作者 | 張翠翠
編輯 | 傲敦
用了八個多月“花名”後,林月孟在去年12月收到一封快件,他被老東家告知不再發放補償。
“這表明公司主動終止競業協定,但不會明确說理由。”他解釋稱,對方停止打款并不完全意味着協定失效,不到一年限制時間,自己仍有義務為上一家公司涉密内容保密。
林月孟曾在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從事算法工作,到今年3月入職現公司整整一年。2021年1月離職時,他被啟動兩份為期一年的競業協定,一份是總體限制協定,另一份跟期權有關。
“這些檔案并不全是一式兩份,有些檔案簽字了,但不讓拍照,按下手印就拿走了。”現已擔任另一家公司的算法技術總監的林月孟,至今都清楚的記得前一家公司列出的限制公司名單,“大概有一頁半A4紙,有的看不出競對關系”。
為了規避麻煩,林月孟在新公司不敢用真名。競業期内,林月孟收到過老東家HR例行抽查電話,也常有獵頭聯系,事實上也被問過是否入職現公司。他習慣性的全部否認,“沒有不透風的牆,我不能在微信或者語音上做任何承認或回答任何問題”。
換回真名後,林月孟偶爾還會關注招聘資訊,他的下一個跳槽計劃已經在醞釀。
而在林月孟看似麻煩卻不斷嘗試開啟下一個跳槽計劃的背後,是汽車行業加入人才争奪戰後他所代表的行業人才的誘人“錢景“。獵頭徐靜對騰訊汽車稱,企業在用非常離譜的高溢價招聘,算法、軟體和自動駕駛人才薪水要求很高,沒有預算就是預算,有人在兩個禮拜之内換了6家企業。
車企和科技公司互相“拉黑”
汽車、科技和網際網路行業邊界日漸模糊,這讓更多人才卷入競業範圍。
市場公關崗的李響與林月孟同屬一家公司,日常工作看似沒有涉及核心技術,但也不幸被卷入競業大戰。去年12月離職時,李響簽署了為期半年的競業協定,競業名單中有汽車圈也有科技圈,他認為,“這已經是行業慣例”。
“新勢力企業中公關傳播不再是一個服務部門,是承接企業戰略的角色。事實上公關了解很多企業戰略規劃和商業模式運作。新興企業都在用内容方式講品牌故事,是以傳播類、營銷類人員也在被競業限制。”
李響回憶,“蔚小理”三家新造車企業從去年3、4月開始陸續讓公司核心人員簽署了一份明确限制網際網路和科技企業的競業協定,“那個時間段小米、百度等跨界造車浪潮很猛”。
緊張的“搶人大戰”氣息正是從那時開始彌漫。去年5月,何小鵬公開表示研發同學将擴張到500人以上;同年7月,雷軍在微網誌裡釋出自動駕駛部門招聘廣告,首批招募500名技術人員,有人一星期就拿到了小米汽車offer;華為為了給車企賣車,“天價”提成招人。
新勢力造車企業連夜跟員工簽署競業協定,被拉入“黑名單”的後來者們從2022年開始“反擊”。
今年1月,一位華為員工在社交平台發帖稱,“已經lastday離職流程一直不批,HR和直接主管每天溝通,讓簽競業協定,并且簽了就立即啟動,競業協定上列了不限于蔚來、理想、小米、Momenta、吉利、滴滴等20幾家智能駕駛車企、相關聯企業及子公司,簽了就隻能去養老院了。”
3月中,華為内部人士向騰訊汽車證明了上述消息。華為汽車業務在2月底更新技術人員競業協定内容,“把能想到的車企供應商都算在裡面,競業時長在3-24個月不等。過去都是核心技術人員才會涉及簽署競業協定,現在普通技術員工也要簽”。
與華為幾乎同一時期,宣布造車不到一年的小米也開始更新競業協定範圍和内容。36氪曾報道稱,小米在從2月中旬開始推行一項競業協定,主要面向19級以上的核心人才,競業公司也包括“蔚小理”等新造車企業。
同類消息在脈脈等職場社交軟體上成為熱點話題。2月25日,一位ID顯示在小米技術委員會任職的人發帖稱,部門被要求全員簽署競業協定,同時“增加了很多車企,大約40餘家公司被列在競業清單中”。
在汽車行業工作十幾年的李響認為這很合理,“汽車已經變成一個新賽道,已經真正成為數字化智能終端,是以現在不會是汽車公司與汽車公司較量,會是汽車、網際網路和科技公司三者之間的競業和競争”。
曾在傳統車企擔任營銷副總裁的趙悅告訴騰訊汽車,銷售和營銷領域經驗很重要,但競業限制範圍也不會很廣,賣車不是靠個人,即使是最進階别的人最多會被競業兩年,多數都是一年。
“過去傳統車企高層離職後很快就會入職下一家,也會很高調,但是現在不同,我熟悉的營銷高層被競業後入職新造車企業都會非常低調。”趙悅說,在算法、軟體等核心技術崗位競業更是殘酷,“競業限制範圍廣跨度大,列上一串企業,一個搞技術的人競業一年,對個人對行業傷害都很大”。
無論是傳統車企還是網際網路造車公司,一面說裁員,一面又說招不到人,而多數企業隻想找現成的人才直接創造價值。
“前段時間大家都在轉吉利研究院院長被網際網路造車公司高薪挖走,開始他本人辟謠了,但是後來又加入到順為資本,這是‘曲線救國’,他不可能不去造車。”趙悅說,懂的人都懂。
人才寶藏被撬開後,傳統車企不再“佛系”應對。去年8月,一份多達130餘家競業企業名單的長城汽車競業協定被曝光,違約金高達80萬元。“技術中心全員簽訂,人力最新規定說離職之後百分百會啟動。”脈脈上有長城員工透露,有的競業期甚至長達2年。
長城在職員工江林告訴騰訊汽車,這份更新競業協定不是入職的時候簽的,“是去年8月統一讓員工簽了一批”。
業務闆塊複雜的比亞迪動作較快。早在去年3、4月份,比亞迪就與“蔚小理”等企業第一批就啟動更新版競業協定。不過新協定僅面向新員工,一位比亞迪内部人士告訴騰訊汽車,現有員工仍然沿用過去針對汽車行業的競業協定。
相比自主品牌車企的迅速反應,外資及合資公司車企有點“反應慢”。
一位福特中國的研發工程師告訴騰訊汽車,沒聽說過有競業協定,“估計是高層才會簽”;華晨寶馬一位電池專家表示,“沒有簽過競業協定,對跳槽沒有什麼影響”;另一位上汽通用負責車聯網相關業務的人士則透露,“簽了協定,但這在公司内部并不普遍,客觀上确實提高了人才流動成本”。
30%的補償金和不設“上限”的違約金
對發起方來說,競業協定是築起隐形壁壘的手段,看得見的代價是給前員工的一筆不算太多的補償金,看不見的是,企業會動用HR、私人偵探或律師等專業團隊來維護自身利益。
而對簽署該協定的個體來說,所有的沖突都會對焦在一個字上:錢。
前公司和現公司給林月孟的薪資并不少,但說起“錢”,他還是覺得“肉疼”。據他描述,網際網路企業一般會設定半年到一年的競業期,補償金良心企業會給到前一年平均月薪的50%,每個月像工資一樣打給競業期的離職員工,而大部分人隻能拿到30%。
“當時協定裡規定的現金部分的違約金是年薪的3倍,另外還有期權部分的賠償。”剛入職時,林月孟給法務看了上一家公司的競業協定和脫敏資料,對方表示如果最壞的結果發生,“比如引起訴訟的話,公司願意支付現金部分的賠償,但是期權股票部分要自己賠付”。
競業協定中約定的補償金有量化标準,違約金則無“上限”,是以兩項金額看起來懸殊巨大。
在2021年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争議案件适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中規定,若勞動者履行了競業限制的義務,要求用人機關按照勞動合同解除或終止前十二個月平均工資的30%按月予以支付經濟補償的。
關于違約金,《解釋》中規定,勞動者違反競業限制約定時,應當依約向用人機關支付違約金。約定的違約金數額應在公平合理的範疇内,否則超出該範疇的違約金數額或将難以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援。
不過,林月孟對騰訊汽車回憶道:“實際執行過程中沒有商量過這個‘約定’違約金金額,如果有異議員工可以不簽,但是很少有人不簽,不想鬧得太僵。”
研發工程師王迅的前公司是一家上遊原材料供應商,離職前的最後一天公司才告知啟動競業協定。“協定裡規定的賠償金是競業期獲得的雙倍收益,包括下一家公司的工資收益再加上前公司已經給到的補償金。”
無“上限”的違約金成為企業留住人才的法寶,為了警示更多員工,動力電池巨頭甯德時代甚至把違約金“炒”到了100萬元。
裁判文書網顯示,2019年-2020年間,甯德時代因競業限制糾紛将9名前員告上法庭。原因是他們在離職後分别加入無錫天宏和保定億新,這兩家公司被判定為蜂巢能源關聯公司,法院均判處員工需要支付甯德時代競業賠償金100萬元。員工不服上訴,二審仍維持原判。
涉事員工在甯德時代時的月薪在8000元-2萬元不等,違約金統一都是100萬元,對于月薪僅為8000元的員工來說,賠償金相當于年薪的10倍。
“巨額”賠償金引起業内和媒體熱議。“對個人來說這不是一筆小錢,但跟企業的體量相比,賠償的錢還不夠花費法務、HR盯着你的精力。企業寫在競業協定裡面比較嚴厲的,主要還是起到警示的作用。”一位業内人士這樣對騰訊汽車表示。
不過,法院判決中駁斥了賠償金不合理的指控,“勞動合同法的目的在于預防商業秘密被洩露的可能,并不以用人機關遭受實際損失為前提”。
随着新能源汽車行業的飛速發展,動力電池等核心技術人才已經成為各家争搶的焦點。
已從甯德時代離職的員工告訴騰訊汽車,甯德時代内部經理以上的職位都要簽競業協定,競業時間一般在2年;據一位電池上遊電解液供應商員工描述,“競業協定很普遍,而且上下遊都會限制,我們跳槽去電池公司也會被簽競業協定”。同時,他表示,“違約金亂開的,這個本來就不規範”。
隻要不走上法庭,競業協定和涉及到的錢數更像是被藏在暗處的武器。
一位接手過競業協定相關訴訟的律師告訴騰訊汽車,沖突被挑明之前,很多人都不會注意違約金,對于那些不違約的人來說,更沒概念。
宋震曾在傳統車企從事三電工作,2017年入職時簽署過一份競業協定,2021年離職時公司對他啟動了協定。宋震對騰訊汽車回憶稱,當年簽署的“空白”協定在簽字啟動時增加具體企業名單,但是由于離職後換了賽道,上司沒有執行競業限制。
從上一家公司離職到加入新公司有一段空檔期,宋震并沒有收到過前一家公司發放的30%補償金,也沒注意過協定裡的違約金細節。但說起“甯德時代100萬違約金”事件,他用肯定的語氣說,“競業協定被濫用了”。
“企業對知識是鎖定的,希望把你入職期間一切有價值的工作全部鎖住,龍頭企業通過這種方式禁止人員流動。”宋震認為,這是國内知識産權保護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針對員工個體給潛在競争對手施壓,其實核心是想解決不正當競争。
反競業套路下的虛幻與真實
競業協定逐漸成為普遍現象,但在實際操作中,員工在離職時真正啟動競業協定的仍屬少數。“簽歸簽,不一定真的會啟動。”林月孟說,協定更多是起到警示作用,讓員工跳槽時有所顧慮。
即便真的啟動,“規避”競業協定的手段也已經成為行業慣例。一位獵頭告訴騰訊汽車,員工離職的時候低調一點,在入職的時候用花名,先簽署第三方合同,競業期過後再簽正式合同。
“引入進階人才後,企業會簽外包崗位,一旦法院舉證,外包公司并不在你的競業協定名單中,以此來規避。”上述獵頭說,通常情況下,在企業内部軟體中搜尋不到相應的人,“無名無頭像”。
徐靜是專門為新勢力企業挖進階人才的獵頭,據她描述,國内新勢力企業對智能駕駛相關崗位執行層的競業限制更加嚴苛,戰略相關高層反而會打“情感牌”戰術。
“比如VP級别高層離職,一般會轉為該企業進階顧問,期限大概在半年到一年不等。”徐靜解釋稱,其實這是變相競業,進階顧問也會有相應的限制條款,但相比實際意義上的競業協定會寬泛許多,“違約金是象征意義的,期權和股票也都會全部解禁給到員工”。
曾在車企擔任過技術高管的羅軍認為,實際上企業不願意出此下策嚴防執行層員工,但在智能駕駛賽道還未進入決戰時,大家都會不惜一切代價防止核心技術洩露。
“如果一些敏感IP被執行層面的技術專家帶到競争對手那裡,會大大縮短研發周期,甚至有可能實作商用,這會對企業形成更大傷害。”羅軍說,很多人想做智能汽車,但真正有經驗的人非常緊缺。
不過從商業化程度看,智能駕駛賽道遠比電池領域“安靜”。新勢力企業高層段輝對騰訊汽車分析稱,從競争壁壘看,不難了解甯德時代的做法,但從行業發展前景看,産業鍊其他企業也需要人才,普通工程師流動起來,才能帶來希望。
“汽車設計和電池制造不同,前者可以探索技術規避,後者更像制藥,電池材料探索很可能是‘有去無回’的事情,尤其是電池配方一旦洩露,就會給企業帶來緻命打擊。但配方等關鍵技術會有嚴密的加密措施,也不是所有人能掌握的。”段輝這樣認為。
一位電池企業中層上司在非公開場合曾無奈表示,對競業限制也要考慮員工個人的發展生存問題。“不可能挖幾個研發人員就能把我們研發方向和戰略都改變了。”
無論是電池還是智能電動車賽道,非風口行業人士看來今天的人才戰太離譜,但站在時代和市場角度,似乎又合理。甲方乙方似乎正在“不約而同”的把事情往極端方向推進。
獵頭徐靜對騰訊汽車回憶稱,企業在用非常離譜的高溢價招聘,算法、軟體和自動駕駛人才薪水要求很高,沒有預算就是預算。“有人在兩個禮拜之内換了6家企業,用上一家企業offer擡高下一家企業offer價格。後來獵頭圈和這6家車企把這人拉黑了。”
在“買賣”雙方失衡的環境中,智能駕駛賽道從業者擁有了更高的議價空間,但反過來企業也會想盡辦法鉗制住付出高昂代價招來的人,競業限制企業名單随之“野蠻生長”。
“入職時給你寫20家,離職時可能是一百倍的2000家企業,現在一些新勢力已經列了1000家企業。”羅軍認為,雙方的博弈正在把人才生态帶入惡性循環,不過相比網際網路行業,智能汽車賽道遠未到“明着搶人,暗地害人”的熱戰階段。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騰訊汽車,某大廠會給一批競對公司内線打錢,之後有人單線跟“卧底”聯絡,提供照片、語音等證據,“這種東西就跟法律夫妻和事實夫妻的判定一樣,法律訴訟中都會認”。
因為一套成熟的競業與反競業的“套路”存在,員工與企業、競對關系公司間難免引起争端,“競業限制糾紛”引發的法律訴訟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裁判文書網資料顯示,從2014年起相關訴訟顯著增加,到了2018年相關訴訟已達到324起,2019年有420起,2020年達到585起,2021年為388起。
曾在新造車企業擔任自動駕駛副總裁的海林認為,目前行業屬于惡性競争階段,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高薪挖人”,現在又衍生出被濫用的競業協定,這種模式持續不了太長時間。
羅軍則認為,任何一個行業熱的時候都難以避免人才戰,智能汽車正在重複房地産、網際網路行業之前發生的事情,存在即合理,現在剛剛看到端倪。“網際網路公司競争中,有些企業赢在關鍵人身上,智能汽車賽道是資産和人才密集型産業,等真正決戰時,企業願意賠付違約金,掏錢搶占戰略級人物。”
競業協定是為了維護行業秩序而誕生,但在某種意義上,它似乎又無法左右自身散發出的力量本身,反而成為破壞秩序的力量。
吉林大學青島汽車研究院副院長顧國洪,曾在兩家锂電池企業擔任高管,他認為,“我們有必要對競業禁止限制範圍的合理性進行慎重和深入地思考。在競業限制、科技創新、勞動者權益三者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是當今社會最大公約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