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關羽:由凡入神的曆史與想象》第七章書摘,由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 | (荷蘭)田海
“關夫子”的形象
17世紀中期,士人群體開始給關公冠上一個新的稱呼——關夫子。很顯然,這個稱呼是比照口語中的孔夫子一詞來的。“孔夫子”這個詞至少在12世紀就已廣泛出現在口語中,比孔子本來的稱呼更加廣為人知。 “關夫子”這一稱呼最早出現在一部1657年出版的佛教論集中,同一時代出現的還有一個新的關公形象。這一形象有一張不同尋常的紅色面孔,三縷長長的黑須,身着綠袍,膝蓋上還攤着一部書,代表關公所讀的《春秋》,這一形象從此流行開來,其流行程度僅次于一手舉偃月刀、一手撫摩長髯的傳統坐像或站像。但“關夫子”這個新稱呼似乎隻在士人群體中流傳,大多數人依然繼續使用地方習俗中的稱呼,特别是關公、關帝或者關聖帝君。文人與受教育群體在清代始終保持着增長,這一稱呼的迅速普及顯然也與此有關。
當然,稱呼上類比于孔子并不會讓關公真的轉型為同類神祇。因為孔夫子并不會成為扶乩儀式中的主角,也不會真的為祈拜者提供神助或庇佑。盡管祈拜者能夠以同樣的情由向兩尊神祇祈告,但對祈拜者而言,關公顯然更加實用,也更為流行。江南常熟的地方志記載,晚明時期關公擁有多種身份,既是“科場司命”,也為佛教徒充當“寺院宿衛”,又是道教徒對抗蚩尤的神将。我們很難确定關公作為文士的新形象從何而來,但這一形象很可能為他在大衆中的進一步傳播提供了助力。這也說明士人群體并不想把關公視為一尊僅供愚俗平民崇拜的神靈。在接下來的兩節中,我們首先讨論北京正陽門内的關帝廟對推廣這一士人形象所起的作用。我将說明關公文人形象的大規模流行與晚明文化氛圍有着直接的相關性,盡管這一形象的雛形已經存在了幾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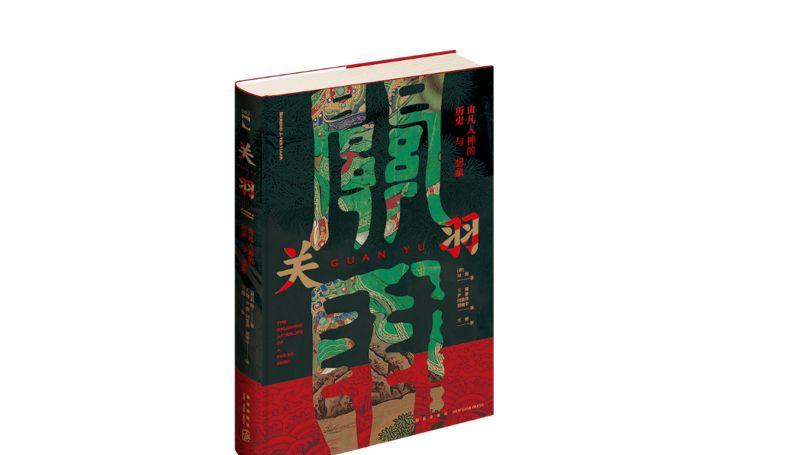
《關羽:由凡入神的曆史與想象》,作者:(荷蘭)田海,譯者:王健 尹薇 闫愛萍 屈嘯宇,版本:新星出版社2022年3月
正陽門的關帝廟
對于生活在晚明和清代的士人來說,北京正陽門旁的關帝廟盡管并沒有多麼宏偉壯麗,但在衆多崇祀關帝的廟宇中卻最為出名。這座城門今天仍舊獨自兀立在天安門廣場一端,但在那個時代,它無疑是北京最重要的一座城門。無論是供職于内城,還是受诏從外地來紫禁城觐見皇帝,各路官員都要從這座城門穿過,連皇帝自己從外城南端的天壇祭天回銮也要穿過這裡。在皇城的九座甕城中(文獻中一般稱為“月城”),七座的門樓上都建有小型的關帝廟,甕城裡還有兩座真武大帝廟,裡面供奉的是另一位重要的宿衛驅邪之神。是以,這座關帝廟中的神祇一開始首先是皇城的宿衛之神,與他在明代軍隊中的角色幾乎一模一樣。
晚明蔡獻臣在約1615—1617年撰寫的筆記中提到,這座關帝廟緣起于關公在明初對皇室的幾次襄助。無論是否确有其事,這一說法本身無疑為這座廟宇如此顯赫給出了一種被人廣為接受的解釋。據蔡獻臣所言,朱明王朝早在鼎定之初,尚未結束征伐之時就已經得到了關公的護佑。盡管明初史料并未言及此事,但在蔡獻臣的時代,關公護佑了王朝鼎定江山卻是一個常識。而且,蔡獻臣此處還提到1550年發生的“虜薄都城”一事,應指俺答汗在這一年成功侵襲到北京周圍。大軍壓境時,人們“夢君将天兵大戰,盡殲之”。次日,“胡虜”撤退,京城得以解圍。蔡獻臣談道,包括這件事在内,關公一系列的顯應神迹讓皇帝深感其神威之盛,皇帝是以賜予關帝一個新的封号。故事裡的這位皇帝就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萬曆皇帝。
《三國演義》中的桃園結義片段。
但正陽門邊的這座小關帝廟之是以最終成為整個關羽崇祀網絡的關鍵中心之一,或許更因為它的位置實在太過重要了。各路精英天天從這座城門下穿過,也經常擁堵在小小的甕城裡。不難想象,他們是以成為關羽的信衆,進而成為神廟各路信衆中最為重要的群體。正陽門關帝廟的靈簽也非常出名。我們可以想見,人們從正陽門穿入,準備進入内城的時刻,往往也是面臨人生重大轉折的時刻,可能是科舉高中,也可能是名落孫山,可能是新官上任,也可能馬上就要得見天顔。他們是以更加希望得到神靈的啟示。盡管甕城已經在20世紀初被拆毀,但這座關帝廟以及相鄰的觀音廟卻儲存到了20世紀60年代,直到那個時代的政治狂潮将其徹底吞沒。
與正陽門關帝廟有關的預言最早見于李蓘(1531—1609)的作品。當然,雖然李蓘提到的這則預言結果轟動一時,但卻未必是關羽崇信者們所樂見的那一類:
歲(嘉靖)戊午間,予在京師正陽門外,(關)王之廟素稱靈赫。有王姓者持錢乞簽,蔔弑其母,亦即昏眩,大呼伏地雲:王縛我,王縛我,我欲爾爾。
這件奇事被巡檢上報給了上官,姓王的人很快被關進了大牢,但罪人最終受何刑罰就不得而知了。
晚明的傑出學者焦竑(1541—1620)不僅為正陽門關帝廟撰寫過碑文,還主持編纂了廟中神祇的行傳集。1603年他為這部行傳集作序,題為《漢前将軍關公祠志》。序中如此描述正陽門關帝廟的地方崇祀:
自文皇奠鼎于茲,人物輻辏,绾四方之毂。凡有謀者,必祈焉。曰吉而後從事。⋯⋯四方以京師為辰極,京師以侯為指南,事神豈可不恭?餘少知響往,夢寐之中累與侯遇。
在這段文字中,焦竑一方面說明了這些每日穿梭于正陽門的一般信衆是如何祈求神示的,另一方面還寫到了他個人的夢示經曆。或許正因為自己的夢示經曆,焦竑此後又參與了另一部神祇行傳錄的編輯工作。
将近兩百年後,紀昀也描述了正陽門關帝廟的盛況,與焦竑所述差異不大。紀昀久任京官,曾任《四庫全書》總編修,是以經常出入紫禁城:
神祠率有簽,而莫靈于關帝。關帝之簽,莫靈于正陽門側之祠。蓋一歲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黃昏,搖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給,置數筒焉。雜沓紛纭,倏忽萬狀,非惟無暇于檢核,亦并不容于思議,雖千手千目,亦不能遍應也。然所得之簽,皆驗如面語⋯⋯
紀昀還記述了一些頗為日常的例子,在這些例子裡關帝的簽文詩句十分晦澀,卻又總能預示出即将參加鄉試的士子心裡的願望。毫無疑問,隻有在科考結束的那一刻,人們才會悟到這些詩句的真意。這種感悟未必與他們初見這些詩句時所想所感相同,但卻會成為對簽文的最終解釋。
是以,正陽門關帝廟展現的正是士子和關帝崇拜之間一種最為直白的關系。盡管這裡未必是全新關帝信仰的發源地,但因為這種關系,正陽門關帝廟成了傳播這些觀念的理想場所。無論是直接入廟拜訪,還是和同侪一起交流有關這座廟的各種故事,這些都讓新信仰的種種細節不斷灌輸給了士人,并從這裡帶向王朝各地。有一個例子能夠非常好地說明這種傳播能力。1614年,朝廷冊封關公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這一冊封是在正陽門關帝廟中公布的,之後沒過幾年,這個封号就傳遍了全國。晚明至清代的文人們與這座廟宇關系密切,由這座廟而來的各種靈驗傳聞也是以頻繁進入文人們的随筆集,字裡行間都可以看到廟宇和神祇對文人墨客的深刻影響。
熟讀《春秋》
關羽的神祇聖迹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發展方向:他對《春秋》這部儒家經典的研讀能力明顯在不斷增強,最終被大衆視為解讀《春秋》的大師。《三國志》中有關關羽的傳記隻記載了他曾給諸葛亮寫過一封信。當然無論這封信是親筆所書還是由人代筆,其内容都早已散佚。從今天可見的傳記材料看,關羽和他義兄之間完全是用口語來交流的。《三國志》裴松之注中大量引用了《江表傳》注釋相關史事,後者撰于三世紀晚期或四世紀早期,今已散佚。《江表傳》中提到,“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這句話對後世很多個世紀關羽形象的建構産生了很大影響。盡管這段文字并沒有說明曆史上的關羽經史水準到底如何,但後世文人卻都将其作為關羽精通文學的證據。
這段文字中所用到的“略”字,應當解讀為“謀略”“軍略”而非他解。但能通過背誦或閱讀《左傳》作為制定軍事政策時的參考,這在那個時代并不稀奇,因為相比于那些抽象的軍事學著作——比如《孫子兵法》,《左傳》裡有一系列作戰的生動例子可供參考。這種解讀方式并不來自儒家強調“褒貶”的《春秋》解讀方法,盡管後者才是儒家研讀《春秋》的主要方向。但這段文字裡并沒有提及《春秋》,而如大塚秀高所言,西晉作者筆下的關羽形象有可能受到了同時期劉淵傳記的啟發。最後,這段記載也未提及任何與“讀《春秋》”這一舉動有關的内容,而強調的是關羽的記誦能力。這也許說明關羽學習過《春秋》中的某些内容,而且能複述其中的一些重要故事,但他靠的并不是深厚的文字功底,而是口默心記。
在關公崇拜出現之初的一個世紀裡,關羽身上這種糅合了真實與虛構的文字能力并未對其神祇形象建構産生過什麼影響,因為這類神祇中很少有能夠識文斷字的,大多數雛形期的神祇更經常被标榜為不通文墨之人。無論關羽最初的玉泉山神迹,還是解州鹽池神迹,這些故事關注的都是關羽的武力。從宋、金、元至明初,關羽顯聖的故事都是以這一要點為中心展開的。第五章我們講述了1125年發生在荊州府的故事,關公使一個文盲獄卒突然獲得了讀書寫字的能力。盡管獄卒的書法變得十分傑出,但他寫下的具體文字卻與儒家經典并無關系。這個故事裡,書法能力隻是證明關公對這位獄卒施加了神力的證據,因為這位獄卒本身是一個文盲,毫無疑問其書寫能力隻能來自神賜。實際上,獄卒寫下的這段文字非常簡單、常見,遣詞造句上既沒有精巧之處,字裡行間也沒有什麼微言大義,文學水準極其有限。這些文字隻是獄卒常年接觸的刑獄檔案範圍内的文字水準,與真正的經典毫無關系。
不過到了1204年的一塊廟碑中,作者已經明确将關羽的曆史形象描述為一個可以閱讀《春秋左氏傳》的人。《三國志平話》這部通俗文學作品是這一形象的最早出處。該書大約編撰于1294年,最終結集于1321—1323年。書中描述關羽“喜看春秋左傳”,這裡的“喜看”是通俗小說中對于“閱讀”的一般寫法。這一說法并未在最初《江表傳》中提到的“好左氏傳”上有更大的發揮。16世紀晚期十分流行的一則故事中有了對關羽“讀春秋”更為明确的描述。故事提到,關羽陪同兩位義嫂時,夜讀《左傳》以免擾亂心神。但無論是16世紀早期的《三國演義》版本,還是後世對這個故事的引述都沒有說明關羽夜讀的是《左傳》,可見這點并不是關羽故事傳統中的固定要素。我在毛綸(1605—1700)與毛宗崗(1632—1709後)對《三國演義》的評點中才明确找到了這一要素,不過在毛氏父子的時代,“關羽夜讀《春秋》”已經成了士人對關羽的固有認識。毛氏的點評中多次提到,關羽通過閱讀《春秋》已經對這部經典了然于胸。可見,盡管“讀春秋”早已包含在神祇形象的意蘊之内,但關公崇拜真正系統性地吸納這一要素并将其納入文學叙事是明末清初的事情,其背後的驅動力正在于當時士人讀者渴望一個更加文雅、更加士大夫化的關羽形象。當毛氏父子以文學批評的方式将這一形象和小說糅合為一體後,它也就成了關羽在讀者那裡的标準形象,并一直延續至今。
上面這些例子為我們展示了“關羽通春秋”是如何不斷地融入關羽信仰傳統的。這些例子雖然發現時間較晚,卻能夠為我們說明文字傳統對于宗教崇拜的影響。當然,這一影響具體的發生時間和社會效應還要做進一步的研究。“關羽通春秋”的基本情節由來已久,《三國志》注疏中聲稱關羽對《左傳》有興趣,這是該情節的源頭。但這一内容在來源可疑的廟碑以及通俗文學中首次出現卻都不早于元代。假如論及“關羽通春秋”這一觀念對關羽崇拜活動産生的實際影響,那更不會早于晚明,要到清初才在關羽的聖迹傳中正式出現。
作者 | 田海
編輯 | 宮子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