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琴,東京大學地區文化研究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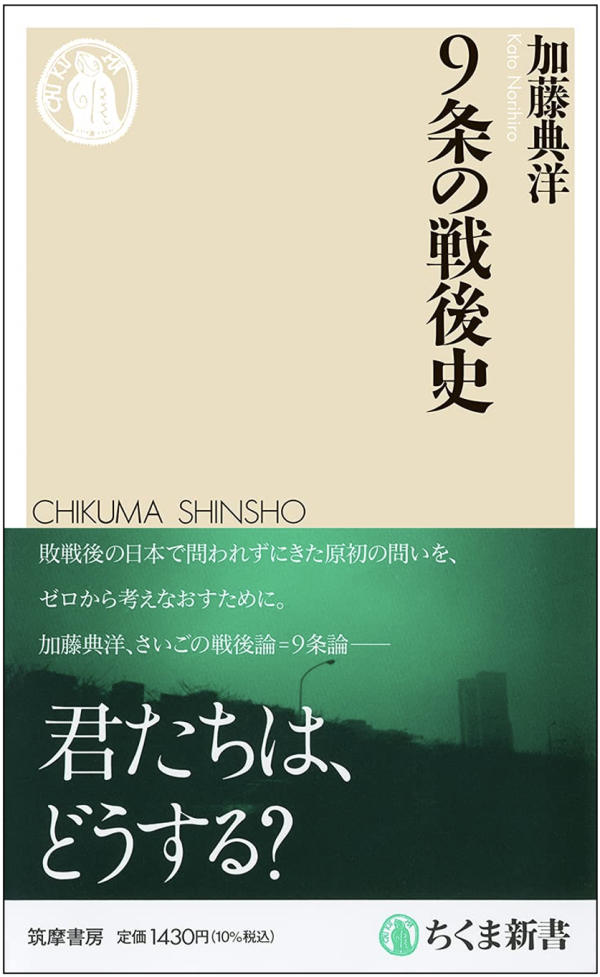
《九人的戰後史》,加藤築地著,2021年5月出版,555頁,1,430日元
近日,日本内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以"緊急"條款的建立為由,發表了"新冠肺炎災難是修改憲法的好時機"的驚人言論;就日本社會而言,一方面,人們早已厭倦了"修憲"與"憲法保護"之間曠日持久的争論,另一方面,圍繞戰後憲法的學術界和批判界是一種不斷的、不同的解釋——幾乎所有的解釋都會聲稱已經超越了傳統的"修憲""憲法保護"辯論。這種情況的客觀結果是,雖然"修憲"仍然是一個有争議的話題,但它也越來越與條款的解釋和思想的贊美聯系在一起。
在上述背景下,幾十年來,一直孜孜不倦地思考戰後日美關系的評論家加藤,無疑與他的手稿《戰後九部史》("九部戰後史"築地,2021年)的編纂和出版有着現實的相關性。這本500頁的書是在他的前一本書"九個介紹"("九個條目"創世紀,2019年)中對日本戰後憲法的全景回顧,該書以全景方式回顧了1950年代。日美之間圍繞日本憲法,特别是第9條放棄武力條款和日美之間的一系列曲折博弈。保障條約,揭示了不同時期"修憲"和"憲法保護"辯論背後的政治趨勢和意圖。可以說,這是一本具有近年來清遠原意的重要書籍,有助于我們了解日本現政府修改憲法的思想和曆史立場,進而打破了分别貼上"修憲"和"憲法保護"标簽的口号式了解。
加藤的《九條介紹》
加藤首先指出,在憲法制定時,對"九條"的主導了解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按照麥克阿瑟的思路,"九條"是先進政治思想的展現,另一種是美國日本特使的繼任者杜勒斯,認為"九條"包含着日本的"無能為力", 阻止日本走向蘇聯共産主義。兩者都是"在與整個國際社會決裂的前提下确立的極端九種解釋"(25頁)。相反,為了把握日本政府和不同時期意識形态圈子對"九"解讀背後的意圖,進而正确了解目前"修憲"和"憲政"的立場和前景,我們必須回到具體的曆史舞台上來。
當然,在回顧戰後"九國"曆史時,首先要提及的曆史事件是1951年日美"單方面和解",即在沒有蘇聯和中國的情況下與美國簽署的《舊金山和平條約》。衆所周知,雖然以日本簽署這一和平條約的形式可以擺脫GHQ(日本盟軍總司令部)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但在實質意義上,每個人都知道日本仍然從屬于美國;針對吉田政府的親美态度和反對修憲的态度,鸠山一郎的後政府試圖扭轉日本對美國的依附,使憲法"九條"的維持和修改成為一個重大的争議性問題。是以,1950年代出現的"憲法修正案",無論是1954年自由黨提出的"憲法調查",還是該黨主席匡葵在同一時期提出的憲法修正,都是為了強調戰後憲法對美國的"強加"色彩,目的是通過修改憲法來尋求日本脫離對美國的依附的可能性。加藤特别指出,1955年的《日美共同防禦條約(審判)》并非旨在"複活戰前的軍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而是将日本從美國的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第75頁);但事實是,1955年标志着保守黨合并(又稱"保守派契約")的自由民主黨及其推動的修憲法案,最終并沒有得到日本人民的支援,以至于修憲勢力和憲法保護勢力形成了"三分之二"的對抗,一直持續到冷戰結束的"三分之一"對抗。加藤評論說,"這一時期的第一位憲政家,即沒有充分體驗到占領恥辱的政治複出群體所缺乏的",是"必要的意識,準備和意識",這将"明确區分"美國獨立和恢複戰前民族主義(第75頁)。換言之,正是因為1950年代的憲政主義者一直把日本和美國作為兩個現代民族國家幾乎完全排他性的關系上,才沒有看到在沒有民族國家作為基礎的情況下尋求日本獨立的可能性,而是(例如)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聯盟的基礎上, 如此之多,以至于他們關于民族獨立的話語以及關于憲法修正案和重新軍備的話語作為先決條件或手段,很容易被回收成戰前民族主義甚至軍國主義的詞彙。(當然,加藤也看到,在同一時期,石黑一雄曾提出要通過反對"非武裝中立"的再武裝和憲法修正案來尋求超越基于民族國家的民族獨立的道路;然而,或者為什麼,石黑強調憲法應該暫時"當機",直到聯合國充分履行其職能, 聲稱我們會看到與加藤自己的"答案"有一些相似之處。)
是以,在憲法修正案失敗之後,換句話說,通過修正案實作國家獨立的嘗試失敗了,保守黨的美國獨立計劃失去了其可操作的現實。這種情況的結果是,一方面,"修憲論"中作為可能性存在的民族主義,甚至戰前的民族主義色彩越來越強烈,催生了脫離現實、被極端意識形态拖延的"修憲論",或許沖突的是,公衆對"修憲"背後可能性的警惕,挫敗了政府修改憲法的企圖。 在1955年,也導緻了他們所擔心的民族主義"憲法修正案"的興起;先前一體化的獨立化和民主化逐漸開始分裂和反對強調戰前價值觀(獨立)和戰後價值觀(民主化)的兩種傾向(157頁)。
然而,加藤提醒我們,在1955年修改憲法的失敗嘗試中,值得強調的是,到目前為止,"憲法修正與外國軍隊的撤出形成了直接關系"。從邏輯上講,第一項憲法修正案與目前的憲法修正案相反,在憲法修正案中,憲法修正與自衛隊對外國軍隊的軍事援助(行使集體自衛權)有關。也就是說,從保守契約時期的自民黨憲政改革理論、再軍備理論來看,自民黨的憲政改革理論現在的動機恰恰相反——後者的動機是:響應美國的要求,以成為美國世界戰略的頂端,試圖修改憲法和重新武裝。"從這個意義上說,1950年代修憲和重新武裝的目的,也是一種'手段',與今天的自民黨相反;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在較長的描述這種颠倒的曆史背景之前,加藤首先回顧了1960年左右發生的"安全鬥争"以及這場運動對日美關系的重要性。關系。如前所述,1955年鸠山政權的憲法修正案以失敗告終,是以對"獨立于美國"的要求和對"民主"的要求演變成兩種不同的方向或選擇。"從'民有憲政感'出發,逐漸确立了'保證民主化、和平主義,即使不獨立'的信條,修憲綱領形成了'反發展',因為獨立是修憲的最高優先,要進行修憲和修憲,在此基礎上讨論民主化與和平主義。丸山認為,安全鬥争是最大化和爆發這種"敗類"的機會。"'安全鬥争'(第151頁)可以說是戰後"九國"曆史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一方面,日本首相對共産主義的深深敵意,導緻他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采取親美路線,最終修改了與美國的《日美安全條約》,這一變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正式恢複了日本與美國的"平等關系",但卻是: 正如加藤當時的日本外交官西彥(Yoshihiko Nishi)所警告的那樣,這相當于向外界發出信号,即日本對美國反對蘇聯的軍事和地緣政治立場很可能導緻蘇聯甚至中國對日本的态度惡化。(加藤指出,兩年後的古巴飛彈危機可能與《安全條約》的修訂密切相關。也就是說,日本在這一時期手頭的"中和"甚至"共産主義"籌碼确實對日美關系産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可能改變了日本與美國的關系。另一方面,從參與"安全鬥争"的衆多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加藤區分了這場政治運動中的兩種不同要求:反對"安全條約",即要求美國獨立,以及"岸上下台信",即"戰前否認和民主化實作"(第206頁)。加藤指出,當預先宣布從美國獨立"安全鬥争"時,參與者并不多;無論加藤的分裂是否現實,重要的是要注意,"獨立"和"民主"的分離确實标志着196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的程序和戰後憲法的命運。
1960年6月18日,日本抗議者包圍了議會。
這是因為,1960年岸上政府垮台後,重返政壇的"老吉田"自民政權,通過實施吉田當年采取的"九部憲法為堤壩"的憲政了解,将"憲政"與"依賴美國"結合起來,進而為日本社會的非政治化和高度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對此,加藤寫道:"老吉田以自己是保守派鴿派而自豪,他們奉行親美和依賴美國的路線。在大力抵制美國重新武裝要求的同時,确立了美國經濟健康增長的最高優先地位,确立了新的憲法立場,即滿足所謂經濟民族主義的心理需要。由此産生的日本自衛隊的"合憲性解釋"(第207-208頁)也為随後的憲法"九條"與日美的共存奠定了關鍵階段。安全關系。另一方面,這一時期出現的修憲再軍備論(自民黨鷹派)出于民族主義情緒,失去了積極的現實意義,并沒有像第一次"修憲"那樣,把修憲作為美國獨立的"手段",而是作為"獨立的象征"(第209頁)——"修憲"的"堕落"。在政經分離、社會去政治化、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民族願望"逐漸從"獨立"變為"民主化",再從"民主化"變為"享受經濟繁榮"(223頁),使大多數公民在維持憲法現狀的前提下,更願意默許自衛隊與日美安全關系的存在。在這種背景下,無論是"修憲"還是"保憲",都不能動搖日本對美國的依戀。
在"安全運動"之後,戰後憲法的下一個曆史關鍵點是美蘇冷戰的結束。加藤指出,雖然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美國有清水太郎、姜登軒等獨立思想,但在日本經濟繁榮和話語前提下,沒有得到充分回答的問題是,日本應該如何實作獨立,維護自身安全,同時又不陷入戰前民族主義,換句話說, 如何防止周邊國家對自己采取孤立主義政策。冷戰結束後,這一根本理論問題成為日本迫切的現實,因為由于蘇聯解體,日美安全條約不再具有與美國的軍事意義,而是美國作為"霸權"國家的象征意義,另一方面, 日本必須"安全","這種差異在日本方面造成了難以了解的不安,并使日本陷入了無休止的讓步"(第323頁)。換句話說,日本需要美國軍隊的存在,以對抗來自鄰國假想的軍事威脅,但從地緣政治上,也不僅僅是從日美明確的規定方面。《安全條約》是對日本安全的明确承諾,也不保證在發生實際戰争時援助的及時性。是以,日本政府今天修改憲法的意圖,與1950年代修憲的目的背道而馳,不僅不再是脫離美國獨立的手段,而是聽取美國意見的結果。
這一曆史情況也解釋了2000年日本社會出現的"憲政修正主義"。在加藤看來,為了抵消依戀美國的屈辱,以自民黨修憲草案為代表的保守派陣營逐漸開始"不必要地鼓吹戰前式的民族主義主張"(379頁),甚至重新強調戰前對人民的憲法義務。相比之下,日本逐漸表現出對亞洲國家的外交虛張聲勢和"複古主義傾向和對美國的跪拜"的結合,以及整個社會的右傾(395頁)。與此同時,刻意回避日美關系的現狀,導緻一些極右翼言論中出現了"反對日美安全條約是叛徒"的奇怪理論。從表面上看,與意識形态上的"反動"主張相比,安倍晉三政府的憲法修正案似乎"低調"——但加藤一槍指出,這表明美國在這裡的依戀沒有羞辱感。特别是在3月11日地震之後,日本社會的屈辱感日益被一種自私的排斥感所取代:"沖繩與大陸不同,不是我們;沖繩與大陸不同,不是我們;沖繩與大陸不同,不是我們;有了這個想法,就不會有"羞辱的感覺"。由此可見,美國在日本的存在已經成為一個自然的事實,民族獨立、戰後日本社會結構的扭曲,正在跟随美國也正在被遮蔽和忽視的過程中。
如果說"憲政修正主義"從1950年代到現在的曆史演變是一條曲折和堕落的軌迹,那麼,最初作為其對立面出現的戰後"憲政主義"的曆史又如何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加藤的論述中,冷戰前,"修憲"的論述反映了對現狀的更真實的思考,是以,與"修憲"的複雜性相比,加藤認為"憲政主義"的邏輯"自1960年代丸山金男時代以來幾乎沒有變化",要點有四點:
第一,作為一個開創性的法律存在,第9條和和平主義展現了通過和平思想的現代背景和二十世紀世界大戰的悲慘經曆所獲得的願望;不要再走戰争的道路了。(423-424 頁)
不過,加藤指出,自戰後憲法頒布實施以來,在"憲政"邏輯背後或公衆"憲政保護"意識背後,存在着某種"自欺欺人",即從結構上保住戰前信仰的"國家"地位,隻有以前占據這一職位的"天皇"到現在的"九"。"這種處于世界之首的帝國主義思想的'光榮'已被和平思想的'光榮'所取代,和平思想在世界之巅擁抱'放棄特殊意義上的戰争'憲法"(第449頁)。從這個意義上說,僅僅"捍衛"憲法第9條,無論是在概念上還是在原則上,都可能比那些将憲法修正案視為日本獨立"象征"的保守派更負責任。在今天的曆史背景下,即使在"憲政"那裡,"九"也越來越是一種消極的抵抗,以至于許多人認為,為了捍衛"九"不得不默許維持日美安全關系。但是,一旦上述前提被接受,"憲法保護"和"憲法修改"之間可能隻有一個紙面上的空白——例如,近年來,吉田先生在日美同盟的"現狀"背景下,通過探索最初的"意圖"(确切地說,美國人的意圖)來提出憲法修正案,以"捍衛"憲法。面對當今複雜的形勢,加藤寫道:
保守派陣營好,創新陣營好,沒有考慮過的問題是:如何在不離開美國的情況下實作戰後國際秩序和亞太各國都能接受的國家安全措施?(348頁)
在加藤看來,"九"的意義不在于其思想有多先進、高尚——沉溺于這種理想主義的悼詞,與其說是為了符合"九"在現實中的有效性和潛力,還在于思考如何在"九"基礎上探索超越日美安全關系的維護國家安全的道路。如果"九條"确實像"憲政家"所說的那樣,是當今核武器時代真正現實的安全戰略,那麼就不應該把它看成是需要妥協和讓步來捍衛的軟弱原則,更不應說是抵制日本軍國主義回歸的最後手段,而應是打破現狀的有效武器。為此,加藤認為,需要做的不僅是将"九"和《日美安全條約》分開,而且要暫時将"九"與國家對其公民進行人身保護的承諾和要求分開。
總之,面對"九條"與美國的依戀關系糾纏在一起的複雜局面,仿佛是互相前提的,加藤的回答是,日本應該回到失敗的"起源",即對日本過去的侵略戰争的懲罰,以及對日本未來的期待。具體來說,加藤認為,今天的日本自衛隊應該"重組為一支聯合國部隊,目前以契約的形式,基本上移交給美國司令部作為聯合國司令部,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中建立國土安全部隊,但這支國土安全部隊沒有安全權力"(526頁) - 也就是說, 完全圍繞聯合國重新整合日本的軍事力量,進而打破了日本對美國的依賴。正是因為在現代民族國家憲法中,上述聯合國主導的安全戰略,隻有日本戰後憲法明确規定放棄武力的原則,才能實作。"與聯合國的聯系,其他國家的信任,擺脫日美同盟的國家意願 - 将這一切結合在一起的主要軸心是憲法第9條"(第527頁)。然而,上述方案隻是紙面上的可能。在加藤看來,這種"力量"的源泉隻能是人民的意志。在讨論接近尾聲時,加藤再次提到"安全鬥争",認為1960年的全國政治運動今天仍然可以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啟發,因為那一年的事件極大地改變了美國對日本的政策和态度:
直到冷戰結束,由保守派鴿派推動的憲法保護輕裝經濟增長政策很可能是有條件的,或者說,正是由"安全"形成的"中立牌"打開了大門,日本當時可能是中立的或社會主義的(正如你從當時的檔案中可以看出的那樣, 當美國國務院和大使館将"安全鬥争"完全視為共産主義運動時)。
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不以某種方式呈現人民的意願,政治的"權力"是不安全的。表達人民意願的最一般方式是通過選舉和全國投票。(528-529 頁)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這兩個重要段落中,加藤強調了在之前的描述中被淡化或糾正的一面,即"安全鬥争"作為反對美日同盟和争取主權獨立的政治運動。也就是說,也許從主觀上講,将這場政治運動發展成為一場民族運動的機會實際上并不是一種"獨立"呼籲,而是拒絕政府試圖恢複戰前價值觀的"民主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種"錯誤識别"效果必然會通過兩國上司人以私下會談或秘密會晤的形式進行的任何會晤來實作,無論是在陽光下還是在鸠山由紀夫的光照下,曆史一再表明。在這方面,表達人民意願的"最普遍"方式,可能不取決于選舉和投票,正如加藤最後所說的那樣,而是取決于人民的另一次鬥争。
負責編輯:丁雄飛
校對:徐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