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聽音頻的朋友可移步喜馬拉雅,搜尋《通俗西藏史》,老布充滿大碴子味兒的口音,将撲面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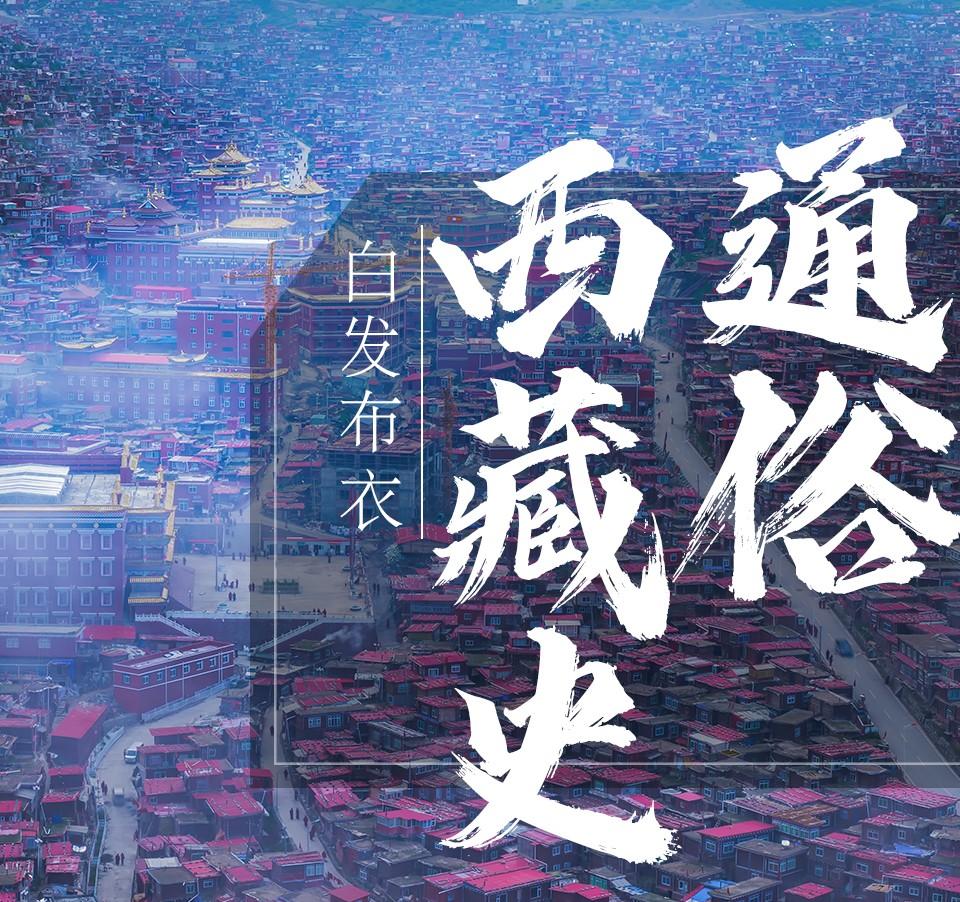
各位喜馬拉雅的小夥伴大家新年好,老布又來講德雲社版的西藏史啦!
前幾期咱們講完了文成公主,這一期咱來聊聊象雄是咋沒的。
其實咱們在前面講了兩期象雄,說實話真是講了個寂寞。
為啥呢?
因為我們現在對象雄文明,知道的實在是太少了。就像在前面節目裡說的那樣,我們不清楚象雄的疆域到底有多大,不清楚這個文明的國家形态,不清楚它的王統延續,不清楚它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清楚原始本教和雍仲本教的邏輯關系,還不清楚象雄文是不是真的存在。
也就是說,對于這個古老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我們現在還搞不太清楚。
是以,我才會在前面的節目說了這樣一個比喻,我們對象雄文明的認知,就像一串斷了的念珠。握在手裡的這幾顆珠子,根本沒法還原象雄的原貌,更不用說把它穿在一起,形成一個系統了。
但是象雄研究有意思的地方也恰恰在這裡,就是我們對它的認識很有限,但人人都知道象雄文明的影響力很大。也就是說,我們不清楚細節,但清楚宏觀,是不是很詭異。
一般來說,細節的堆砌決定宏觀的認知,而象雄的研究呢,正好相反,我們知道宏觀的影響,但不清楚細節。
造成這種詭異局面的原因在于,象雄文明的影響,在西藏仰俯皆是,到處都能看到。比如說,随處可見的煨桑、瑪尼石堆、轉山、挂經幡、跳鍋莊,以及西藏佛教裡面大量的護法神,現在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知道,這些影響來源于象雄。
同時,川西地區一直都有從阿裡遷來的傳說,最近發現的古代手抄本,也能佐證這種說法的可能性。
是以,如果你把象雄單獨放在阿裡高原上來考量,你會發現很多東西都不能自圓其說,但如果你把它放在整個亞洲的角度上來看待,就會發現它很有點文明中轉站的意味。
而這一點恰恰也是西藏文明的定位,之後不管是吐蕃王朝,還是教派政權,其實都是象雄類型的放大版,或者說是2.0版。
這就是象雄文明的特殊意義,雖然說我們依舊不清楚很多細節,但現有的證據已經能清楚地證明,它是周邊文明共同催生出的文化現象,是一個文化雜糅共生的文明。
是以,它真的不是我們想象的那麼高冷,也不像阿裡諺語說的那樣,“隻有最親近的朋友和最刻骨的仇人,才會造訪我們!”
可能在我們不知道的久遠年代裡,堅韌不拔的商人們,就已經跨越重重險阻,從中亞、西亞、東亞帶着物資和技術來到了象雄,然後再繼續向目的地跋涉,直到他們消失在漫漫風塵之中。
至于象雄的記憶為什麼會失落,這其實也不難解釋。
當象雄是一個獨立政權的時候,不管它所處之地有多荒涼,它都是中心之地,必然會有相應的記載,相應的向心力。是以,四面八方的商人來此交易,孕育出特有的宗教和文字,都是早晚的事情。
但等到它滅亡了以後,這處高原變成了一個不值得投資的邊荒之所,被漸漸遺忘也就順理成章了。
我們其實可以用古格王朝的例子,來類比象雄文明。
當古格王朝強盛的時候,它是整個阿裡地區國家聯盟的中心,是後弘期佛教的上司者和發動機。于是,我們就在古格發現了璀璨的繪畫藝術、佛像制造和佛經翻譯。這些方面的成就,都是各地文化在此交融的結果。
但等到古格王朝滅亡了以後,這處高原成了格魯派政權的邊荒之地,或者我們說的範疇更大點,阿裡成了清朝這個龐大帝國,西南邊境的最遠端。可能在某些駐藏大臣眼裡,有它沒它都影響什麼。
這種地位上的一落千丈,直接導緻古格在經濟、文化、藝術的各個領域全面衰退,成了帝國疆域上的透明人。
象雄的情況比古格還要嚴重一些,您别忘了,古格王朝就算再強大,也不可能威脅到拉薩的政權,而且從宗教層面上說,古格的教派也奉大昭寺為尊,古格國王每年都向大昭寺供奉财物,古格的國寺(托林寺)最後也改宗了格魯。
是以,你可以認為拉薩和古格這兩個政權,他們屬于全面戰略夥伴關系。
但象雄和吐蕃可不是,這哥倆之間可是赤裸裸的競争關系,是從政權到宗教全方位的競争關系。
按照《唐通典》裡對象雄的記載,這個國家“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東西千裡,勝兵八九萬。”[1]
這是啥概念,象雄的東部邊境正好頂着吐蕃王朝的軟腹部。
咱們前面說過西藏的地形特點,西藏其實是個盆地,就是這個盆地實在是有點高,但周圍那些雪山更高。不管哪個外部勢力想打進來,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皚皚的雪山。再加上,海拔太高,人人上來腦袋,都嗡嗡滴,這是西藏政權永遠不變的地利。
但從象雄打過來,可沒那麼多高山阻隔,再說了西部海拔更高,也不存在什麼高反的問題。
另外,吐蕃發迹的地方是前藏的山南,後藏地區直到囊日倫贊時期才正式并入吐蕃的版圖,而且還是瓊保邦色砍了藏蕃國王的腦袋來投奔的。
也就是說,吐蕃在後藏地區的統治是相對薄弱的,而且瓊保家族可是發源于象雄的勢力,要是一直往上倒扯,人家可是一撥的。
是以,在吐蕃贊普心裡,象雄一直都是個威脅,是個躺在卧榻之側,打呼噜的中年油膩死胖子。
再加上象雄也确實挺硬實的,在松贊幹布征服了這個地方以後,象雄人不斷掀起叛亂,硬是折騰了一百多年,直到赤松德贊時期,才算是徹底消停。
有了這些曆史背景,其實我們就能大概分析出,吐蕃統治了象雄之後,很有可能推行過強力的文化清洗。這種文化清洗,可能既包括政治層面,也包括宗教層面,畢竟盤根錯節的本教力量,對于佛教這個後來者來說,是個無論如何都要用力抹掉的記憶。
其實在西藏曆史上,宗教鬥争比比皆是,一會兒滅佛,一會兒滅本,兩邊輪着來。不過總體上來說,赤松德贊之後的西藏,本教就是個挨捶的腦袋了。
等到了佛教的後弘期,古格王朝的領袖拉喇嘛·益西沃,又把本教好頓滅,毀經卷、拆塑像、燒死本教徒,手法和滅佛一模一樣。
經過了這種長期的壓制,本教被滅到了什麼程度呢?
直到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整個阿裡地區一座本教寺院都沒有了。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古代的象雄文獻儲存不下來,其實是挺正常的。我們目前能夠看到的象雄文獻,基本都是晚期的作品,最早的也不超過八世紀。
古代記憶散失得太厲害,是很多人質疑象雄和本教的原因,也是我們不清楚細節的原因,但現在也沒啥好辦法了,隻能寄希望于考古的發現了。
咱們剛才說了象雄的種種不确定性,但有一點我們是非常确定的,這就是象雄滅亡于吐蕃人之手。
關于這段滅亡象雄的曆史,西藏還流傳着一個很有名的傳說故事。
松贊幹布即位之初的時候,吐蕃面臨一個四方動亂的局面。
這些兵火動亂之中就有象雄,古藏文史料在這地方寫的是“外戚象雄”,可見雙方之前就有姻親關系。
為了穩定住象雄勢力,松贊幹布再次使用了和親工具,他自己娶了象雄公主為妃,又把自己的妹妹薩瑪噶嫁給象雄王李彌夏。
應該說松贊幹布的政策很有效果,兩國之間的關系迅速升溫,甚至在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吐蕃攻打吐谷渾時,象雄還曾出兵相助。
但問題是兩個國家關系不賴,不代表吐蕃公主心情愉快!
在《敦煌本吐蕃文獻》裡,就記載了吐蕃公主的一條滅國之策。
據說,象雄王李彌夏不喜歡吐蕃公主薩瑪噶,而是寵愛秀格妃。結果松贊幹布的妹妹火了,“不料理内務,不生兒育女,獨居一處。”
松贊幹布知道以後,覺得妹妹老這麼鬧脾氣也不是個辦法,就派了一個大臣去規勸,臨行前還特别叮囑:“我妹妹這事兒辦得不對,長此以往,有礙朝政呀!你跟她說别這麼折騰啦,好好過日子,要為李彌夏生兒育女。”
大臣到了象雄王都瓊窿銀城以後,發現薩瑪噶根本就不在王都,而是跑到瑪旁雍錯旁邊自己過去了。
于是使臣又來到湖邊找到了薩瑪噶,薩瑪噶就問了:“我哥身體咋樣?”
大臣說:“安泰”。
然後薩瑪噶又問大臣:“你心情咋樣?!”
大臣說:“舒暢”。
完了薩瑪噶就說了,“你們倆一個安泰,一個舒暢,可我又不安泰,又不舒暢”,然後她就高歌了一曲。[2]
薩瑪噶唱的這首歌特别的長,我就不念了,你們去内容履歷裡面看原文吧!
其實您就算看原文,也不一定能看懂,老布就沒看懂!
雖然都是沒看懂,這層次還是不一樣滴,老布的層次還是要稍微高那麼一丢丢。
因為老布知道,你們為啥看不懂,這就是差距!
在西藏有種叫“德烏”的隐語,隐藏的隐,語言的語,有的是書裡也翻譯成謎語。
不過呢,在漢語語境下,謎語差不多是個專有名字了,一說就讓人想到猜謎遊戲。
是以,我感覺還是翻譯成隐語比較好。
這種隐語在西藏源遠流長,後來發展成了一種類似于中原地區“谶語”的存在,就是一語成谶的谶語。就是“大楚興陳勝王”、“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類的東西。
我以前曾經看過一篇專門研究拉薩這種童謠的文章,這次寫這篇文稿還特意找過,可惜死活沒找到。現在真是老了,好多東西看過就不記得了。
“德烏”這種隐語,很早就在西藏出現了,在衆多藏文史料裡都記載,吐蕃早期的國王以“本、仲、德烏治理天下”。[3]
這裡面“本”好了解,說的就是本教,“德烏”是隐語,剛才說了,那“仲”是啥呢?
南喀諾布先生對“仲”的定義是“曆史的叙述”,又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包括曆史寓言和傳說故事。[4]
不得不說,大學者說話就是謹慎。
老布呢,鬥膽來給解釋一下!
由于西藏的曆史記載存在文史不分家的特點,是以南喀諾布先生的定義,其實可以簡單了解成“西藏的曆史記憶”。
對于吐蕃來說呢,“本”、“德烏”和“仲”這三樣東西,還不是一起來的。
在《弟吾宗教源流》、《賢者喜宴》裡面記載,從聶赤贊普時期開始,吐蕃就已經有本教了。但“德烏”和“仲”進入吐蕃的時間,發生在是止貢贊普的兒子布德貢傑時期。
《漢藏史集》和《西藏王臣記》都記載,“王子布德貢傑在位之時,有仲和德烏輸入”。[5]
咱們之前曾經仔細地講過止貢贊普,這位被殺的贊普是西藏曆史上的一個裡程碑事件。
由此産生的影響是,吐蕃的喪葬、陵墓,禮儀等各種制度,都發生了變革。這些變革隐喻着國家管理方式的變化,仲與德烏在這個時期被引入吐蕃,可能是帶有某種象征性的意義。
其實,“仲”作為曆史記憶被運用到治理國家的層面,還算比較好了解。
這種情況大概就是大臣對贊普說,“大王啊,以前曾經咋樣咋樣啦!您應該咋樣,咋樣呀!”
這種事兒在中原王朝也常有,就是什麼“古人雲”、“子都曰過”等等等等!
但“德烏”作為一種隐語被用來管理國家,這就有點令人費解了。
不光我們費解,像意大利藏學家圖齊,這樣的大神,也一樣費解。
他在《西藏的本教》裡寫道:“我們難以解釋,謎歌為什麼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它們屬于贊普及其王國,所依賴的三種因素之一。” [6]
注意啊,圖奇在這裡将“德烏”翻譯成了“謎歌”,謎語之歌。
我們以前曾經講過,吐蕃的贊普和大臣喜歡在重大活動中唱歌,從敦煌文獻中記載的歌詞可以看出,這些歌詞裡面經常包含着隐喻。
比如說,咱們在講瓊保邦色的時候曾經說過,他曾在囊日倫贊面前唱歌顯示自己的功勞。
這段歌詞裡有這樣幾句,“孟哥之地有一虎啊,殺虎者,是我蘇孜,……藏蕃牙帳之上方啊,有白鹜在飛翔,射殺白鹜者啊,是我蘇孜。”
“孟哥之地有老虎”和“牙帳上有白鹜”很顯然是在隐喻兩件事情。很幸運的是這兩件事情,敦煌文獻裡面都有記載。
“孟哥之地的老虎”指的是瓊保邦色,砍了藏蕃小王馬爾門的腦袋來投降;“牙帳上有白鹜”指的是大臣“蒙氏溫布”對贊普不忠,瓊保邦色揭發了陰謀,“緻令贊普兄弟未受傷害”。[7]
也就是說,大臣向贊普表功的歌詞中,并不直接說出具體事件,而是用了隐喻的手法。
但問題是這種手法一般隻有當事人清楚,剛才瓊保邦色唱的這倆事兒,正好有史料記載,我們可以推測出他說是什麼。可如果沒有史料的記載,單獨拿段迷歌出來,我們就看不明白了。
我把這段歌詞的全部内容貼在内容簡介裡,你們去看看後面部分能不能看明白。
是以薩瑪嘎對松贊幹布唱的謎歌,當時的吐蕃人能聽明白,但對我們這些後輩來說,幾乎是一頭霧水。
另外還有一點,“德烏”不是僅限于歌詞,之後西藏曆史中特别盛行的降神,也應該算“德烏”的一種形式。
在教派時代,降神是個非常重要的社會活動,一旦遇到什麼重要事件,總要把神找來問問意見。以至于在格魯派的時代裡,西藏發展出了四大神巫的體系。
不過,神一般不會給個明确答複的,一般不會明确的說:“隔壁吳老二是個壞蛋!”
當然了,你也可以了解成,神的力量太大,神巫就算是半神之體,也承受不住,沒把神的意思轉達清楚。
是以,降神以後那些晦澀難懂的蔔辭,其實也是“德烏”的一種表現。
今天有關于“仲”和“德”的内容聊得有點多了,就說到這兒吧,不再往深裡講了。大家如果對這方面的内容感興趣,推薦大家看《苯教與西藏神話的起源——仲、德烏和苯》這本書,寫的人是曲傑·南卡諾布、翻譯的人是向紅茄 才讓太。
寫的人是頂級大咖,翻譯的人也是頂級大咖,是以這本書是研究這個領域最權威的作品了。
不過這本書不是很容易讀懂,反正我讀着挺費勁的,大家可是試試看。主要是這本書的叙事結構,一看就不是漢族的思維方式,讀的時候很容易走神,不太容易抓住脈絡。
但裡面的知識點真得是超級好,就算是為了豐富知識體系,也值得仔細讀一下。
今天的内容呢,有點太長了,而且特别雜亂。
我們總結一下,前半部分咱們講了象雄文獻沒儲存下來的原因。
應該說是原因之一吧,肯定還有其他原因。但這件事讓我們對象雄的細節知之甚少。
後半部分咱們用吐蕃公主的迷歌,引出了“仲”的“德烏”這兩個知識點。不過這兩個知識點内容非常龐大,足夠寫幾本書的,咱們作為假裝的專業人士,隻能聊點最基本的概念。
下一期呢,老布會結合象雄王都——瓊窿銀城的内容,來給大家仔細講一下,薩瑪嘎這美女唱的滅國之歌!
好啦這期節目就到這兒啦,感謝各位小夥伴的陪伴,如果您覺得老布講得尚能入耳,麻煩您來個訂閱,最好再轉發給您的朋友們,這是對老布的最大支援啦!
要是您不嫌麻煩,給老布這個有點另類的西藏史節目,來一個五星好評,那老布就感謝地眼淚嘩嘩滴啦!
再次感謝各位喜馬拉雅的小夥伴們,咱們下期再見!!
參考書目:
[1]、《通典·邊防卷六》_杜佑;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東西千裡,勝兵八九萬。辮發氈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物産與吐蕃同,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酋豪死,抉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髒,易以黃金鼻銀齒,以人為殉,蔔以吉辰,藏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牛羊馬以充祭。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大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2]、《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_黃布凡;
此贊普之時,對如象雄之小邦,一面聯姻結好,一面又攻打征戰。
贊蒙賽瑪爾嘎爾為國家大政嫁給象雄王李彌夏,李因原有秀格妃載婷夏,不與贊蒙同寝。贊蒙遂讓位秀格妃載婷夏,也不為李彌夏料理内務,不生兒育女,獨居一處。此事傳入兄長之耳,王兄對布吉木贊芒炯囑道:“贊蒙違背常情,照此下去,将有礙朝政,叫她不要如此下去,應為李彌夏料理内務,生兒育女。”芒宗受命,遂去了瓊隆城,恰逢贊蒙不在,去瑪浜湖玩水賞魚去了。芒炯又去了瑪浜。見贊蒙施禮後,贊蒙問道:“王兄陛下身心安泰否?”答曰:“安泰”。又問:“芒炯你心情舒暢否?”答曰:“舒暢”。随後,芒炯将王兄贊普之聖俪向贊蒙作了禀報。贊蒙說:“芒炯呵!見到你就象見到王兄贊普一樣,你是賓客,請受我一拜!”
施禮後,贊蒙歌曰:
我份内的地盤,
一座瓊窿銀堡。
四周人們都說,
外觀是懸崖峭壁,
内看是黃金珍寶。
我在懸崖之前的,
住地還不美妙嗎?
從外觀看,蒼白又崎岖!
我份内的奴隸,
古格的腳夫。
役使着不美妙嗎?
古格人熟悉了會結怨!
我份内的食物,
魚和小麥。
吃着還不美妙嗎?
——魚、麥嚼起來苦澀!
我份内的牲畜,
鹿和野驢,
馴養着還不美妙嗎?
鹿、驢性子太野!
啊!北邊的牧區上方,
有一頭公野牦牛,
如要殺死北方牧區的野牦牛,
從山谷裡發出呼喊,
派澎域董氏、東氏去幹;
從谷口打暗号,
召喚吉地之夏氏與布氏來做;
從中間射箭過來,
交與雅爾姆之洛氏與額氏。
從深谷發呼喊,
然後從中間,
射殺野牦牛。
牛頭為瓊瓦之精華,
角、筋賜給董、東,
肉、皮賞給洛、額,
内髒與牛尾分給夏、布。
在鈎子的尖兒上,
挂着虎肉,
不能向右歪斜,
不能向左傾倒。
如果向右歪斜,
細喉嚨魚鷹在期待;
如果向左傾倒,
小水獺在匍匐窺伺。
虎肉在漸漸下垂,
如果不快快取下,
明天後天以後,
水獺會來吃它;
能躍出水面的大魚,
也會跳到空中吃它。
鈎子上的東西,
可要多加注意,
多多當心!
長長的銀河,
地上的清泉,
兩處的人,眼相望聲相聞。
越來越近呵!……
向上接近天空,
天空星辰亮晶晶,
上面星辰接近山岩,
山岩星辰亮晶晶;
離都爾瓦河近了,
善躍水獺上下浮沉。
離年噶爾大地近了,
六谷金燦燦,
離墨竹、隴若近了,山風涼雕鷹。
采集黃精柏枝。
在雅姆的沙灘上,
難以行走的母馬,
應将屍體扔進吉河,
作魚監之剩食。
唱畢,芒炯起身辭别,并索取贊蒙給王兄的回信。
贊蒙說:“沒有任何書信,王兄身心安泰,我心裡高興。對贊普的囑托,我不顧喪命與處罰,定将去做。把這個呈獻于贊普手中吧!”
随後,贊蒙把一個牦牛尾巴,加上印封讓哨回去。
布吉木贊芒炯回到贊普駕前,禀報說贊蒙無任何回信,唱了一大段歌,歌詞内容是如此這般,并讓捐回這個加上封印之物。
贊普啟開印封,看見裡面有大約三十顆上好的松耳石。
他思付了一下說:“這似乎是暗示咱們,如敢打李彌夏就拿松耳石,如不敢打,就象女人一樣披上牦牛尾巴。”
君臣商議後,遂出兵滅李彌夏之國。
[3]、《弟吳宗教源流》_弟吳賢者(著),許德存(譯);
[4]、《苯教與西藏神話的起源——仲、德烏和苯》_曲傑·南喀諾布 [意]、向紅茄 才讓太(譯);
“仲”是一個古藏文詞彙,傳統上用來指兩類叙述形式。
第一類涵蓋了對古代曆史事件的全部叙述,其寓言成分和詩體般的潤色使這些曆史事件更加豐富、飽滿。一些經典範本構成了《嶺·格薩爾王》和阿古登巴、尼曲桑波,等其他傳說故事,其中一些奇妙的傳奇成分是以曆史為依據的。
第二類僅由神奇、幽默或令人驚歎的故事構成,其講述形式
令人着迷,但缺乏曆史依據,如深得藏族喜愛的《詐屍成金的故事》、《麻雀的故事》和有關其他鳥禽的寓言及猴子、野兔等動物的故事。這些深得藏族男女老少鐘愛的故事代代口耳相傳,不可避免地會在其最早的核心部分添枝加葉。僅有少數見諸文字。根據曆史經文的陳述,用于古代吐蕃治政的“仲”就屬于這兩類。
[5]、《從政治到宗教:“仲”(sgrung)與“德烏”(Idevu)的功能及演變》_劉鳳強;
《弟吾宗教源流》、《賢者喜宴》都認為從聶赤贊普開始,便有了苯、仲與德烏護持王政。這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從聶赤贊普開始,或許有苯教輔助王政,但仲與德烏則相對較晚。《雅隆尊者教法史》說,在波德貢甲時“始有寓言、謎語,苯教為朗本興波且”,《漢藏史集》載“王子波德貢甲在位之時,有仲和德烏教法産生”間,《西藏王臣記》稱“王父止貢之世,則從象雄、勃律傳入辛氏之杜本,及小王之世,修建青瓦達孜宮,輸入仲、德烏及大聖辛氏之朗苯”。以上均提到仲與德烏出現于波德貢甲時期,結合敦煌吐蕃曆史文書來看,止貢贊普因與羅阿木的一場荒唐的戰鬥而死于非命,因其砍斷了天繩而屍體留落人間,于是贊普死後沿天繩傳回天空的時代結束,藏地開始出現喪葬與陵墓,禮儀制度的變革,背後隐含着古代藏地統治方式的變化,标志着一個新的時代開端。故在波德貢甲時傳入了仲與德烏,應該是符合曆史實際情況的。
按《西藏王臣記》的記載,最初仲與德烏是與朗苯同時傳入藏地的,《土觀宗派源流》稱“朗辛有四歌贊法”問,意即朗苯教徒擅長唱贊歌歌頌神靈,這說明講故事、唱贊歌是朗苯教徒的重要特點,仲與德烏最初應是朗苯傳播和宣揚宗教的手段,是服務于宗教的。在波德貢甲時,藏地發生巨大的社會變革,統治者将朗苯引人,苯教徒則通過寓言故事、唱歌、謎語等方式維護贊普的統治,起到護持王政的作用,這也是苯教在吐蕃早期盛行的重要原因。
在仲與德烏傳入藏地初始,故事、歌謎等可能多是由苯教徒創造出來,這些故事、歌謎的寓義也都由苯教徒來闡釋。在服務于王政的同時,苯教徒又通過仲與德烏控制着王權。但随着時間的推移,仲與德烏逐漸不再是苯教徒的專有技能,而被藏地上層統治者所掌握,他們開始代替苯教徒創作、解釋仲與德烏,在這種情形下,仲、德烏與王權的關系更加密切,而且這也可能是苯教在吐蕃衰弱的原因之一。傳統藏文史書都認為,在吐蕃第二十八代贊普拉妥妥日年贊時,天降經書,是佛教傳人吐蕃之始,是以,很多史書都說在拉妥妥日年贊之前仲與德烏護政,此後以佛法護持,如《賢者喜宴》、《西藏王臣記》等均持此觀點。這當然是後世佛教徒頌揚佛法的一種說法,實際上,在松贊幹布時期仍以仲與德烏作為統治的重要方式,《漢藏史集》稱:“為了使愚昧之人也能了解佛法,松贊幹布首先教以‘仲’、‘德烏’、本波的教法”。
這裡将仲與德烏的功能由護持王政改寫成了解佛法,是後世對仲與德烏功能的有意曲解,但這則史料也透露出一個重要資訊,即松贊幹布時仲、德烏、苯教在社會中仍占據非常重要地位。
[6]、《西藏的苯教》_〔意〕圖齊,金文昌(譯);
我們更難以解釋謎歌為什麼能獲得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使它們也屬于贊普及其王國所依賴的三種因素的組成部分。
就我所知,今天再沒有謎歌師了,但與此相關的習慣卻仍在流傳。其前提就是指一種消遣時間的手段,甚至那些有文化教養的人在節日聚會和進行猜謎時也醉心于此。……許多這類猜謎活動在上層家族中也很流行。
是以,我們可以由此而得出結論認為謎歌師是一種占蔔師,在一些關鍵的時刻就使用他們,如在開始戰争行動或被認為是危險的舉動之前就要這樣作。
[7]、《隐喻與權力:藏地古代的謎歌—德烏LDEVU》_石碩;
有關這兩段唱詞,敦煌藏文寫卷P.T. 1287記:
其後,娘氏孟多熱忠貞之子尚囊,充任贊普内侍道從之官,應诏前往牙帳。
後,贊酣普君臣大酣飲宴,瓊保·邦色(蘇孜)乃于宴前對酒高
歌:
孟哥之地有一虎,殺虎者,我蘇孜也;
我把整隻老虎獻與上方,腸腸肚肚分賞予洛埃。
藏蕃牙帳之上方,白鹜在飛翔,
射殺白鹜者,蘇孜也,
将大鹜翅膀獻與上方,
羽毛賞予洛埃。
前年早于去年,
岡底斯雪山腳下,
糜鹿野馬在遊蕩,遊蕩到香波山前。
如今再來觀賞,
在香波山二年神”跟前,糜鹿野馬不要狂妄,
糜鹿野馬如果狂妄,岡底斯雪山會把你吞沒。
在去年、前年、更早之年頭,在瑪法木湖之岸旁,
白天鵝、黃鴨子在嬉戲徜徉,遊蕩來到當戈湖上,
如今再來觀賞,當戈之湖是天神之湖,
天鵝黃鴨不可狂妄,天鵝黃鴨若是狂妄,
瑪法木湖水會把你吞沒。
“彭域”成了洛埃的附邑,
攻下“彭域”的卻是“色窮”,
如今更是一望無際。
伍茹、秦瓦有如糧倉,
如今四周皆牧場,豈不是蘇孜之勳勞所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