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布蘭迪斯大學創始人、聯合編輯兼教授羅伯特·庫特納(Robert Kutner)在2020年5月19日出版的《美國展望》(American Prospect)雜志上評論道:"在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美國制造》,它分為兩部分。
(上文收到)
重振美國制造業的大模式
事實上,即使中國無意通過"中國制造2025"和"一帶一路"等涉及大規模政府投資的戰略獲得全球經濟上司地位,美國恢複其昔日的制造業力量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國的崛起隻會使美國實作這一目标的需求更加迫切。中國對國有資本的重視使該國能夠長期規劃其經濟,瞄準并緻力于上司一個又一個新技術領域,而美國過度依賴華爾街扭曲的市場信号,使該國在工業發展中處于不利地位。随着中國成為開發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提供者,這一新角色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影響正變得越來越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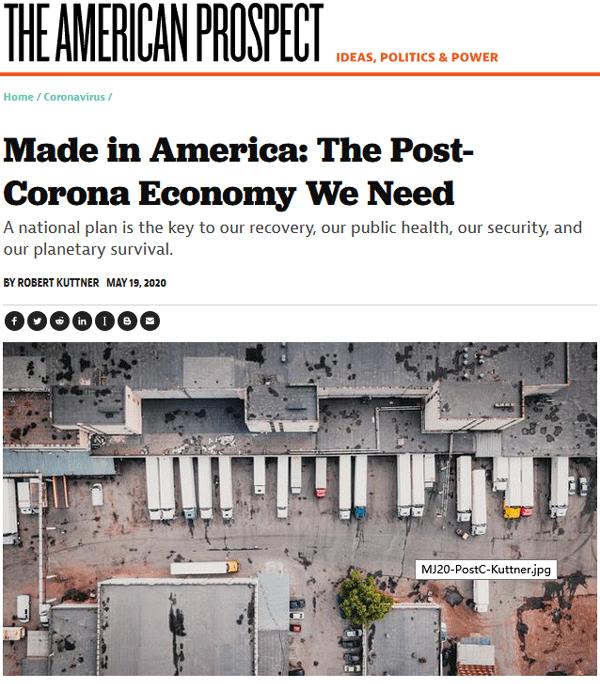
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創始人、聯合編輯兼教授羅伯特·庫特納(Robert Kutner)在2020年5月19日出版的《美國展望》(American Prospect)雜志上評論道:"在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美國制造》(Made in America),它分為兩部分。
在第一波制造業轉變之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和約翰·齊斯曼(John Zysman)于1987年合著了《制造業的重要性:對後工業經濟的誤解》(The Importance of Manufacturing: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現在看來,這本書對美國經濟的軌迹是相當可預測的。他們在書中指出,制造業不僅為社會提供了就業機會,而且大型制造業企業也可以作為區域經濟穩定器。
2020年,制造業是一個國家掌握未來先進技術的門票。畢竟,工程師們正在離生産工廠中的房間不遠的地方進行技術創新。如果美國失去機床、半導體、太陽能電池闆或電信裝置的制造能力,像中國這樣的重商主義競争對手不僅将成為制造業的主導力量,而且将成為技術創新的全球上司者。如果美國政府不幹預,美國将不再有資格與中國競争。
自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和約翰·齊斯曼(John Zissman)出版這本專著以來的幾十年裡,美國的貿易形勢已經從1975年的160億美元的适度順差增長到2019年的5780億美元的嚴重赤字。在高科技産品領域,它已從進出口的基本平衡增長到1320億美元的赤字。我們在很多行業都失去了制造技術和制造能力。在美國貿易代表面前,一些遊說團體認為,美國不應該再繼續生産尼龍襪子、婚紗,甚至印上聖經,這是最古老的西方傳統。
在後疫情時代,美國在經濟中的行動應該集中在恢複制造業力量上。正如美國國防進階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曾經在軍民兩用技術中扮演國有投資銀行的角色一樣,美國政府也應該在工業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事實上,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這樣做了。然而,這一次,美國政府的主要目标應該是阻止北京通過"中國制造2025"引領許多新興技術的發展。如果華爾街在未來繼續出賣其國家利益,美國政府應該持有高科技公司的股份,并在其董事會中安排公務員,就像重建金融公司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做的那樣。在此基礎上,從業人員代表将能夠錦上添花。
從表面上看,自由放任是一種非官方的美國意識形态,它反對建立德國西門子、中國的華為或歐洲空客等大型"國家冠軍"。但有一個無可辯駁的論點恰恰相反。波音公司已經因737 MAX的災難性管理問題而陷入困境。現在美國政府正在盡一切努力確定波音公司的償付能力,作為交換,波音公司應該允許美國政府持有該公司的控股權。波音公司是一家嚴重依賴華爾街的私營公司,它的表現非常糟糕,以至于它認為隻有在成為國有企業後才會變得更好。
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美國公司獲得了救助資金,除了回購股票和股息之外,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它。這表明"市場"不知道如何識别私營部門的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市場"在私營部門不會生效)。然而,在實踐中,美國經濟體系中并不缺乏這樣的投資機會。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迫切需要改變國有資本短缺的原因。
從管理經濟到綠色經濟
改變美國的國有資本缺口應該與基礎設施現代化以及現有經濟模式向更具彈性的循環經濟過渡齊頭并進,這兩者早就應該實作了。根據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的資料,全國基礎設施更新的資金缺口約為4.5萬億美元。2009年《2009年複蘇和再投資法案》的發起人聲稱,刺激計劃是"及時、有針對性的和暫時的",我們提出的新的綠色投資倡議應該是精心策劃的、公開的、透明的和永久性的。目前的危機使勞動力市場接近崩潰,但也為推出綠色刺激計劃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在上個世紀大蕭條期間,政府對胡佛水壩和金門大橋的推動并非漫無目的,今天我們可以将閑置資源轉化為社會所需的基礎設施。
由于稅收和公共債務可以用來為社會服務,是以利用它們來創造就業機會是有道理的。然而,根據一些貿易規則,這種做法往往被視為"非法的自身利益"。對于美國的國家複興,我們可以無視這些規則。我們可以與歐盟達成一項新的貿易協定,歐盟同意我們對混合經濟的看法。至于在人權、勞工權利和知識産權保護等問題上記錄不佳的中國,它必須接受補償性關稅和規則。例如,任何美國公司都不應遵守中國的強制性技術轉讓規則,美國公司将不再被允許這樣做。
為了在國家層面啟動公共投資并推動向經濟的綠色轉型,我們還需要将美國的經濟政策從已被證明是錯誤的經濟思維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效率是人們喜歡談論的一個詞。随着美國媒體最近關注供應鍊的脆弱性,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美國過于關注供應鍊效率,不能忽視供應鍊彈性",前世貿組織總幹事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在最近由經合組織和公開市場研究所主辦的一次會議上表示。
然而,"效率"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問題。在我1996年出版的《一切出售:市場的美德和極限》一書中,我指出,"效率"的概念可以用三種方式來解釋:第一,亞當·斯密的"效率",它基于供需概念的沖突;第二,基于供需概念的"效率";第二,基于供需概念的"效率";第二,基于供需概念的沖突;第二,基于供需概念的"效率";第二,基于供需概念的沖突;第二,基于供需概念的"效率";第二,基于供需概念的沖突;第三,熊彼特的"效率",他認為,從長遠來看,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事實上,中國在全球争奪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時完全忽視了市場價格信号,就像美國在二戰期間所做的那樣。
更進一步,對"效率"的标準描述通常沒有考慮到不正确的市場價格造成的數萬億美元的損失,就像氣候變化、1929年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一樣。"效率"所定義的人實際上是在假設官員腐敗、市場力量、經濟力量和制定規則的政治力量之間沒有回報循環。是以,人們在實際迎合"彈性"概念時,經常談論"效率"是荒謬的,與曆史事實相悖。現在是放棄這一概念的時候了。在大蕭條、凱恩斯主義革命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後,我們都認為我們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但事實并非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歐洲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表現出一種更溫和的經濟民族主義:即使馬歇爾計劃包括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美國也幾乎不會反對;但不知道美國官員何時在芝加哥式經濟學的侵蝕下失去了清醒的思維,然後在被華爾街遊說團體收購後放棄了"第三條道路",以尋找荒謬的"完美市場"。
與此同時,美國官員為相信重商主義的中國人開了綠燈,認為華爾街和美國大公司分享與中國打交道的好處沒有錯。我們必須反對這一點,戰後的社會契約應該有21世紀的現代版本,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為國家政策留出足夠的空間。
我們可能很快就會進入一個可再生電力的時代。但目前的市場價格仍然反映了太多的化石能源交易。隻有通過政府法規和補貼,我們才能将經濟從依賴化石燃料轉變為擁抱綠色能源。未來的能源不僅會更清潔,而且使用起來也會更便宜、更安全。市場經常在定價上犯錯誤,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也需要政府和民主計劃。
我們需要在國家層面制定戰略,重新獲得美國在先進制造業和綠色能源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需要強調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工業将掌握新技術,當地中小企業将發展,美國就業崗位将大幅增加。我們可以一口氣做更多的事情。當然,這可能與一些人對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傳統觀點背道而馳。事實上,我們早就應該放棄這些錯誤的想法。
(《觀察家報》的網絡翻譯可在《展望》雜志網站上找到,2020年5月19日,全文)
本文為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内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将追究法律責任。在WeChacn上關注觀察者的WeChacn,每天閱讀有趣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