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屁驚天地,一屁崩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國王在看戲,聞了這股氣,感覺很滿意。誰崩得臭,封他當教授;誰崩得響,讓他當校長……”這段荒誕诙諧的順口溜,盡管難登大雅之堂,想必不少人都在童年時期對着讨厭的人大聲唱過。而更詩意恬靜的童謠,則可能在某個月色溫柔的夜晚浮現,“月亮走我也走,我和月亮交朋友”“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南塘。”……
可随着年齡漸長,我們卻不曾想過,童謠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廣為流傳,耳熟能詳,卻帶着“屎尿屁”的順口溜能否算作童謠?“月光光夜光光”一類的字句除了朗朗上口之外,又蘊含着哪些文化内涵、帶來了怎樣的心靈慰藉?除了為兒童增加些逗趣時光,本土童謠的藝術價值究竟如何?兒時聽聞的童謠,長大後我們能想起來的有多少,明确意識到某個作品對自己精神世界建構起了重要影響的又有幾多?
兒童文學、性别與當代文學文化研究者王帥乃長期為“新京報小童書”撰寫專欄,梳理點評已有中文版的凱迪克金獎繪本。1946年的金獎繪本《公雞喔喔啼》(The Rooster Crows:A Book of American Rhymes and Jingles)是美國各地經典童謠的合集,王帥乃希望從這一繪本出發,從各個角度出發,比較美國童謠、歐洲“鵝媽媽童謠”以及中國本土童謠的差別,以反思本土童謠選集存在的問題,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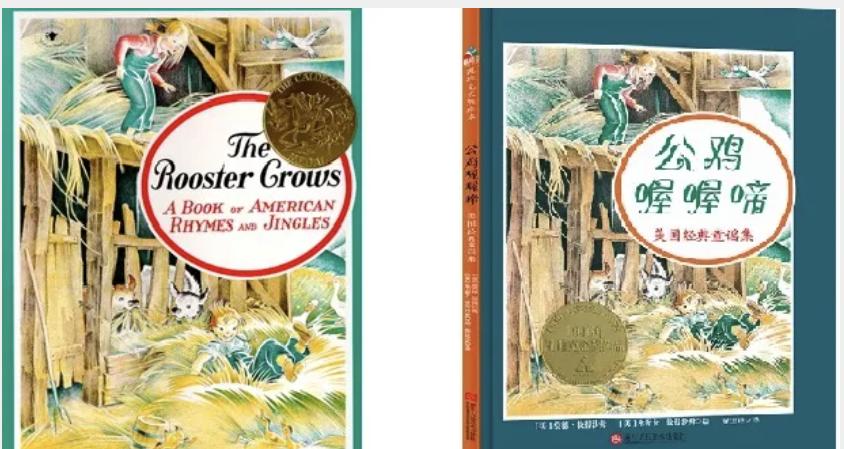
左為1945年的英文版本。右為森林魚引進的中文版。
我們傳唱的童謠是否太淺顯直白了一些?為什麼童謠中的孩子沒有姓名,他們的爺爺外婆、姑姑嫂嫂卻總頻繁出現?當童謠中的男孩子歡樂玩耍時,女孩子們怎麼總有幹不完的活兒?曾經口耳相傳的詩意童謠,如何在當下重新煥發生機?
正當年節之際,1946年這部金獎之作《公雞喔喔啼》又是童謠集,便不大想把它寫成學院派氣息過于濃郁的稿子。完成一篇從頭至尾介紹美國童謠背後人類學儀式意義或曆史淵源的文章固然不錯,卻屬這一文類批評的“正常操作”,或者我們可以不局限于這一本美國童謠,而是以此為契機在比較中讨論能為本土原創童謠選集的經典化做點什麼。
假如這個專欄(點選此處進入專欄)裡有部分文章能以閑話而“不那麼理論”的、探讨和尋問的方式完成,并可能在文章結束後還能“激發”或延續一些思考和“行動”——那麼這本收集自美國民間的老童謠一定是極佳的選擇對象——在這隆冬時節的溫暖屋内,何妨抱着擁被談天的安逸、圍爐煮茶的散漫與熱忱,對着或真實或想象的窗外大雪漫天,邀請讀者同來“講那過去(又或許從未過去)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沒有較高
群眾認可度的本土童謠集?
撰文 | 王帥乃
所謂“三國童謠”,在這裡大緻是指中、英、美三國已籍成“經典”的童謠。說是“大緻”,主要是因為雖然“鵝媽媽童謠”的成書版本最早可追溯至1760年英國書商約翰·紐伯瑞出版的《鵝媽媽的旋律或搖籃曲》(已散轶),但其異文變體卻遍布歐洲大陸。就連我們今天讨論的“起點”、美國童謠集繪本《公雞喔喔啼》中也有不少同題篇目,如《圍着玫瑰轉圈圈》《揚基歌》《傑克·霍納》《豌豆粥》《傑克和吉爾》《小瑪菲特小姐》《矮胖子達姆普蒂》,等等。
《公雞喔喔啼》英文版内頁圖。
在凱迪克金獎作品中,也有另一些頗帶民間色彩的詩歌體裁文本。但讀到《公雞喔喔啼》這樣的被稱為“美國版鵝媽媽童謠”的彙集之作時,還是很難不去聯想和困惑于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好像沒有類似的較高群眾認可度的本土童謠集,這究竟又是為什麼呢?
原創兒童文學的學術研究和民間關注長期保持着分裂狀态,對此,國内的研究同行可能已經見怪不怪了,譬如原創兒童小說在各類文體的學術研究文章中收割了半壁以上江山,但排除各類硬性或半硬性的“必讀書目”要求的影響後,大部分作品的大衆閱讀認可度相當一般;而繪本正相反,市場表現如火如荼,但在學術研究領域,即使算上國外引進繪本,相關論文的搜尋結果卻寥寥,現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教育學和心理學而非文學或美術領域;至于童謠,則是兩下裡都無甚關心。或許隻有初為父母的那幾年裡,人們才會将它們當作語音和識字訓練的工具書放進自己的購物車,過後也就不再去注意它們了。
作為兒童文學的研究者,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發現自己對于童謠這一文學體裁,特别是本土童謠,抱有許多“基底”性的困惑:除了為兒童增加些逗趣時光,目前市面上大多數本土童謠選集的藝術價值究竟如何?兒時聽聞的童謠,長大後我們能想起來的有多少,明确意識到某個作品對自己精神世界建構起了重要影響的又有幾多?如果答案是比較消極的,這是體裁本身的問題,還是編選者水準問題?假如是體裁問題,那麼幹脆安心地把童謠當作早教工具而丢掉将其作為精神彼岸之一的期許,我們是否會有些不甘和不舍?假如是編選問題,那麼想必由審美水準較好的業内人士精心制作和編選一些本子後,前述價值和影響情況會較我們這代更好一些,但什麼樣的本子才是好的童謠本子?《鵝媽媽童謠》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力如果是後一種假設為真的注腳,那麼它以及《公雞喔喔啼》這樣的本子可以在哪些方面給予我們一些參考?
這些問題,但求此文能探尋、摸索出一些答案的輪廓。
月光光,夜光光:當月亮成為感受世界的基底構成
前些天翻開朱介凡先生編選的《中國兒歌》(朱先生師承黎錦熙和顧颉剛,這本書收集了1499首遍跨各省的中國童謠,保留了各地方言,五分之一來自各地府志、縣志,五分之四為作者田野采錄,1977年在台灣出第一版,不久前大陸有了本書的簡體版。本書被視為中國童謠全面內建和研究的經典之作)時,讀到朱先生在開篇即寫“《月光光》的兒歌,是南北各地最普遍流傳的”,不覺心念一動。
《中國兒歌》,朱介凡 編著,樂府文化 | 晨光出版社 2022年1月版。
專欄的上一篇文章正巧寫的是那個要求國王父親摘月亮的公主難題(我要摘月亮——如何用父愛解答這道史上最難“考題”?),也正說了“自古以來,不分中外地,人類似乎習慣于将自己千奇百怪的無法排遣的情思都一股腦地向月亮抛擲去”:母親哄孩子睡覺唱的是“月兒明,風兒輕,樹葉兒遮窗棂”;有不得志的兄長思念弟弟時要先問“明月幾時有”;有人會在看見圓月時變身成狼釋放野性;有長辮子女孩以月亮之名守護“愛和正義”;山地民族跳月祝禱安康幸福;《酉陽雜俎》裡那顆不安的頭顱必然是飛行于月下而不是一片黑暗之中;更不用說世界影史裡那被炮彈擊中的著名的月亮之臉(世界第一部科幻電影)。
朱介凡道,初時隻以為那是春夏時節孩子們躲在戶外遊戲,月光下的世界如輕紗籠罩,童謠是為贊美月亮,後來知道它們隻是借月起興。其實,毋甯說“起興”是更進階别的贊美,隻有一種事物已然成為我們了解與感受世界的基底構成時,才會下意識地信手拈來:
月光光,夜光光,船來等,轎來扛。
一扛扛到河中心,蝦公老蟹拜觀音。
(廣東五華)
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南塘。
(台灣)
月光光,海光光,擔擔水,洗學堂。
(湖南隆回)
月亮月亮光光,牛兒吆到梁上,
梁上沒草,打到溝垴。
(甯夏中甯)
另外還有“月光堂堂”“月亮圓圓”之類的變體,以及許多諸如“月奶奶”“月亮哥”“月光公公”“月亮爺”之類的童謠起興在大江南北皆有流傳,甚至我還記得十多年前曾有部《聊齋奇女子》電視劇以“月高高,星寥寥”為片尾曲的起興開頭,其旋律、配器,加上粗犷蒼涼的男聲演繹,與《聊齋》的“月下生鬼氣、江邊繞孤魂”十分比對。到如今,劇情如何以及歌詞後文都已經忘了十之八九,唯有這一起句印象最深。
類似的還有“秋雁兩行江上雨”,這都是起筆已開氣象教“意境全出”的例子,雖然後繼乏力,再沒有超過開篇的,但能讓不少觀衆因為一個句子記住整個作品許多年,對作者也算是份光榮與慰藉。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散步詠涼天,幽人應未眠,在全人類共享的對月遐思經驗上,我們更有一份蔓延幾千年的古典美學傳統。假如有一部能成為經典的《中國童謠》,我想,其中一定要有一些像“月光光”這樣近乎“母體結構”般有力量亘穿千年永遠鮮活,并散落、融入到山南海北每個中國人肌體和神髓裡的意象與句式罷。
《中國兒歌》實拍圖。
重新定位“童謠”的範疇:以一中一西兩首童謠為例
童謠的定義到底是什麼?是否必須為民間流傳而非作家創作(哪怕文詞既簡單又有韻律,且在民間特别是孩子中間已經有一定的傳唱度)?這個問題的緣起可以一中一西兩首作品為例來講。
《布裡格斯鵝媽媽童謠金典》,[英]雷蒙德·布裡格斯 著/繪 李晖 譯,樂府文化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1年6月版。
其一是1966年獲得凱特·格林納威獎的《布裡格斯鵝媽媽童謠金典》内一首《迷失的逗号I》(為友善後文說明,在李晖原譯的基礎上有微調):
迷失的逗号I
一隻孔雀如我所見尾巴像在燃燒,
一顆熾烈的彗星如我所見落下冰雹,
一團雲朵如我所見有常春藤卷曲環繞,
一棵堅定的橡樹如我所見匍匐在地面,
一隻螞蟻如我所見吞噬一頭鲸魚,
一片狂暴的大海如我所見滿溢啤酒的泡沫,
一隻威尼斯玻璃杯如我所見十六英尺深,
一口井如我所見盛滿人們哭泣的眼淚,
他們的眼睛如我所見在一團火焰之中,
一所房子如我所見像月亮一般高又高,
太陽如我所見在午夜十二點,
看見這奇妙景象的人被我看見。
相應的英文原版:
Missing Commas I
I saw a Peacock(,) with a fiery tail,
I saw a Blazing Comet(,) drop down hail,
I saw a Cloud(,) with Ivy circled round,
I saw a sturdy Oak(,) creep on the ground,
I saw a Pismire(,) swallow up a Whale,
I saw a raging Sea(,) brim full of Ale,
I saw a Venice Glass(,) Sixteen foot deep,
I saw a well(,) full of mens tears that weep,
I saw their eyes(,) all in a flame of fire,
I saw a House(,) as big as the Moon and higher,
I saw the Sun(,) even in the midst of night,
I saw the man(,) that saw this wondrous sight.
這首詩非常有趣。我在原文中打了括号,我們先假設文中的逗号不存在并對照中文版來讀,不難發現其遣詞不俗,意象風格瑰麗,行文弄句也頗優雅,比起文風質樸的道地的民間文學,它更像是文人詩作;給它分音步後更能看到,這是一首近完美的拟英雄雙韻詩——嚴格遵照每行為五音步抑揚格的韻律,雙行對偶押尾韻,兩行換韻且全文隻間隔重複了一處,就連文風都帶着一些英雄詩般的悲情雄壯。
《布裡格斯鵝媽媽童謠金典》内頁圖。
之是以說它是“拟”,主要還是因為本詩既短又顯然帶着些怪誕和遊戲意味,與其說它是嚴肅崇高的端正史詩,不如說它更像亞曆山大·蒲柏對這一文體著名的仿拟、諷刺使用;另外,據《牛津童謠詞典》記載,這首詩最早能溯源到1665年的《卡洛琳的摘錄本》裡(除了其中一句有差異。這類摘錄本一般内容混雜,可能有文學段落、俏皮話、素描、字謎等等,主人很可能會将它們攜帶至社交場合),而最完整的版本可以溯源到1671年的《威斯敏斯特鬧劇,或宮廷和劇院最新歌曲和詩的精選集》(Westminster Drollery, or A Choice Collection Of the Newest Songs& Poems both at Court and Theatres),這是一本标注由“ a person of quality”(十七世紀時,一般指上流社會者)收集編寫的混雜型詩集。從上述對文體創作的分析和來源看,這首詩确實很有可能是當時的文人或藝術家戲仿“英雄雙行體”的遊戲佳作。
現在我們把逗号加回來再讀,也就是從一行的後半段到下一行的前半段為一句,詩義便有大不同。
“尋回的逗号”版:
一隻孔雀如我所見,
尾巴像在燃燒,一顆熾烈的彗星如我所見,
落下冰雹,一團雲朵如我所見,
有常春藤卷曲環繞,一棵堅定的橡樹如我所見,
匍匐在地面,一隻螞蟻如我所見,
吞噬一頭鲸魚,一片狂暴的大海如我所見,
滿溢啤酒的泡沫,一隻威尼斯玻璃杯如我所見,
十六英尺深,一口井如我所見,
盛滿人們哭泣的眼淚,他們的眼睛如我所見,
在一團火焰之中,一所房子如我所見,
像月亮一般高又高,太陽如我所見,
午夜十二點,看見這奇妙景象的人被我看見。
中國古代有回文詩,文人常以此炫技或遊戲,比如著名的“賞花歸去馬如飛”。上面這首《迷失的逗号 I》可以說是英文版的“疊字回文詩”,或者我們可以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那樣叫它“詭計詩”(a trick poem)。
像這樣曲折環複的詭計詩也更像是文人琢磨文字後的設計而不像是民間天然生成。然而,《威斯敏斯特鬧劇》是被歸入“民謠”書籍類的選集;19世紀的時候它已是女孩們日常文字遊戲時的“道具”;在當代,雷蒙德·伯裡格斯也将其收入了《鵝媽媽童謠金典》裡。凡此種種,似乎可以說明至少在英國,對童謠的創作者/來源身份的規定并不那麼嚴苛,隻要孩子們願意接受,即使其遣詞造句比民間口頭文學要文雅複雜一些,也完全可能被收入“鵝媽媽童謠”這樣我們一般認為是收錄“正宗民間口頭文學”的文集裡。
而這與我閱讀國内各類童謠集後的體驗非常不同。
不論是朱介凡收集的《中國兒歌》(朱介凡在序言中确實解釋過何以将書命名為“中國兒歌”而不選用“童謠”一詞,最主要的一點是他定義下的童謠重在政治性,少與兒童生活相關),抑或出版于1996年的郁甯遠從全國征集到的數千首童謠中選編的《中國童謠》,還是新近出版的較系統全面的《中國傳統童謠書系》或市場反應相對較好、各類以“老童謠”為關鍵詞命名的童謠集,編選者似乎都将目光集中在單一展現語言淺顯、文意與結構單純、方言特征較濃的短作品上。
我想,這很可能是造成我們的“童謠”難以成為深層精神給養的原因之一,一味追求淺顯直白易于了解,對淺語背後是否承載值得反刍的意蘊卻缺乏要求。我們一再說好的兒童文學是“淺語的藝術”,并非隻有“淺語”而無“藝術”。
在童謠中滲入“深層思考”、讀來顯得餘韻悠長這一點上,鵝媽媽童謠在三國作品中确實可拔得頭籌,比如《愚人鎮的聰明人》《三個快活的威爾士人》《如果願望是馬匹》(此處以及下文引用的英美童謠由于中文版翻譯的緣故,未能盡現原文的押韻,隻好請讀者諸君暫且單看文意了),等等:
如果願望是馬匹,乞丐也會騎。
如果蘿蔔是手表,我身上
也會戴一塊。
而且如果“如果”和“而且”
是各種鍋碗瓢盆,
補鍋匠就會沒活兒幹。
這首詩正着讀是表達某些超功利追求的珍稀及其實作的艱難,反着讀也可以認其為更有意思的啟示——一個乞丐也可以擁有願望并借以飛馳的世界,一個戴着蘿蔔手表而嘲諷時間刻度乃人造的世界,一個補鍋匠從補鍋中解放出來的世界,想必是個更少苦難、更多自由閑暇時光的世界吧?
回過頭來看,我們目前對童謠的認識與定位,很可能會使得一些詞句文雅又不艱澀、能給予兒童長遠的美學和哲思給養,同時還韻律優美的好作品無法納入“童謠”這一架構裡,久而久之,這一文體便成為“帶有童趣的順口溜”的代名詞。
這裡我想舉例的是以小河為代表的努力尋找和煥新老童謠的一些當代音樂人以及他們找到的作品。
2018年時,小河開啟了“尋謠計劃”,采集各地老人記憶中的童謠,從中提取他們認為值得傳遞給今天以及未來的孩子的作品,為之譜曲,并在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公園、書院、國小、四合院裡做現場音樂會,帶着前來圍觀的人們跟着老人學唱童謠。
不得不提的是《秋柳》。這首詞由杭州站活動中尋訪到的梁文海老先生提供,原是民國時期的學堂樂歌。
B站《尋謠計劃·秋柳》視訊截圖。
上世紀初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為兒童在新式學堂裡開設樂歌課教授樂理知識,從西方宗教音樂或日本歌曲集中選擇旋律優美或活潑者,填上富有中國美學意味和中國兒童生活情趣的詞,這就形成了最初的“學堂樂歌”。
我們幾代人所熟知的《送别》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由弘一法師李叔同在美國民謠《夢見家和母親》的旋律基礎上重新填詞所作。《秋柳》的詞一說為李叔同作,一說為其再傳弟子陳嘯空所作。其從詩義與詩風上來看,确實與《送别》有些“同氣連枝”的韻味:
堤邊柳,到秋天,葉亂飄
葉落盡,隻剩得,細枝條
想當日,綠陰陰,春光好
今日裡,冷清清,秋色老
風凄凄,雨凄凄
君不見,眼前景,已全非
眼前景,已全非
一思量,一回首,不勝悲。
這首詞所包含的是中國詩文傳統裡典型的“故地重遊”與“悲秋”之緒。顧随在《駝庵詩話》裡說,“秋是凄涼,應用纖細文字、聲音來寫”。長河弱柳本是常見的送别之景,到了秋季,細長柔曲似眉如眼的柳葉平添三分哀傷之情與挽留的綿綿情思。其中“亂、細、老”三字洗練老道,将無形的秋令以物之形态和動景化出,與姜夔的“君若到時秋已半,西風門巷柳蕭蕭”是同一種季節色境和人生際遇雙重意義上的悲戚與孤寂。“陰陰”與“凄凄”均有一種朦胧霧感,是春秋二季依托盛放在飄飛的楊花、撲面的淫雨裡的低哀與迷茫底色。假如當日春景尚有一些綠色的融融洩洩,那麼目下的秋風秋雨則是凄凄蒙蒙,是已然與“世事兩茫茫”的正面遭逢了。
這還是單從文字上看的格調,然而,在小河和朋友們重新配器,與孩子們再次唱響它時,這段上世紀的學堂樂歌恰如枯木破塵,霎時間有了活的和新的靈魂——鐘琴的晶瑩夢幻、童聲的稚嫩與天然樂觀是人生的天真和永葆希望,而後長号和男聲的加入則為這首學堂樂歌注入了些許悲壯感慨,這樣“天真與經驗”的重奏使得原詞從蕭瑟纖瘦的悲秋直接通向了這個民族原初的、也是更混沌渾然的詩歌面目——《采薇》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中,它成了一首會将人丢至大雪滿頭的蒼茫寂寥、“置之死地以後生”而不再停留于黃葉紛墜衰弱凄涼時刻中的歌謠。
這樣一段學堂歌謠的演唱,打動了許多人,也成為“尋謠計劃”團隊“出土與煥新”老童謠的代表作。在我看來,《秋柳》某種角度而言與前文提到的《迷失的逗号I》的性質是十分接近的——專人創作、文質兼美、且成人與孩子都樂于朗讀與傳唱,甚至連其精神與文體形式上均承載着本民族的經典詩學傳統這一點都頗為相似。它不僅讓我有了更具體的參照對象,以更進一步思索這一節開頭提出的問題,即假如我們不開始重新定位“童謠”的範疇,而仍然以目前預設的觀念編輯和創作童謠繪本,那麼我們以什麼名目和體系去安裝像《秋柳》這樣的作品并介紹給孩子們呢,是否隻能零碎地自行遇見?同時,它也給了我另一個設想。
當童謠遇上音樂,時光就像錦緞一樣鋪開
“尋謠計劃”發掘的另一些童謠如《盧溝橋》《搖搖小鈴》《四鳥歌》,也像《秋柳》一樣,傳播過程中音樂非常有效地強化了文詞的美學表現,比如《盧溝橋》:
盧溝橋,盧溝河,盧溝橋上走駱駝。
橋上駝鈴叮咚響,橋下蘆花一片白。
盧溝橋,盧溝河,盧溝橋上獅子多。
橋上獅子數不清,橋下蘆花一片白。
音樂突出了原詞中最美的末句,使作品蓦地有了曲終奏雅、由謠入詩的意外之喜,童謠的意境得到了提升。
這使我想起去歲冬季偶然讀到的一個“音樂劇繪本”《多傑》,它用童謠的形式寫出了藏族男孩的生活日常和藏族文化獨特的美學——譬如對太陽、泥土、牛羊飽含着一種泛靈論式的親近。鮮見的畫風讓人印象深刻,而最特别的則是許多頁面中都巧妙地埋藏着這些童謠演唱版的二維碼,讀者可以聽到藏族孩子的聲音從畫面深處傳來。
繪本藝術的包容性極強,就像《讓我們把故事說得更好》裡提到的,有些繪本已經可以通過掃描内頁将頁面上的二維内容以三維立體動畫的方式展現在電子産品中,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在某些适宜的作品中邀請音樂加入呢?
借用現代科技,帶給孩子更多元的藝術體驗,也豐富我們對童謠這一文學體裁的認知。如果繪本是文字×圖畫×書籍設計的綜合藝術,或者我們也可以把有些童謠當作“綜合藝術”來創造,當加上旋律,配好樂器,找到合适的歌者,這些童謠會像一個小魔盒忽然打開,時光就像錦緞一樣飄出來繞着我們的周身鋪開,那麼這些本子,就像小河說的,不是過去的歌曲,是老去之人的記憶。
本土童謠裡的孩子總是生活在一大串“親眷關系網”中
不論是《公雞喔喔啼》還是鵝媽媽童謠,讀者總能遇見一個又一個有名字的兒童形象:躺在那兒賴床的小姑娘瑪麗,去高山上打水結果滾下山的傑克和吉爾,藏在鍋底下的是安妮,剪頭發的是強尼,小瑪菲特小姐永遠坐在闆凳上吃奶酪,躲在牆角吃派的則是另一個傑克——有名有姓的傑克·霍納,而中國童謠讀本内不大容易看到孩子的“名字”。給一個人物命名會産生意義,那是一種“關系”的建立,虛拟人物一旦有了名字,讀者就從茫茫世界模糊的衆面目中将他認領了出來,我們的目光會始終跟着這個名字走,他将是一個更具體可感的人,其輪廓更清晰,生命也更鮮活。
與看不見的名字相應的,本土童謠裡具體孩子的形象不多,往往是以泛指的形式融入叙事的背景闆。而在非繪本版的童謠套書裡,現代兒童本位觀所倡導的兒童/童年作為獨立的生命階段這一點則被侵蝕得更嚴重些,兒童屬于“個人自我”的精神世界表現嚴重不足,孩子總是生活在一大串“親眷關系網”中——爺爺奶奶舅舅外婆爸爸媽媽姐姐妹妹高頻出現,哥哥永遠要苦于沒有充裕的錢娶妻子,是以小娃娃摘一隻南瓜或一隻蓮藕都會被奶奶評價為“好小子,剃頭打辮尋嫂子”;姐姐妹妹的心靈手巧最後也總是逃不脫落腳到“嫁人”一事上。
《公雞喔喔啼》中的兒童似乎更享受獨立的遊戲,叙事裡基本上隻有兒童主人公,或者拟兒童的動物,叙述者常常就是孩子自己。叙事基本上圍繞着兒童遊戲展開,例如“我要去華盛頓太太家,美美喝上一杯茶。還有五塊姜餅可以吃,要不我也帶上你?”“我有一條狗,名字叫棍棍。棍棍最愛幹什麼?躺在地上滾啊滾。”他們向往出門看世界或淘氣,卻較少受到懲罰,即使有,也僅限于口頭警告而威力有限:“媽媽我想去遊泳,乖女兒,沒問題!衣服帽子挂樹枝,千萬别把腳弄濕”“馬爸爸,釘馬掌,馬媽媽,也釘上。小馬寶寶不用釘,光着腳丫跑不停。”
前面說過,相比鵝媽媽童謠,美國童謠集《公雞喔喔啼》的美學水準并不驚豔、缺少可供長久咀嚼的餘韻,但在表現對兒童意志的尊重和平等對話這些方面,還是過關了。
回過頭看本土童謠選集裡的中國孩子,太勞苦、也太頻繁被教訓了些。比如懶漢被警告“白飯吃不成,隻好苦一生”,導讀追加道“這首童謠對懶漢進行了善意的嘲諷,提醒人們要做好每一件事”;比如“我給奶奶嗑瓜子,奶奶嫌我嗑得髒;我給奶奶煮面湯,奶奶嫌我煮得硬;我給奶奶蒸米飯,大米飯,蒸得好,奶奶誇我孝順小兒”;又比如被選入幾個童謠集的《小五兒小六兒》中,主人公淘完氣回家喝湯太急被燙了嘴,在《公雞喔喔啼》和《鵝媽媽童謠》中恰好有一則類似題目的,則言道“有人喜歡豆粥燙,有人喜歡豆粥涼。有人把它鍋裡放,九天九夜不嫌長”,兩下裡對比,其中的導向差異便顯得愈加微妙,而中國老童謠繪本的導讀仿佛害怕讀者不能領會詩中的教育之心,又追加了一句:“通過他倆的教訓,兒童會懂得爬高、喝熱湯之類的事是有危險的”。
嗚呼,中國兒童何其辛苦、何其嬌嫩也!
再以接力社的整套《中國傳統童謠書系》為例,其中囊括了很多舊年間兒童幹活或是提示兒童應盡早學會幹活、進入生産狀态的内容,比如《一母同胞姐妹仨》,一開始是“一母同胞姊妹仨。大姐學繡鴛鴦枕,二姐學繡牡丹花。剩下三姐沒啥學,挎起竹籃去種瓜”,幾個姑娘的生活被“生産任務”安排得明明白白,中間加了一段順口溜,最後寫“鋼刀下去切兩瓣,黑籽紅瓤甜沙沙。男子吃了會種地,閨女吃了會紮花”,又如“一歲嬌,二歲嬌,三歲撿柴爹娘燒,四歲學織績,五歲學耕布,六歲學繡花”。能看得出來,這類書寫的根源正是當時的兒童仍被作為成人的預備役來看待,并不是如今我們更認可的将童年當作一個獨立的生命階段來尊重,并重視這一階段所不可替代的珍貴價值。
同時,本土童謠集裡似乎有更多的家長制秩序展現和兒童受懲結局,比如《小巴狗》“小巴狗,上南山。拾大米,撈幹飯。爹一碗,娘一碗,氣得巴狗白瞪眼”,再如《賣糖的》:
賣糖的,瞎铛铛。
什麼糖?官顯糖。
給我一個我嘗嘗。
我上家裡拿錢去,
我娘打了我一巴掌。
賣糖的,你走吧,
我娘出來沒好話。
這套書在内容簡介裡說“旨在為兒童提供朗誦和閱讀的優秀文本,為家長提供兒童啟蒙教育的必備材料,為教師提供兒童語言教學的參考,為研究者和創作者提供有價值的研究資料”,但是看起來其内容表現并不切合前三條推薦用途。兒童觀與童年觀的表現,考驗着我們的童謠編選者的功底,這一條是現代兒童文學從業者應時刻提醒自己的專業底線,而童謠編選的挑戰卻不止這一點。
本土童謠裡的女童更多地與勞動生産關聯
性别觀是逃不掉的一節。
前面已經提到本土童謠裡的孩子總是被配置設定到更多生産任務、被期待盡早成為為家庭做貢獻的勞力,而這其中女童比男童更多地被與勞動生産關聯到一起,以《中國傳統童謠書系·童趣歌》為例,其中書寫兒童勞動篇目的男女性别比為11:37(如果以人物數量統計,比例更為懸殊);婚嫁歌裡多有鼓勵女性心靈手巧,最後卻将“技能優秀”歸宿于“找個好夫婿”上。
特别典型的性别不平等文本比如《喝完了湯都來玩兒》:
東家的孩兒,
西家的孩兒,
喝完了湯都來玩兒!
東家的妮兒,
西家的妮兒,
喝完了湯都來納鞋底!
上面這首童謠裡對性别的雙重标準無須贅述了。在姐妹叙事中,民間文學裡常見的樹立兩個女性之間的對比與敵意也有所展現,比如這首《棠梨樹》:
……
大姐睡的金子床,
二姐睡的銀子床,
隻有三姐沒處睡,
一睡睡個破籮筐。
大姐抱的金娃娃,
二姐抱的銀娃娃,
隻有三姐沒啥抱,
一抱抱個氣蛤蟆,
抱過來,咯哇哇,
抱過去,咯哇哇,
開開後門摔死它。
再有一些舊時代陋習如童養媳、裹小腳之類,也被選入,這裡就不具體舉例了。傳統的性别修辭還會重點表現在另一個接下來要提到的重要題目裡,即愛情主題。
《中國兒歌》實拍圖。
本土童謠選集裡常見“會幹活的女孩嫁得好”
本土童謠選集寫到“攢錢娶媳婦”或“會幹活的女孩嫁得好”的不少見,卻極少正面談“愛情”,繪本裡則更難見愛情主題的篇目。在面向普通讀者的選集中,像《皇城根兒》這樣某種角度上勉強算反映了女性情欲需求的簡單順口溜已經甚少(但它也隻是個順口溜):
皇城根兒,
一溜門兒,
門口站着個小妞兒,
有個意思兒。
白布汗褡藍布褲子兒,
耳朵上戴着盤桓墜,
頭上梳的是大抓髻,
搽着胭脂抹着粉兒,
誰是我的小女婿兒?
童謠的叙述者是很奇妙的,這個文本既可以視為觀察者的調侃,也可以視為女孩的心理活動,但整體而言,在好不容易出現的“愛情”主題篇目裡,女孩還是相對處于一個被動的位置,即使是後一種解讀,她也始終沒有真正出聲表達。
在《公雞喔喔啼》裡有個貪睡的小丫頭瑪麗,母親怎麼叫都不肯起床,直到一句“給你一個小夥子,臉頰紅潤真帥氣”,瑪麗立刻就回答:“好的,媽媽,我起床。我起床,我起床。好的,媽媽,我起床。現在馬上就起床。”
插畫者彼得沙姆将瑪麗畫為小女孩,很可能是對詩中“重複”這一修辭更像是賭氣撒嬌的小姑娘而非少女的揣測,文字和畫面的組合讓讀者忍俊不禁。相比較而言,從床上彈起來看帥小夥的小女孩雖也扮演了一個逗趣的角色,卻占據了一個主動得多的性别位置。以天真的形象和口吻道出人類天性,一派自然并不可怕,這其實也是兒童文學為性别和性教育的早期引入打開的友善之門,我們完全對這類文體加以智慧利用,大可不必對這個主題諱莫如深。
而在另一首童謠裡,我們能看到歌者對“愛情”本身的贊美:
紅豔豔的玫瑰花,
藍盈盈的紫羅蘭。
世上最甜要數糖,
你比蜜糖還要甜。
你我愛情比金堅,
刀子斧子砍不斷。
隻要貓咪長尾巴,
我就愛你永不變。
再比如《丢手絹》這首遊戲歌,以小姑娘的口吻寫“給我戀人寫封信,把它丢在大路邊。有個男孩撿起它,放進自己兜裡面”;《小小薩麗·沃特斯》裡寫小女孩為了一個小夥子哭鼻子,歌者最後鼓勵她“振作點兒,擦幹眼淚站起來。飛到東飛到西,飛到夫妻懷抱裡”,末句的英文原文更好一些“fly to the one you love best”。也就是說,《公雞喔喔啼》裡贊美的是現代社會裡獨立個體之間的愛情,這種感情關系顯然隻與自由選擇的相愛者及其深情有關,沒有許多複雜的親戚和辛苦的活計(特别是,這些活計不是嫁妝就是聘禮,指向任務式的婚姻而不是愛情本身,例如前文提到的那一類型文,以小男孩為視角,他努力摘瓜種豆,而末了歌者會提示一樁未來的姻親關系,他将獲得一個嫂嫂,他的努力會被調侃為“好小子,剃頭打辮尋嫂子”。即使不論此處有傳統民間文學和文化裡對叔嫂戀的微諷和對已婚女性“操守”的密切注意,對婚姻之後家庭宗族關系的重視也是明顯勝過“愛情”的),而且,女性兒童在這裡是主動行為和發聲者,或者也是獲得了正向溫暖鼓勵的。
在遊戲歌對農民婚後生活的摹拟中,《公雞喔喔啼》對已經照顧好農田的主人公說的是“接下來,娶妻子,歡迎你的新娘子。打開門快請進。擁抱她,親一親。結婚之後要顧家,說話一定要算話。要善良,要和藹!别讓老婆缺了引火柴”。此處,童謠對性别權力結構的上位者提出了要求——這不禁讓我想起朱介凡在《中國兒歌》裡為“窮追不舍打老婆”的童謠辯護為“玩笑的述說,不可看實了。隻是閨房生活之樂,人不察,以為虐苦……怪的是,那妻子并未下堂求去”,朱先生是百年前生人,然而今日我們卻須知道彼時妻子不能下堂求去并非不願,實是因為無路可走,且文學諷刺與嘲谑但凡朝向弱勢者須是有悲憫打底的輕度敲打,好的文學(自然包括了諷刺與幽默文學)永遠更多地劍指勢強者,再沒有以力弱者被打得上天入地無處可躲成就流芳百世的笑話的。
而在同一頁裡,朱介凡先生采輯的一首杭州童謠倒是簡短明了又頗得中式伴侶煙火相守、含蓄情長的三味:
腳踏砻糠火,夫妻對面坐,
白酒燙一壺,鹽菜鹵兒滾豆腐。
對此,朱介凡先生評道“如果是在西湖,室外正飛着雪,那更是天堂世界了。沒有第三人,新婚,小孩還未出生”,确實不錯。雖然句句寫俗,但其實極雅,正屬“豈止無是非,甚至無美醜”的自然落成。隻這四句,一切外在時令節候、内在情衷讀者皆自能補出,中國讀者尤能深明其意。這樣的短謠算作愛情或是婚姻主題都無不可,私以為大可選入給孩子的童謠集,尚能一補本土選集裡相關主題的缺失,不知諸君以為如何?
舊習俗、舊儀式、舊崇拜
我想,編者應該留神将一些明顯違背現代科學和價值觀的舊習俗、舊儀式、舊崇拜從低幼繪本中剔除,比如“我吃飽了把書念,明年進京考狀元”,比如“扯回地菜煮雞蛋,都說延年去病靈”之類。
屎尿屁可否也能進入童謠裡?
最後是一個問題,有些童謠裡有屎尿屁,有髒話,同時卻也有诙諧、冒犯精神的根芽包含其中,而家長對此的包容度有多少?回想起自己記住的童謠裡,有不少竟是此類校園口口相傳之作,比如“××的屁驚天地,一屁崩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國王在看戲,聞了這股氣,感覺很滿意。誰崩得臭封他當教授,誰崩得響讓他當校長”等等。如果我們接受它們繼續口頭流傳,是否接受其中某些進入書面系統呢?
寫到這裡,這九段錦算可以告一段落了,這篇文章斷斷續續寫了将近一星期,無非是“文學愛好者”的一點不甘心,不甘心于承認一種文體隻能被當作“工具”使用而無法成為持續的審美長進和深度思考的能量之源。
我曾經以為隻有越劇才是戲曲化《紅樓夢》的最佳體裁,哪怕同屬江南劇種的昆曲也難以超越,聽過昆曲版“寶黛初會”以後卻發現,越劇紅樓得原著之“天然一段風流态度”的真摯,而昆曲紅樓雖在戲詞上尚可推敲,卻顯原作的“夢幻、精緻與孤獨”之所長;“新文學”未降生之時,多少鴻儒耆宿認為以白話作出好文章是沒有希望的,但我們卻有了《狂人日記》《四世同堂》《呼蘭河傳》。是以,我深信沒有絕望的體裁和器皿,隻有不會寫不會作的人罷了。某種器物或體裁或許有天賦性格,但人卻能超越桎梏,使“不可能”變為可能并終成真實。而《鵝媽媽童謠》廣泛與長久的流傳也給了我更多的信心。
我想起小河尋謠的現場,因為附近有山泉之聲,當他問大家“能聽見嗎,一直有一個水聲”,孩子們紛紛說“我聽見了”“我也聽見了”,一個小女孩指着遠方回答:“我聽到大海從那邊傳過來!”
真妙啊,她不是說她聽見“那邊有大海的聲音”,她說她聽到“大海從那邊傳過來”。也許遠處真的有一片大海,巨浪洶湧,滾滾而來。
參考文獻:
[1] Opie P ,Opie I .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ursery Rhymes[M].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1951.
[2] Leslie E.The American Girls Book: Or, Occupation for Play Hours[M]. James Miller, 1865.
[3] [美]莫德·彼得沙姆,[美]米斯卡·彼得沙姆繪;徐廷廷譯. 公雞喔喔啼 美國經典童謠集[M]. 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8.
[4] [英]雷蒙德·布裡格斯;李晖譯. 布裡格斯鵝媽媽童謠金典中英雙語版[M]. 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1.
[5] 朱介凡編. 中國兒歌[M]. 昆明:晨光出版社, 1996.
[6] 郁甯遠編. 中國童謠[M]. 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 1996.
[7] 金波編. 中國傳統童謠書系全8冊[M]. 南甯:接力出版社, 2012.06.
[8] 山曼編,景紹宗繪. 老童謠[M]. 濟南:明天出版社, 2013
[9] 鄧詠秋主編. 遊戲篇 節日篇 幽默篇 最愛中華老童謠 全3冊[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2.
[10] 李叔同;餘涉編注. 李叔同詩全編[M].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5.
[11] 錢仁康. 學堂樂歌考源[M]. 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 2001.
[12] 顧随. 駝庵詩話[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撰文|王帥乃
編輯|申婵,肖舒妍
校對|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