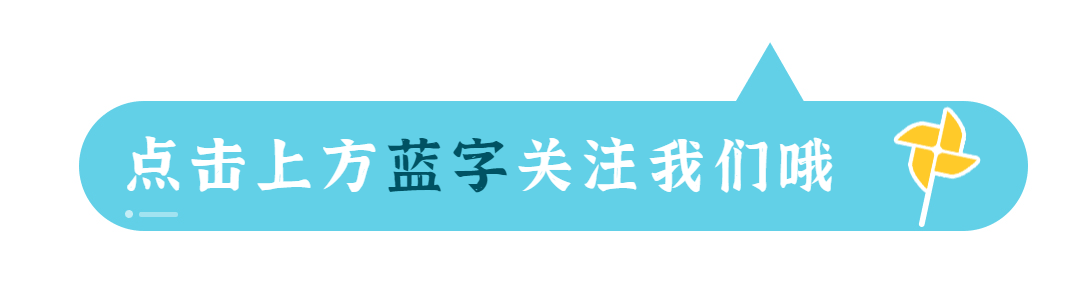
蘭陵王名為高長恭(約541年―573年),一名高孝瓘,是北齊文襄帝高澄第四子,東魏大權臣北齊創始者大丞相高歡之孫,封為蘭陵王。
身世撲朔迷離
蘭陵王的父親是北齊高祖神武皇帝高歡的長子文襄皇帝高澄,而母親卻連個姓氏也沒有,這使他的身世變得撲朔迷離。
《北齊書》中載:“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又載文襄六男中:“文敬元皇後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甯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容貌超凡脫俗
《北齊書》、《北史》中說他“貌柔心壯,音容兼美”;《蘭陵忠武王碑》中說他“風調開爽,器彩韶澈”;《舊唐書·音樂志》中說他“才武而面美”;《隋唐嘉話》中說他是“白美類婦人”。可見,蘭陵王的美确是不容置疑、超凡脫俗的。
性格與将士共之
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将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将士共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金墉解圍成名
河清三年(564年)十二月洛陽之戰時,北周攻擊洛陽一帶地區,圍城卻沒有攻下。段韶、斛律光與高長恭奉命前往救援。
段韶利用謀略打敗北周軍隊,高長恭帶了500名騎兵沖進北周的軍隊,到達被圍的金墉(現今河南洛陽東北故城)城下,因為高長恭戴着面具,城中的人不确定是敵軍或是我軍,直到高長恭把面具脫下來讓大家看到他的面貌,哪裡不平哪有蘭陵王,之後高長恭成功替金墉解圍,北周軍隊最後放棄營帳撤退。
這場戰役是高長恭最受注目的戰役。根據《北齊書》的記載,士兵們為了這場戰役而歌誦他,後來就變成知名的《蘭陵王入陣曲》。同年十二月,他被任命為尚書令。
曆封郡公
他後來曆任司州、青州與瀛州的地方首長。武平元年(570年)七月,被任命為為錄尚書事。武平二年(571年)二月擔任太尉。
同年三月,與太宰段韶、右丞相斛律光聯合進攻跷谷,抵禦北周宇文憲的攻擊。五月,段韶包圍定陽城,而北周汾州刺史楊敷堅守住城池,段韶久攻不下。
段韶病倒之後,由高長恭接替統領全軍,他成功的利用伏兵擊敗了從城中撤退的楊敷軍隊。
武平三年(572年)八月,他被任命為大司馬,武平四年(573年)四月擔任太保。他前後因各項戰功被封為巨鹿郡、長樂郡、樂平郡、高陽郡等郡公。
遭帝猜忌
在洛陽之戰後,北齊後主高緯曾問高長恭說:“這樣沖進敵陣之中,如果不小心發生意外怎麼辦?”高長恭回答說:“國事就是我們的家事,在戰場上我不會想到這個。”
後主因為他說的“家事”,又聽到士兵們唱的《蘭陵王入陣曲》,開始猜忌他會謀反。
定陽之戰時,高長恭代替段韶的職務統率軍隊,但是常常收取賄賂,累積财富,屬下尉相願問他:“您既然受到國家的委托,為什麼要如此貪心呢?”
高長恭沒有回答,尉相願繼續問:“是不是因為邙山之戰大勝,您害怕功高震主,遭受忌妒,而要作令人看不起的事情呢?”,高長恭說是的。
尉相願說:“如果朝廷真的對您有所妒忌,這件事情更容易被當成是罪名,不能避禍反而更快招來禍害。”高長恭流淚屈膝問尉相願解決的方法,尉相願說:“您之前已經立下戰功,這次依然打勝仗,聲望太大,最好之後都裝病在家,别再管國家的政事。”高長恭同意他的說法,可惜沒有辦法成功退出。
被毒身亡
武平四年(573年)五月,北齊後主高緯派遣使者徐之範送毒酒給高長恭,高長恭跟妻子鄭氏說:“我對國家如此忠心,哪裡有辜負皇帝,而要賜我毒酒?”妻子回說:“為什麼不親自當面去跟皇帝解釋呢?”高長恭說:“皇帝怎麼可能會見我?”之後就飲酒而死。妻子鄭氏則進入佛門。追贈太尉,谥号武王。
威名美譽
蘭陵王一生參加了數次戰役。其中廣為傳頌的一次就是曆史上着名的“邙山大戰”。公元564年,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黃土高原的北周對北齊發動進攻,北齊重鎮洛陽被北周十萬大軍團團圍困,北齊武成皇帝急忙調集軍隊前去解圍。
在洛陽城外,北齊援軍發動了一次次進攻,都被北周軍隊擊潰,眼看就要面臨全軍覆滅的境地。這時,受命為中軍将的蘭陵王戴着“大面”,身穿铠甲,手握利刃,率領五百精騎,奮勇殺入周軍重圍,勢如破竹,一直殺到洛陽城下。
守城的北齊軍隊被困多日,不敢貿然開門,蘭陵王摘下面胄,城上的北齊軍立即歡呼起來,打開城門,與城外大軍合兵一處,奮勇殺向周軍,周軍大敗。《北齊書》書載:“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又有史書記載:周軍“丢棄營寨,自邙山至谷水,三十裡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正是這次大捷,使得蘭陵王威名遠揚,北齊皇帝加封他為尚書令。
蘭陵王不僅骁勇善戰、屢建戰功,而且忠以事上,和以待下,在士兵和當時社會中廣有威名。北齊書記載:他“為将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将士共之”。
即使是對自己的“政敵”,他也能夠做到寬厚以待。史載,當初長恭在瀛州時,行參軍陽士深上表告發他貪贓枉法,長恭是以被免官。
等到高長恭東山再起,引兵進攻定陽時,陽士深剛好在高長恭營中聽命,是以非常害怕高長恭會借機報複殺害自己。
為此,高長恭安慰他說:“吾本無此意。”可陽士深心中仍不踏實,非要央求懲罰。高長恭隻好找了一個小過失,打了陽士深二十闆子,好讓他安下心來。
《北齊書》還記載了他一個非常“平民化”的動人細節。說一次他上朝時,跟随他的“仆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事後高長恭竟不以為意,“無所譴罰”。
北齊蘭陵王高長恭是個低調的人。
當然,他也必須低調。
雖然貴為帝王家的皇子王孫,可他的身世實在尴尬。他的父親是北齊文襄皇帝高澄,母親卻連個姓氏都沒有。
兄弟六個中,他排行老四。其中老五安德王高延宗的母親不過是“廣陽王妓也”,可正史也明确記載其姓氏為陳。由此推算,蘭陵王母親的身份和地位,恐怕連妓女也不如,後人猜測她可能隻是宮中一個地位卑下的宮女罷了。
在講究血統和門閥的時代,蘭陵王的“莫名”身份給他帶來的尴尬和壓力便可想而知。是以,他必須低調,夾着尾巴做人。
除卻身份地位外,就個人才情和社會關系而言,與其他兄弟幾個相比,蘭陵王也必須低調。老大河南王高孝瑜不但長得“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而且“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可謂才貌雙全。更重要的是,高孝瑜和九叔武成皇帝高湛一起在祖父的神武宮中長大,“同年相愛”,關系很不一般。
待高湛即位後,對高孝瑜是“禮遇特隆”,到晉陽巡幸時,還不忘遠在北齊都城邺(今河北臨漳西南)的同歲族侄,寫信告訴他:“吾飲汾清(山西名酒)二杯,勸汝于邺酌兩杯。”兩人關系如此親密,連史官都不禁要贊歎“親愛如此”。
老二廣甯王高孝珩也頗有才情,有着“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等諸多優點,特别是繪畫技能非同一般。他曾在自家大廳牆壁上畫了一隻蒼鷹,“見者皆以為真”;還畫過《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
另外,高孝珩還有着出色的行政才幹。北齊的皇帝走馬燈式地變換,可他卻一直都擔任高官要職,曆任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将軍、大司馬等要職,辛苦地支撐着北齊搖搖欲墜的高氏江山。
老三河間王高孝琬雖說才幹不如兩位兄長,可性格率真,膽識過人。當初,突厥與北周軍攻陷太原,武成帝高湛為避敵軍鋒銳,準備東撤,他拉住皇叔的馬頭不讓撤,并光着膀子出陣,誓要與敵軍死拼到底,後來北周軍敗退,他也是以被拜封為并州(今太原)刺史。
另外高孝琬還有一大心理優勢,那就是他的母親是文敬元皇後,并是以“驕矜自負”。身為差點就要做皇帝的文襄世嫡,人家驕傲也是有資本的。
老五安德王高延宗,雖說身世和蘭陵王相比也高不到哪裡去,可他“命好”,從小被二叔高洋(文宣皇帝,北齊實際第一位皇帝)收養,很受寵愛。
12歲的時候,高洋還讓他騎在肚皮上,甚至縱容到“令溺己臍中”的荒唐地步,尿完後高洋還欣然感歎道:“可憐止有此一個。”
老六漁陽王高紹信年紀太小,自不需再做比較。
蘭陵王夾在這些兄弟中間,上不得,下不來,頗有幾分“外婆不疼,舅舅不愛”的心理孤苦和地位尴尬。
如果細究蘭陵王不被疼愛、不被重視的緣故,除卻母親身份低下外,我想也與他的相貌有關。史載他長得“貌柔心壯”,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個皮膚白皙,眉清目秀,頗有“中性”之美的“花樣美男”。
可無論是與“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的祖父高歡相比,還是與“神情俊爽”的父親高澄相比,蘭陵王的長相都缺乏一種必要的“英武之氣”。
在這個崇軍尚武的皇族家庭裡,他這樣既不魁偉,又不雄毅的“小白臉”,肯定不符合皇室的審美情趣。是以,我們也就不難了解,為何他二叔偏偏喜歡“坐則仰,偃則伏”的超級大胖子高延宗了。
蘭陵王低調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可能還與他童年時遭遇父親橫死的變故有關。作為把持東魏命脈的大丞相高歡的長子,他的父親高澄從小就得到政務上的曆練,16歲時任京畿大都督,入輔朝政,加上其“器識不凡,機略嚴明”的才華,很短時間内就使得“朝野振肅”。
29歲時,他更是以大将軍身份兼相國,封齊王,并加殊禮,即“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可謂登至人臣的最高位置了。可年少得志、野心勃勃的高澄并不滿足,把控軍政大權的他早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也是以根本不把東魏的孝靜皇帝放在眼裡。
有一次,他不懷好意地拿了一大杯酒,強行給孝靜皇帝勸酒。孝靜不高興地說:“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高澄一聽大怒,大聲喝道:“什麼朕!朕!狗腳朕!”罵完竟還讓身邊的侍臣崔季舒打了皇帝三拳,然後“奮衣而出”。
這還不算完,事後高澄讓崔季舒“入謝”,孝靜覺得惹不起,隻好忍氣吞聲賜其彩帛。那麼賜多少呢?崔季舒還得請示高澄,高澄說那就取一段吧。
孝靜給了400匹,可高澄還說:“亦一段耳。”由此觀之,高澄是那種“得勢不饒人”、飛揚跋扈的主兒。
這種太過“高調”的自負性格,也讓高澄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一日,他與幾位心腹在城北東柏堂裡密謀如何受禅當皇帝時,一個叫蘭京的廚子奉命進食,高澄也不知為何看他不順眼,就順口對身邊人說道:“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卻。”蘭京可不是一般的奴才,他是梁國将軍蘭欽的兒子,因戰争為東魏所虜。蘭欽想用錢财贖之,可高澄不許。
可能在他看來,他要的就是一種勝利者的驕傲感,想看的也是失敗者的屈辱相。是以蘭京求請好多次,高澄都不準許,後來還打了蘭京一頓,并威脅他“更訴當殺爾”。
此次高澄的指令,使得絕望的蘭京不得不铤而走險,他集合六名同黨闖進堂裡,将高澄刺殺。對于這一蹊跷的刺殺事件,因為太多的巧合而令後人一直存疑。
譬如在事發前幾日,城裡就有童謠四處流傳:“百尺高竿竿折,水底燃燈燈滅(澄字的拆解會意)。”另外,還有侍臣崔季舒在諸大臣于北宮門外等候上朝時,竟無緣無故哭誦鮑明遠詩句:“将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
是以,高澄的死,最大的可能是緣于一場蓄謀已久、計劃缜密的政治謀殺。那些看似迷信的謠言,恐怕隻是政敵精心籌劃的心理戰罷了。
父親的橫死,對蘭陵王的性格形成和處世态度的影響是深遠和巨大的。無論做人,還是處事,若太過張揚、太過高調、太不把别人放在眼裡時,都有可能讓自己随時陷入“絕地”。
由于身份特殊,估計也嘗盡世态冷暖炎涼,是以蘭陵王很懂得體諒别人,正因如此他将軍做得不像将軍,王子也當得不像王子。
史載他“為将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将士共之”。這說明他是那種能與将士同甘共苦的“親民型”皇家幹部,并且蘭陵王的寬厚仁義,絕非隻是擺擺樣子。
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他對“政敵”的态度。當初他在瀛州(今河北河間)時,行參軍陽士深上表告發他貪贓枉法,他也是以被免官。
等到他東山再起,引兵進攻定陽時,陽士深剛好在他的軍營中,是以很害怕蘭陵王會借機殺了自己。但蘭陵王卻為此安慰他說:“吾本無此意。”可陽士深心裡還是不踏實,央求懲罰,蘭陵王隻好找了一個小過失,打了陽士深20闆子,好讓他安下心來。
《北齊書》還記載了一個關于蘭陵王很“平民化”的動人細節。說是有一次他上朝時,跟随他的“仆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事後蘭陵王竟不以為意,“無所譴罰”。
由此觀之,他平常對待下人,也一定是非常寬厚仁慈的;要不,奴仆是不會有這麼大的膽,敢把他這樣的王子不放在眼裡。
在君臣有别、等級森嚴的封建王朝,特别是北齊那樣“不把人當人”、動辄砍頭的瘋狂時代,蘭陵王溫情和寬容的一面,煥發出溫暖的“人性”光輝,更顯得難能可貴。
曆史評價
究其蘭陵王的一生,談不上波瀾壯闊,也算不得精彩傳奇。史書上僅以四百多字的傳記,略述他的生平。千百年後,當我們想竭力了解他時,卻發現他的曆史面貌如此模糊,隻能在與同時代的人物對照中,隐性發掘他的事迹。
如今,在河北磁縣城南5公裡的劉莊村東,還可以看到他的墓碑,上有“齊故假黃钺太師太尉公蘭陵忠武王碑”篆書字樣。有趣的是,在民間的記憶中,蘭陵王的形象卻是出奇的鮮活。
其中傳說最多的就是這位英俊的王子因為太過俊美,是以每次沖鋒陷陣時,都會帶上一副铮獰的鐵面具。
這個傳說固然生動,可在正史中找不到足夠的證據。如果他真和北宋時被稱作“狄天使”的狄青将軍一樣,“臨敵被發、帶銅面具”,有如此出采的将軍風姿,嚴謹而細心的史官是不會不做記錄的。
譬如《北齊書》裡就曾記載,在蘭陵王的祖父高歡時代,敵方的将軍蔡佑穿了一套新式的“明光鐵铠”(其式樣可參看高洋墓裡的持盾陶俑)而被稱作“鐵猛獸”的動人細節。
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早在唐朝時這個傳說就已經定型。崔令欽在《教坊記》裡記述“代面”(又稱大面)戲起源北齊時,就捎帶記載:“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威敵,乃刻木為假面,臨陣着之。”
而在段安節《樂府雜錄》裡,進一步演繹“以其顔貌無畏,每入陣即着面具,後乃百戰百勝。”隻可惜把蘭陵王誤記為“神武弟(應是神武孫)”。
由此觀之,搞藝術的并不在乎曆史的真僞。反倒是善意的想象和不太離譜的傳奇,反而能為藝術增添動人的色彩。
在正史裡提及此事時,隻是提及邙山大捷後,“武士共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鮮卑族本就能歌善舞,蘭陵王又是“音容兼美”,音樂造諧頗高,是以帳下的軍士填詞譜曲,作《蘭陵王入陣曲》,一來可作頌歌敬獻上司,二來可作軍歌鼓舞士氣,也自在情理之中。
不過,後來與面具扯上關系,由簡單的歌謠轉變為壯美的舞曲,再升華成華麗戲曲,倒是與軍士無關,而是與北齊發達的俳優文化有關。
同樣流淌着鮮卑族血液的唐朝,後來完全繼承了北齊的俳優文化。其中,以創立教坊的唐玄宗最為癡迷,貢獻也最為突出。《舊唐書?音樂志》稱:“歌舞戲有《大面》、《缽頭》、《踏謠娘》、《窟壘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于禁中以處之。”也就是說,這些多是緣自北齊的歌舞戲,“戲弄”的娛樂色彩太重,無法當作正統的雅樂、宴樂、法樂等“正聲”,可唐玄宗又是喜歡不得了,那就幹脆設個教坊,專心用來表演散樂百戲。
在豔麗的脂粉香氣中,被徹底娛樂化的《蘭陵王入陣曲》也漸漸褪去武曲的本色,漸變為“軟舞”。到了南宋時期,又演變為樂府曲牌名。按王灼《碧雞漫志》的說法,已經“殊非舊曲”,早與悲壯激烈的戰場節奏無關了。
幸運的是,唐時傳入日本的《蘭陵王入陣曲》倒是保留了幾份真實的原貌。和唐玄宗一樣,日本人也非常喜愛蘭陵舞曲,而且要寬容得多,引入日本後,視為正統的雅樂。
另外,由于對于引入的盛唐藝術非常敬仰,也格外珍視,日本對其保留和傳承,有着一套十分嚴格的“襲名”與“秘傳”制度,我們也有幸在千年之後,還能欣賞到原汁原味、壯懷激烈的蘭陵舞曲。
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992年,時值《蘭陵王入陣曲》誕生1428周年,日本雅樂團通路磁縣,到蘭陵王墓地參拜、供奉演出了着名的《蘭陵王入陣曲》。除卻穆重的音樂和精美的服飾外,最吸引人的便是那張頭頂飾有辟邪神獸,高鼻深目,表情兇狠的華麗面具了。
當然,這一切可能都與蘭陵王無關。可善良的人們,還是情願相信這位悲情的英俊王子,曾經就是戴着這樣華麗的面具沖鋒陷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