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高爾基對十月革命後時局與社會洞察深刻,對以“革命”名義作惡表示的強烈義憤,對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與思想自由抱有執着信念;十年之後他從海外歸來,一頭紮進了贊美斯大林體制的大合唱隊列中。回國後不久便上司寫作了“俄國文學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頌揚奴隸勞動的那本可恥書籍”(索爾仁尼琴語)——《斯大林白波運河修建史》。
文/金雁
手頭這本高爾基文集《不合時宜的思想》使我困惑不解。從曆史學的角度我對高爾基及他那一代俄國知識分子的“艱難曆程”已有所了解,而且在閱讀之前我已知道在本書中我會讀到一個“人道主義的高爾基”,甚至可能還是一個“自由主義的高爾基”,他既不同于此前那個“無産階級的海燕”,也不同于此後那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禦用大師。
但我真的開始細讀本書時,我仍困惑了。我驚歎于作者對十月革命後時局與社會的深刻洞察,對以“革命”名義作惡表示的強烈義憤,對民主理念的了解與堅持,對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與思想自由的執着信念,對俄國人國民性的陰暗面及其在革命中的表現的尖銳評論與那些不幸而言中的預見。當然,對這一時期他不顧個人安危而挺身救助那些政治落難者的行為,對于他在布爾什維克驅散立憲會議之時發出的“來複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的嚴正抗議,就更是令人感到震撼了。
正是由于他如此“不合時宜”,以緻最後他不得不走上出國漂泊之路。到這時為止,這個高爾基還是我們讀得懂的,這個高爾基甚至與“無産階級的海燕”也不沖突——因為“海燕”在當年那個時代也是“不合時宜”的叛逆者,而同情弱者、維護正義、伸張人性、抗議強權等等“不合時宜的思想”也合乎邏輯地可以成為“海燕”的靈魂。畢竟,“海燕”也好,“不合時宜者”也好,都是在扮演社會批判者或“異見分子”的角色,都在充當社會的心靈與頭腦、人類的良知與理性之象征,都是俄國傳統所謂“知識分子”的典型品格。
然而十年之後他從海外歸來,一頭紮進了贊美斯大林體制的大合唱隊列中,而且表現得如此“出色”:他已經不是一般地合乎“時宜”,而是在揮刀砍向那些“不合時宜者”;他已經不是一般地從異見人士變成了“無不同政見者”,而且還率先向異見人士、被懷疑有異見的人士乃至被指定為異見者以便其他無異見者可以踩着他的屍體向上爬的人士發出了血腥的吼叫:“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就是這個高爾基,回國後不久便上司寫作了“俄國文學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頌揚奴隸勞動的那本可恥書籍”(索爾仁尼琴語)——《斯大林白波運河修建史》,當年的人道主義者這樣贊美勞改工程:“對人的原料進行加工,比對木料進行加工,要困難不知多少倍!”至于高爾基在吹捧斯大林方面的表演,由于過分肉麻就不說也罷。
當然,曾有人解釋說這一切都是強加于高爾基的。這種解釋把高爾基的晚年幾乎說得如同囚犯,甚至連他的死因也似乎不明不白:當年蘇聯大肅反時當局就曾宣稱這位紅色文豪似乎是被“人民的敵人”暗害的。而到了“解凍”時代也就有人請君入甕,把暗害者的罪名扣到了斯大林當局的頭上。
如果是這樣,高爾基似乎也就沒什麼“難讀”,可是嚴肅的曆史學家好像很少支援這種說法,如同不支援說斯大林的暴政是由于他當了沙皇的密探一樣。
是以我們隻得承認,至少在沒有新證據前隻能姑且承認,高爾基的确發生了難以解釋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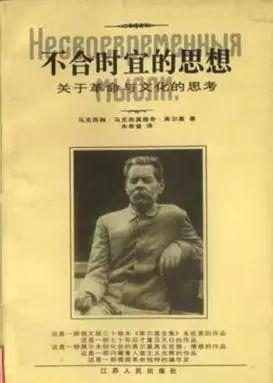
一貫的理想主義者?
如前所述,高爾基從“海燕”到“不合時宜者”的心路旅程是不難解釋的,因為這兩者可以用人道主義精神串起來。如果高爾基并沒有當過“不合時宜者”(如同改革前我們的印象那樣),那麼他從“無産階級海燕”到“紅色文豪”的曆程也是不難解釋的,因為這兩者可以用“社會主義”信仰串起來。在前一種情況下,高爾基的形象就如同雨果《九三年》中描述的那個出于比革命更崇高的人道精神而放走了貴族的高尚革命者郭文。而在後一種情況下,他的形象就如同那笃信“貧下中農打江山坐江山”的阿Q式“革命”者。
然而從“不合時宜者”向“紅色文豪”的轉變,卻委實令人費解,因為這猶如郭文變成了阿Q,其不可思議的程度,要遠遠勝于朗德納克侯爵變成郭文,也遠遠勝于阿Q變成了趙太爺。關鍵在于按人們通常的見解,信仰的改變乃至“階級立場”的改變,都要比人格的改變容易解釋。如果一個人原來虔信自由主義,經過深思後又改信了社會主義,或者相反;先信社會主義後信自由主義,那不會使人驚奇。如果一個人原先忠于“封建王朝”,在社會變動中重新站隊,轉而效力于“資産階級共和國”,那也不令人詫異。但如果郭文變成了阿Q,那就如同普羅米修斯變成市井小偷一樣令人難以接受了——盡管從“主義”的角度講,也許普羅米修斯的“盜”火與小偷的竊财都可以解釋為蔑視财産權的某種“主義”。
為了避免這種解釋的困惑,許多人力圖從“主義”中尋找“高爾基這兩個極端(按:指“不合時宜”與禦用大師)背後的一緻性”,試圖證明“正是那些促使他反對十月革命的因素導緻他擁抱斯大林體制”。(《讀書》,1997年第11期,第70—71頁,程映紅文。)這些評論者還認為:“高爾基的這段曲折一定程度上在激進主義革命的知識分子朋友或同路人中頗具代表性,那些與革命時分時合,雖有龃龉但最終仍然認同的人為數不少,隻是不如高爾基富有戲劇性罷了。”
我對此難以苟同。問題恰恰就在于那些人“不如高爾基富有戲劇性”。這個差别恐怕不是能輕易地“罷了”的。的确,同情革命但又嫌其“過激”,認同變革但又驚懼于其“代價”太高,贊成其宗旨但又厭惡其血腥手段的知識分子“同路人”在當時的俄國是不少的。他們的确與革命“時分時合”,但隻要人格未被扭曲,就不會“合”得那麼“富有戲劇性”。可以設想他們會為未來的彩虹而容忍眼前的血腥,但卻未必會高聲贊美血腥。而在此後的程序中他們也往往難以逃避在這二者間進行選擇:或者因不肯贊美血腥甚至隻因贊美之聲不高而被“分”了出去,或者違心贊美而犧牲了人格——而在後一種情況下已不能說“正是”那種高尚的人道精神“導緻”這種贊美了。
更何況從高爾基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來看,他對十月之變的抨擊已經不僅是非議其手段而認同其方向、同情其宗旨而擔心其“過激”了。他指責布爾什維克的來複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而不是指責其為實作這一夢想付出的代價太大。他以《一月九日與一月五日》為題,把1918年對支援立憲的示威勞工的鎮壓等同于1905年沙皇對請願勞工的鎮壓,顯然,他在此并不是嫌對1905年慘案的報複太過激烈。
實際上,如果真是基于理想主義的認同使高爾基不計較手段的分歧而放棄了反對派立場,那麼這應當發生在列甯時代才合乎邏輯。的确,即使反對十月革命的人也往往不否認革命中存在着某種程度的理想主義激情,而從列甯到斯大林時代,無可否認的趨勢是這種激情在消退,而越來越讓位于既得利益的實用主義。像孟什維克學者П.П.馬斯洛夫、崩得首領Д.И.紮斯拉夫斯基以及一大批“同路人”作家如B.B.伊萬諾夫、П.А.皮利尼亞克、А.Н.托爾斯泰等人就是基于這種“同路者理想”而在列甯時代完成了與革命從“龃龉”到“認同”的轉折的。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樣的轉折已經很難發生了。這時發生的知識分子“忏悔”潮與黨内反對派的“歸順”風一樣,如果不是迫于壓力、賣論求生,或者是麻木不仁、随行就市,那就恐怕有更為形而下的成分。當然,不能說這個時代的社會一點理想主義色彩也沒有,但這點剩餘的“理想主義”若能感召高爾基并使其轉向,他當初怎麼會執意與列甯過不去呢?
高爾基和斯大林。
被蘇聯成就感染?
或又曰,“感召”了高爾基的并不是理想主義激情,而是蘇聯建設的成就。“看到俄國成為一個有秩序的大工廠”,高爾基圓了“強國夢”,于是也就心悅誠服地抛棄“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那些價值了。但如果高爾基真是這樣的“強國主義者”,他在斯托雷平時代就應當效忠沙皇才是,因為鎮壓了“一月五日”請願者之後的斯托雷平的俄國,當年在經濟上也同樣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是以我認為,導緻高爾基轉而“擁抱斯大林體制”的,絕不是那些“促使他反對十月革命的因素”,甚至也不是那些當年使他成為“無産階級的海燕”的因素。(《不合時宜的思想》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封底有編者之言:“高爾基是一座森林,這裡有喬木、灌木、花草、野獸,而現在我們對高爾基的了解隻是在這座森林裡找到了蘑菇。”
問題在于這“蘑菇”是從哪裡長出來的?是在健壯的“喬木”上,還是在腐爛的朽木中?
在由“龃龉”而轉變為“認同”的人中間,除了那些原來同情革命而後因“同路人理想”原諒了革命的血腥的人以外,還有其他種種類型。例如有人從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立場出發,認為不管什麼“主義”、使用了什麼手段,能使俄國強大并戰勝仇敵就是好的。二戰時期的白俄僑民中不少此類人士,當時甚至連過去的白軍統帥鄧尼金也向斯大林進表稱臣,并請纓抗德呢。
還有的則是出于一種類似于“和平演變”“曲線改造”的動機,其典型便是以前立憲民主黨人H.B.烏斯特裡亞洛夫為代表的“路标轉換派”。正如當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使不少沙皇當局的反對派認為外部反抗不如内部推進,進而發表《路标》文集宣布改變路線與當局和解一樣,1921年蘇維埃政府放棄“戰時共産主義”而改行新經濟政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經濟自由化,這也使該政權的一些反對派産生了改外部反抗為内部推進的想法,于是在白俄僑民中出現了《路标轉換》文集與同名雜志。其中的烏斯特裡亞洛夫等人更于1935年回國服務于斯大林治下,完成了另一種“從龃龉到認同”的程序。
高爾基的曆程顯然與以上這些人都不同。他的“轉變”既不是出于“同路人理想”,也不是出于民族主義或“路标轉換”意識,那麼是出于什麼呢?慣于從形而上的角度尋找“動機”的研究者們至今未能提供可信的解釋。
并不複雜的真相
然而,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在形而上的層面鑽牛角尖呢?在沒有新的證據支援這些形而上的“動機說”之前,我們不妨設想:也許事情本來并不那麼複雜?也許老百姓的思維方式比學者的思維方式更能了解這一切?也許我們的大文豪并非整天生活在形而上世界,他也會有形而下的考慮?也許從郭文到阿Q的轉變并不是那麼不可思議,隻是可能不像“從朗德納克變成郭文”或“從阿Q變成趙太爺”那樣更有“思想史”色彩或更富于“學術”意義?也許高爾基的轉變機制并不是個思想問題,而更大程度上是個人格問題?
其實并非“也許”,早在高爾基仍是“不合時宜者”時,他就已經在給前妻的信中透露了苦衷:他“對沒有實際效果的文字抗議感到厭倦”了。高爾基不是魯迅,不會沉醉在“絕望的抗戰”中;知其不可,何必為之;悲劇難演,喜劇何如?考慮到“實際效果”,高爾基不得不“合乎時宜”起來。當然,也許他本來沒想要“合乎”到後來那種程度,但這哪裡由得了他!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在對黨内反對派(或“反對派嫌疑人”)大開殺戒以前,已經先在“同路人”身上牛刀屢試。從沙赫特案件到“工業黨”“勞動農民黨”“孟什維克聯盟局”等“地下黨”獄,早已使“同路人”們談虎色變,更不要說“不合時宜者”了。高爾基在這時回國未必是純粹出于“思想史上的原因”,但他既然回來,以他的身份與當年的表現,能不把“時宜”“合乎”到最大限度嗎?
當然,這樣的解釋容易招緻的一種批評是:大文豪會如此屈從于權勢麼?試看他當年面對沙皇專制,是何等正氣凜然!但關于這一點,索爾仁尼琴在他的着作中已作過有說服力的解釋:那種專制比起“古拉格”來,是太小兒科了!在小兒科裡經受了考驗的人格如今發生了扭曲,并不是很奇怪的事。
于是,《不合時宜的思想》一書給人的感慨太多了。這本書無疑使高爾基作為一個深刻思想家的形象豐滿起來,但它同時也使我們看到了一幅人格的漫畫。如果沒有這些思想,從“海燕”到“紅色文豪”的高爾基給人的印象是個單純的左派作家,猶如一個“苦大仇深的老貧農”,雖談不上深刻,卻有幾分可愛的樸實與天真。而知道了這些思想之後,卻不免使人在驚歎之餘也倒抽一口涼氣:我們還有必要煞有介事地反“左”嗎?這些人原來什麼都明白,隻是我們這些受愚弄者顯得太傻太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