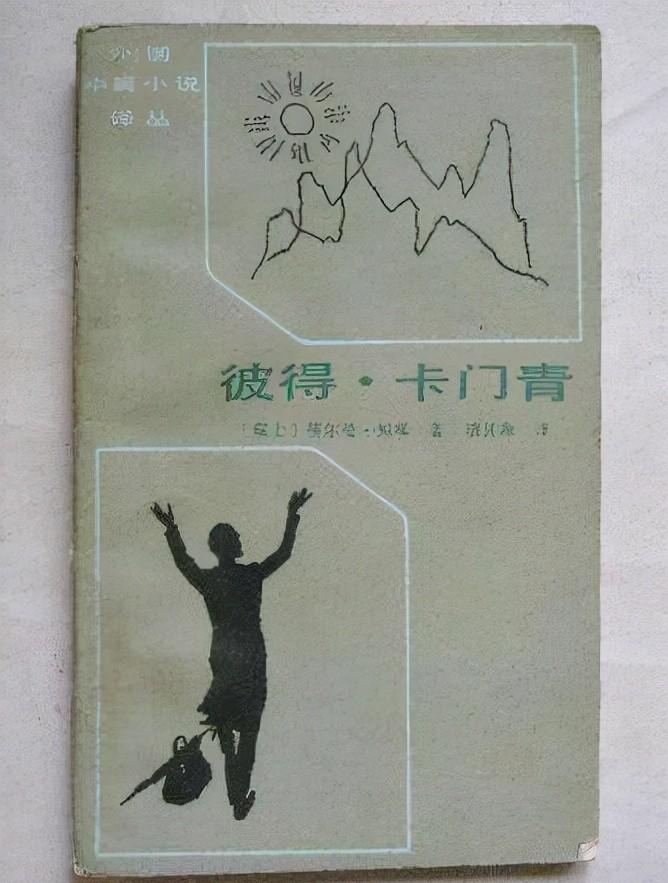
梁東方
現代生活中,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文學這種東西在度過了青春期之後一般來說就沒有用了。成年人而一直還愛着文學的,不是包括但不限于寫作、出版和圖書營銷之類的從業者,就是不食人間煙火者;而且即使是從業者,其中到底有幾成是真正熱愛着文學的人,也是很可以打上個問号的。這大緻上是任何一個經濟“仕”用社會裡的常态。
可是文學的無用有時候又是被有用纏繞的人生中一件非常貼心的東西,它可以将人從有用卻不解決靈魂困惑的泥潭裡打撈出來,為你的其實一直超然不居的靈魂找到一個同志,一個夫妻,乃至一個近乎圓滿的逋逃薮。瑞士作家瓦爾澤、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波蘭作家布魯諾·舒爾茨等等都是生前不名一文,死後才被發現的作家,在他們默默無聞的人生過程中,就是靠着文學寫作的陪伴,才得以不那麼痛苦甚至還有些愉快地延續了自己的生命的。
這樣說的意思并非說文學本身有多麼神聖,實際情況是貼着文學的标簽卻隻在人的低級本能與隻在功利主義範疇内打轉轉的文字始終占大多數,那種一味在人和人之間糾纏的故事和套路,即便是有文學性也已經乏善可陳,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
因為我一直有一種在一般文學興趣裡顯得有些奇怪的愛好:像是喜歡大自然題材的繪畫一樣,喜歡文學中那些以大自然為描繪對象的作品。比如坐着爺爺的馬車去《草原》上割草的契诃夫,比如喜歡一個人到森林裡去走路的普利什文,比如騎着自行車追着鳥兒做觀察筆記的赫德遜,比如寫田野上的生活、寫灌木樹籬的傑弗裡斯,比如寫《沒有見過大海的人》的克萊齊奧……他們當然寫的不僅僅是大自然,而是他們眼裡的大自然,歸根結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之中的文字、文學,是文學中的支流,卻也是我眼中文學之為文學的最高境界。這決定于我眼中的文學的無用之用:文學是生活中的美、陶醉和終極價值所在;唯一與這樣的文學價值認定相比對的,就隻有自然,是人對自然的體驗和讴歌。文學的主要神性,都在這樣與自然相關的話語裡。
正是在這樣的閱讀傾向之下,我有幸遇見了黑塞。準确說是黑塞的光芒照耀到了我,後來我終于到黑塞的黑森林中的故鄉卡爾夫、他上學的毛爾布隆修道院的山水之間、以及大海一樣的博登湖畔的隐居處、瑞士的阿爾卑斯山間的黑塞屋去追尋他文字中的那些風景的時候,這道光芒始終都真切地在眼前照耀着。
黑塞自然平易又極富邏輯韻律的文字,一下就擊中了我。這樣的語言風格也正是我自己自覺不自覺地追求。而他行文中的很多習慣也都是我所推崇的,比如即便是他那些評論和随筆,他也總是書寫自己的直接感受與思索,很少引用,從不引經據典,絕不抖知識。這也正是我自己的閱讀喜好與個人寫作原則。黑塞是一個感受型的作家,他的最偉大的價值就是他的感受,而這也正是一個藝術家之為藝術家的根本。
一個讀者和一位作家的親近感,有時候就先源于這種叙述的語氣和習慣,他像一個人的氣息一樣,天然地對你形成吸引力。黑塞是歐洲保護得非常好的自然環境中生長出來的鐘靈毓秀之人,他那因之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玻璃球遊戲》其實脫離了他大部分作品講述人與自然關系的基調,在我看來實際上并不出彩,他最出彩的還是那些沉浸在大地山川河流湖泊之間的自然文字。他寫過思辨性的東西,寫過愛情,寫過理論,但是他終究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自然之子。《彼得·卡門青》那樣将一個人的少年夢幻與自然山水結合得天衣無縫的作品,始終具有撼人心魄的永恒魅力;人在少年時莫名的憂傷與起伏的希冀,正與大自然晝夜、四季、寒暑的節律有着某種神秘的一緻性。黑塞捕捉到了這種神秘的一緻性,用詩性的文字将天雲花草與人類生命中的色彩聲響編織成誘人的互文關系,每次賞讀都能深深地打動我的心。
《彼得·卡門青》從上帝說起,然後講到上帝的居所自然,“我”作為兒童和少年所觀察到的自然,自然裡的水樹和雲,雲下面我的牧羊生活,改變我的牧羊生活的學校生活,小說在開始了幾萬字以後才進入所謂的正題,也就是我們通常在文學作品裡所習慣的情節。
他娓娓而談的叙述,幾乎沒有故事,但卻還是能讓人很有興趣地往下讀。因為作者的叙述脈絡是青年人的内心世界的成長,是人類對于自然和社會的認知的感覺與進步,是關于一個敏感的靈魂的成長史。
其實證的叙述和空靈的感覺性表達總是交叉進行的;空靈的叙述之中也經常插入實在性的叙述,兩者互相補充,不使讀者疲勞,不使叙述過于平坦。
在小說将近結束的地方,意外的發現黑塞竟然和我有一樣的随身攜帶小筆記本将郊外的景緻記錄下來的習慣;而且,那種一開始隻願意記錄自然界裡的景象,寫生一樣地記錄風霜雨雪和樹木花草山嶽河流,但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人的趣味也是和我一樣的。他對書中主人公的這種描述實際上他自己的夫子自道,是他審美過程和生活曆程的忠實記錄。黑塞實際上是用熱愛自然的方式表達自己疏離于所謂正常的人類社會的審美傾向。從小他就有一種叛逆于慣常人生路徑,蔑視既有的貌似天經地義的人生格局的精神氣質,這種氣質始終伴随着他,至死不渝。
他貌似随意的筆觸,将自由的書寫和自由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活的審美的生活——緊密地結合起來,時時和自然同呼吸。這正是黑塞最根本的寫作之道和生命之道。
這本薄薄的小書我隻在自然環境裡才閱讀,它跟着我在從春到夏的郊外的漫遊裡經曆了很多和美妙的黃昏和傍晚,經曆了潤物細無聲的春雨的洗禮,也經曆了有冰雹的雷雨大風,最後竟有不舍得就讀完的情緒彌漫。
在今天人類越來越失去了梭羅的瓦爾登湖那樣的自然感受的機會的生活狀态裡,在越來越稀少的自然中回味包括黑塞在内的自然文學經典,看人類曾經在那麼豐茂的自然中的那麼豐富的感受,已然是文學的同時也是自然的、地球的至為寶貴的遺贈。好的文學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撫慰着人,指引着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