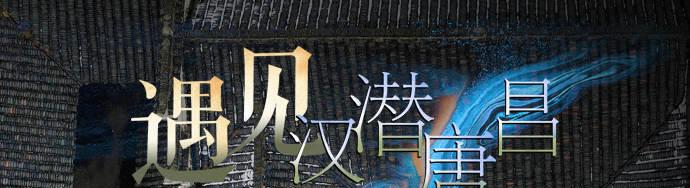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首席記者 鮑亞飛
對於潛來說,蘇轼不能隻是一個人,而應當是一個符号;不能隻停留在古籍和記憶裡,而應當經常跳出來出現在我們面前。
前幾日,特地跑了百十公裡去找寂照寺,找綠筠軒,去找他筆下的於潛女,踽踽而行,遍訪不得。
蘇轼是一位在詩詞書畫上俱可開派的人物:散文與歐陽修并稱“歐蘇”;詩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繪畫他和表兄文同開創“湖州竹派”;在學術論述、醫學、水利等方面也有極高造詣,甚至還有堪比宰相的理政之才。
這樣的一個人曾和杭州臨安於潛有過親密的交集:他把杵臼之交的朋友留給了這裡;他把名聲籍甚的詩歌留給了這裡;他把對官員昆山片玉的評價留給了這裡……
友,是情誼;詩,屬文脈;評,顯思想——如此說來,蘇轼留給於潛的是至少一半的靈魂。
△三蘇祠蘇東坡雕像/圖檔來源CFP
【一】
蘇轼一生多次離京外放,其中兩次是來了杭州:初到杭州時是通判,再到杭州時任知州。
熙甯四年(1071年)底,蘇轼第一次來杭州任通判,34歲。六月出發,十一月底才到,待了三年。
這三年,無論是蘇轼的杭州還是杭州的蘇轼,都是柔軟的——杭州的山都不高,出入自如,平易近人,猶如隐士;杭州的水可鑒心,連而不斷,勾留甯靜,催促傷逝。于是,他可以在這裡銜觞賦詩,訪佛寺、問民風;左采菱、右放歌。在杭州,他不用故作堅強,風是溫潤的,山是深翠的,水是清碧的。
元祐四年(1089年),52歲,他再踏杭州,四月出發,七月到任。
這一次他修繕西湖、治理水災、疏通管道……一切都是民生,都是生活。他不必豪放,不必躊躇滿志,他隻要真誠地生活。蘇轼之于杭州,是習慣;杭州之于蘇轼,是港灣。
△西湖。裡爾/攝
【二】
蘇轼和於潛的緣分,始結于通判杭州。
他至少兩次進入於潛,一次是熙甯六年,一次是熙甯七年,觀政、遊曆、留詩。
熙甯六年時的於潛縣令是刁璹(shú)。聽聞蘇轼來於潛視政,他按耐不住高興——蘇轼是他的同年,蘇轼的二伯蘇渙和他的叔叔刁約也是同年進士。兩人是上下級,兩人又是世交。刁璹知道蘇轼的品行喜好,特地将蘇轼安排在自己覺得最幽靜的綠筠軒。
綠筠軒在於潛寂照寺内,寺廟裡有僧人慧覺。一面是佛門佛學,一面是“臨窗遠眺,滿目皆是茂林修竹”。東坡坐而忘日,寫下《於潛僧綠筠軒》。
當然,蘇轼此次來是為了視政,在縣令刁璹的陪同下,他去往鄉間,走于鄉道。一路民情村風,所到之處,鄉野無不笑面相迎。蘇轼奇之,問:“為何?”答:“刁令熟久矣。”
這個時候蘇東坡才知道刁璹天天走田過地,深為治下百姓所愛,大家熱情相迎的原因不在自己,而在刁璹。回觀這幾天所曆,他頗有所感——可以肯定,這種印象一定非常之深,并在蘇轼的心裡保留非常之久,乃至于蘇轼欣然寫下《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一方面說於潛被刁璹治理得“吠犬足生氂(máo)”,一方面擔憂“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長使山人索寞溪女啼”。
第二次蘇轼再抵於潛時,少了些第一次的輕松。當時飛蝗自西而來,彌天塞地——於潛一帶,蝗害甚重。
他一邊組織人員捕蝗一邊急切地向朝廷報告,在蘇轼後來到任密州時寫的《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中曾有追叙:“轼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
於潛這個地方山秀水靈且人風淳善,是一個堪輿絕佳之地,自古以來少災少害。在蘇轼“災傷手實書”中可以知道,這一次的蝗蟲是由外地蔓延而來,并最終導緻了當地百姓種無可收。
在所謂“止水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的艱難時光裡,蘇轼一直都守在於潛,于是也就有了後來的《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苶(nié),有懷子由弟二首》。
△於潛風光/臨安區委宣傳部提供圖檔
【三】
陪着蘇轼捕蝗的,是刁璹的繼任毛國華。
《蘇轼年譜》記載:熙甯七年八月蘇轼撲蝗。二十八日,還至於潛,晤縣令毛國華……也正是這一天,蘇轼和縣令毛國華、縣尉方武去走訪了於潛明智寺,宿西菩山。
這一夜的明智寺和一年前的寂照寺不同:那夜是刁璹的安排,這晚是蘇轼的有意為之——明智寺是他的至交辯才法師的“三皈依”之地——換成是我,到了好友初入佛門的寺廟,也必然是要去拜谒的。
辯才法師,俗姓徐,於潛縣人,10歲在西菩山明智寺出家,16歲落發受具足戒。他18歲開始遊方問法:離西菩寺去杭州上天竺,師從慈雲法師;25歲時已名聞東南,被宋神宗賜紫衣袈裟、賜法号“辯才”。
這樣一位大師見法問法的地方,蘇轼慢慢走去,心性虔誠。他先說寺前“雲晦”、“遙望”兩山的“石瘦”,再說寺内“清涼”、“明月”兩池的水清,最後還說這種景緻以及修行不是靠追求而是“須天付”的結果。
想必蘇轼是極為尊敬法師辯才的,不然他不會專門去明智寺。當然,他們兩人的關系也一定是非常深的,不然不會有寒冷欲雪裡的空等,不會有蘇迨的“剃落摩頂”,不會有元祐四年的樂以忘憂“過溪亭”……人生零落百十年,故人稀、三兩個。
其實,他們的故事,絕大部分都發生在杭州,是因為辯才是於潛人,是以兩人的交往才被當地人所記。相較于這些千百年前的記憶,蘇轼留給於潛的《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二首》更為人熟知,文獻、縣志有記載,甚至連一些族譜在歸納本宗本族名人的經曆時,也會把眼光打開一些,零碎或者片段地将之收錄。
△杭州龍井村辯才與蘇東坡/圖檔來源CFP
【四】
我想多留一些文字給道潛(号參寥子,俗姓何,於潛浮村人)。一則因為他是於潛的大德;二則因為他和蘇轼的交情非其他任何人可以替代,當然,還因為希望今人能再有這樣的情誼,而不隻是功和利。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1080年東坡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他任團練副使,一個類似于現在“按縣團級待遇”調研員之類的虛職。實際上當時的蘇轼屬于朝廷的監管人員,不能随意離開。他放筆拿鋤耕50畝山坡于城東,于是有了“東坡”。
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心情抑郁——于是道潛禅師不遠千裡去黃州探望,陪了一日又一日,竟然居留一年有餘。
我是一個喜歡朋友的人,陪三五天,最多一周,十天就是極限,像道潛這樣一陪就是年餘的,可能需要50個我。有一個形容至情有愛的詞叫“煮粥焚須”,但我覺得這個詞還不夠。
道潛和蘇轼的初見應當是在1074年之前。蘇轼赴任杭州路上見道潛《臨平道中》詩并刻之為石後不久,尋于西湖,并一見如故、輔車相依——熙甯七年(1074年)秋,蘇轼調密州知州,道潛到密州;熙甯十年蘇轼改任徐州,道潛從杭州到徐州;元豐二年(1079年)蘇轼調湖州知州,道潛又到湖州……湖州任上不足三月,“烏台詩案”發,湖州蘇知州被貶黃州蘇東坡。
額外地說一下,“烏台詩案”的最先舉報者就是那個錢塘沈括。此人不足評。他寫《夢溪筆談》而“坐标中國科學史”,但由他最先點燃的“烏台詩案”受牽連者39人,包括驸馬都尉王诜、李清臣、司馬光、黃庭堅等——這在文學史上是一次浩劫——于是在心裡對他頗為不喜。
不再展開了,不然就談了半個北宋,還是回到道潛這裡來。
元祐四年(1089年)東坡任杭州知州,道潛赴杭州;元祐六年蘇轼自杭調京赴颍州知州;次年二月任揚州知州;再一年又任定州知州——三年三徙,道潛無一次不往……
有些人覺得蘇東坡是個文豪,調動再多,大小總是個官員,這個從於潛浮村出來的和尚說不準是個酒食征逐之輩?
如果這樣想,那就真的陰暗了。
東坡先生曾給李端叔寫過一封信:“得罪以來……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大家都恐避之不及,隻有道潛不離不棄。因與東坡關系太近,他還被治罪、被開除僧籍,甚至被勒令還俗,但護守依然——紹聖元年(1094年)六月,東坡被貶甯遠軍節度副使、再貶惠州、三年後終貶海南儋州——據說放逐海南,在北宋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道潛聽聞,又要從杭州轉海南相訪。
蘇東坡覺得自己可能有去無回,死活不同意,專門作書勸止,道潛才作罷。
蘇東坡是“一蓑煙雨任平生”,道潛是“半聲木魚随君去”。
将近30年的情誼,不為功、不為利、不為名,隻有伯埙仲篪(chí,古代的竹管樂器,像笛子),隻有灼艾分痛——於潛潺潺2000年,這樣的人,無有;這樣的故事,無有;這樣的取艾自炙真意,無有。
△宋:李嵩《赤壁賦圖》絹本,設色,局部/圖檔來源CFP
【五】
曾有人考證,蘇轼留給於潛共有8首詩。這種說法不太嚴謹:有幾首畢竟寫于於潛之外——如果這樣都算,那蘇轼還有更多的詩詞是寫給或生于於潛或活于於潛的人的,比如慧覺,比如辯才,比如道潛——把這些詩都集合起來,加上批注和解析,大抵可以做一本很厚的書:字比書貴,書比人重。
如果再學一學蘇轼刻石《臨平道中》,這一首首就能做成一面詩牆,讓於潛中學的孩子們知道教舍一側的山上曾有綠筠軒,軒中曾住過蘇學士,這個蘇學士應當變成他們耕讀成文的“心向往之”。
自然,更希望現在的於潛鎮能多做一些關于蘇轼的文字收集或考據,多多愛護這位剛過完985歲生日的國寶級人物。
(感謝臨安區委宣傳部大力支援,感謝臨安區委黨史研究室稽核)
【之前,我們寫了什麼】
遇見漢潛唐昌|開篇語
遇見漢潛唐昌|遇見·漢潛唐昌
遇見漢潛唐昌|其耘陌上,四季耕織
遇見漢潛唐昌|邵氏金書鐵券:嘉靖祖母的一生
遇見漢潛唐昌|元好問和滕茂實的一段往事
遇見漢潛唐昌|駱賓王: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本文為錢江晚報原創作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複制、摘編、改寫及進行網絡傳播等一切作品版權使用行為,否則本報将循司法途徑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