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上2019年的尾巴,我們已在本月26日觀賞了今年最後一次也是近十年全國大部分地區可見的倒數第二次日食,不知大家是否欣賞到了這次奇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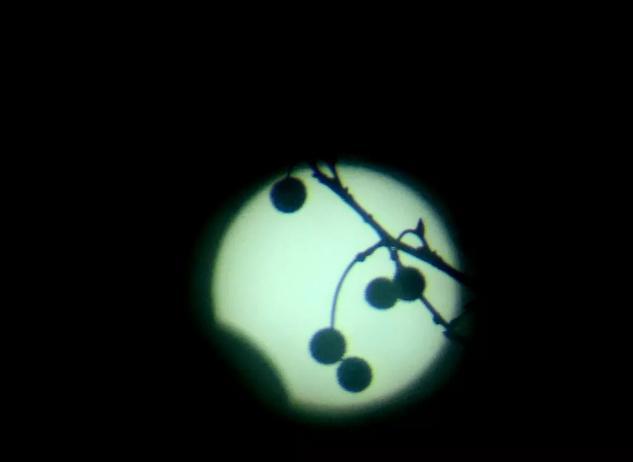
大家一定都聽說過“天狗吃月亮”或“天狗吃太陽”吧,這是中國古代對于月食或日食的民間說法。古人對日月食非常重視,認為這些特殊天象是上天對世間的警示,因而對它們作下了數量衆多的記錄,中國古代對于日食的記錄從上古時期就開始了,根據《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統計,古代文獻中記錄的日食共計約有1000條,雖然記述比較簡略,但仍有很大價值,為後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資料資料與科學遺産。
如果殷墟蔔辭也算文獻的話,那麼中國古代對日食的記載可以上溯到晚殷時期。在河南省安陽市出土一根長約12厘米的獸骨上刻着有關一次日食的蔔問:“癸酉貞日夕又食,佳若?癸酉貞日夕又食,非若?”“癸酉”為占蔔的日期,“貞”意為占蔔,“夕”指黃昏,這句蔔辭的大意為:“癸酉日占蔔,黃昏發生日食,是吉兆還是兇兆?”經研究人員判斷這是殷商武乙時期(即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文物。
有人喜歡提到更早的一次日食記載。那就是所謂的《尚書》仲康日食。據《尚書·夏書·胤征》記載,夏的第四位君主仲康在位時,天文官員羲和酗酒誤事,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其中提到:“惟仲康肇位四海……惟時羲和,颠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馳,庶人走,羲和屍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幹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将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一般被認為是仲康元年農曆九月初一(“季秋月朔”)、發生在房宿(西方星座中天蠍座的一部分)的一次日全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紀事。《胤征》記述的内容簡單說來便是羲和因醉酒,沒有及時報告發生日食,指揮敲鑼打鼓,使得人心倉皇,最後羲和慘被砍頭的故事。因為涉及到《尚書》真僞問題,這一記載是否可靠,尚有争議。譬如對交食預報的“先時”和“不及時”——這裡的“先時”和“不及時”似乎隻有解釋成預報日食先時或不及時在語意上才能通順——一般來說在夏代是無從談起的。但是從《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日有食之”條引《夏書》這條記載并解釋為日食以後,古今學者大多認為這是發生了一次日食。若這确實是真實的日食記錄,對于這次日食發生的确切時間,自古以來被許多天文曆算家推算,尚未取得一緻意見(此處舉兩個例子:唐代天文學家一行認為這次日食發生于公元前2128年10月13日,我國現代天文學家、北京天文館首任館長陳遵妫則認為這是公元前2137年10月22日的一次日食)。
我國曆史文獻中儲存的交食記錄大部分是可靠的。譬如《詩經》日食和《春秋》日食。《詩經?小雅》中的“十月之交”篇中同時記載了一次日食和一次月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春秋》記錄了37次日食,魯宣公以前15次,有7次記明發生在朔日;魯成公以後22次,全部記明發生在朔日。經用現代天文學方法推算,這37次日食中實際發生的有33次。這些結果說明魯成公以後的曆法對朔的推求已經達到相當準确的程度。
有些小夥伴也許會有疑惑,這些日食的記錄有什麼意義嘛?難道古代的日偏食、日環食或日全食和現代的還有什麼不同嘛?
當然不是。首先,所謂“曆法疏密,驗在交食”,日月食記錄的精确度和對日月運動的掌握程度息息相關,而成系統性的記錄又可表明古代已有專人負責此事,并可由此檢驗曆法是否精确。這足以說明我國天文事業起步很早,成就也極其突出,正是對于這些特殊天象的準确記錄才逐漸了解日月五星的運作規律,由此誕生了精确的曆法。而擁有了精确的曆法即是掌握了一定的自然規律,由此推動了各行各業的迅猛發展,這使得古中國成為人類璀璨文明的傑出代表。
最後,由于日月運動的周期性可測定,日月食這類天象是極其容易回推的。若古代的日月食記載與現代回推吻合,則很容易推測出那段曆史真實發生的年代,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手段證明了曆史的真實性和精确性,一個例子便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中利用《竹書紀年》“懿王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即位,天再旦于鄭”對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日環食的記錄,推定出周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這種利用天象記載推定曆史年代的學問被稱為“天文曆史年代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