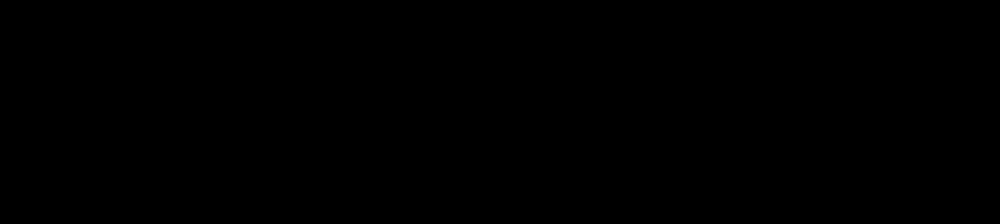
他是一位“被嚴重低估的作家”;
他也是一位極具現代英雄主義氣質的作家;
蘇珊·桑塔格曾說,對于那些會從閱讀中獲得樂趣甚至上瘾的人來說,他是“一個特别令人滿足的作家”;
他用一個句子,便能令你心碎。他就是詹姆斯·索特。
今天分享理想國出品、詹姆斯·索特的短篇小說集《昨夜》的譯者張惠雯的一篇文章。透過譯者與書的連結、共鳴,我們也将再次和這位“美國當代文學被遺忘的英雄”相遇。
不得不抑制,卻又不能不釋放的情欲
文/張惠雯
01. “使它與衆不同的是那種語調,
仿佛它是從陰影中寫出的”
2018年夏末的一天,我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鎮上的一家書店閑逛,無意中看到了這本小說集。在那之前不久,國内剛剛出版了詹姆斯·索特的長篇小說《光年》,在文學圈引發了一場不小的熱潮。是以,當我注意到這是索特的書時,不禁拿起來翻閱了一會兒。我讀了首篇《彗星》中的幾段、末篇《昨夜》中的一兩段,最後翻到了《阿靈頓》……那是一個從覺得不錯到被吸引進去的漸入佳境的過程。當時的情景有點兒像這個集子裡的小說《給予》裡的一段描寫:
我當時站在格林尼治村一家書店裡,驚呆了。我記得那個下午,陰沉、靜谧,我也記得當時的自己,幾乎沉浸在對事物的普通感覺,對生活深度的認知(我找不到别的詞),但最重要的是,那些連綿的詩句帶來的狂歡。它是一首詠歎調,參差錯落,沒有終止。使它與衆不同的是那種語調,仿佛它是從陰影中寫出的。
當然,這些小說給我的不是“詩句帶來的狂歡”,相反,那是一種使人下沉、仿佛慢慢凝結的感覺,你最終會沉入這樣一個深度——面對自己的内心。“使它與衆不同的是那種語調,仿佛它是從陰影中寫出的”——這句話卻是對我的閱讀感受的精準描述。
在談論這部小說集之前,也許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這位對讀者來說不那麼“著名”的美國作家。小說家不是自己生活的記錄者,但他的教育、經曆、他生活過的地方等等會影響他的眼界、思維和審美,而這種影響最終會以某種方式折射進他的作品。
詹姆斯·索特于1925年出生于紐約,原名詹姆斯·阿諾德·霍羅威茨。父親喬治·霍羅威茨是位商人,畢業于西點軍校。詹姆斯生長于曼哈頓,家境富足,如一般的上層中産階級子弟,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曾就讀于紐約著名的私立學校霍瑞斯曼(Horrace Mann School),在父親敦促下最終也選擇了西點軍校,之後加入空軍,成為一名出色的戰鬥機飛行員。詹姆斯曾參與北韓戰争,戰後被派往德國、法國的空軍基地,在歐洲的這段生活極大地影響了他。他儲存了有關當時生活的大量筆記,在後來的訪談中,他提到每當翻看這些筆記,就像是回到了歐洲,回到了法國。
詹姆斯·索特
從詹姆斯不少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歐洲文化尤其是法國文化的影響。譬如,《一場遊戲一次消遣》以法國為整個故事的背景,《光年》中也有涉及歐洲的片段。在《昨夜》這部小說集裡,《鉑金》中的父親布賴恩帶女兒去巴黎,在某個瞬間意識到自己圓滿生活中的緻命“缺陷”;《好玩兒》中,簡把自己幻想中的羅曼史置于威尼斯的背景之上:
這是她一直夢想的旅行,他們會在冬天去,因為冬天那裡沒什麼遊客。他們會住在運河上的一個房間裡,房間裡有他的襯衫、鞋子,半瓶……她懶得去想具體是什麼,某種意大利葡萄酒吧,也許還有幾本書。夜裡,亞得裡亞海的氣息透過窗戶飄進來,她會早早醒來,天還沒亮,看到他睡在她旁邊,正在輕輕呼吸。
詹姆斯從不諱言自己的“歐洲情結”(這種情結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從亨利·詹姆斯到海明威再到索特,我們都看得到老歐洲對美國藝術家的影響),他最喜愛的城市都是歐洲的城市,而法國是他的“世俗的聖地”。
02. 不時懷疑、動搖、挫敗
卻仍在堅持的英雄主義
1956年,詹姆斯·阿諾德·霍羅威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獵手》,從此使用筆名詹姆斯·索特。在《紐約客》的訪談中,他解釋了改名的原因:一方面為了免遭他所供職的軍隊的批評,另一方面是為了模糊自己的猶太裔身份,因為他不想成為“紐約的又一位猶太作家”。第二個原因可以聯系到詹姆斯·索特在寫作上的一個特點:他幾乎在刻意避免話題性。在當時的美國,“猶太作家”的身份恰恰意味着話題性和更多的關注。在美國的文學批評界始終存在着一種社會性的傾向,或者稱之為政治高眉,即他們十分偏好涉及種族、性别、階層等社會問題的“大”文學。
以納博科夫為例,無論他之前創作過多少精美、富有幻想力的小說,他那些缺乏意識形态批判态度的主人公和故事都未能引起廣泛關注。如果沒有後來驚世駭俗、極具話題性的《洛麗塔》,即便是納博科夫這樣的藝術家也可能多多少少被忽略。
第一本小說《獵手》的電影改編權使索特得到了一筆豐厚的收入,他得以于1957年離開軍隊,專職寫作。六十年代起,索特涉足電影界,寫了一系列電影劇本。但無論對于自己的好萊塢經曆還是以軍隊和飛行為主題的小說,索特都不太看重。從《獵手》到最後一本小說《這一切》(All That Is,出版于2013年),索特一生的主要作品包括六部長篇小說、一本回憶錄和兩個短篇小說集(1988年出版的《暮色》及2005年出版的《昨夜》)。作為一位長壽的作家,他完全稱不上多産。
索特去世時,《紐約時報》刊發的悼念文章稱他“作家中的作家”,“銷量極低而贊譽極高”,這也是美國小說界的共識。索特得到的贊譽多來自于同行作家,包括理查德·福特、雷諾茲·普萊斯、裘帕·拉希莉……作家們談及索特時常用的一個形容詞是“被低估的”。“被嚴重低估的作家”——這或許是個讓作者本人感到無奈的贊譽。
索特并不是那種淡泊聲名的人,相反,他渴望聲名,對于自己的作品不暢銷他是相當失望的,他曾說:“除非有足夠的銷量,否則你就不能進入重要作家的行列。”我們不必把他塑造成為理想孤軍奮戰的古典主義英雄。如果他有一種英雄主義氣質,那也是現代式的英雄主義,是一種不時懷疑、動搖、産生挫敗感但最終仍堅持下去的能力。這一點英雄主義展現在與自己期望的名聲相比,他更看重通向“名聲”的途徑。面對強大的主流文學嗜好,索特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一條安靜但也冷僻的道路。一般認為,除了其作品中“時代的缺席”之外,寫得太少、寫得太慢也是索特不紅的另一個原因。
在索特那個時代,發生了太多大事:冷戰、越戰、平權運動、登月……我不知道索特本人是否關心時代話題,但他顯然不想在小說裡讨論這些事。那些吸引眼球、能引發媒體大讨論的東西從來不會成為索特小說的主題,最多是在其小說人物的閑談中一掠而過。
索特小說的魅力不是類似新聞或社會學著作的那種魅力,它隻是一種純粹的藝術魅力,來自于錘煉雕琢的語言、詩性的風格、緊貼肉身和人性的主題。而我始終不太明白的是為什麼對于一些讀者和批評家來說,這種緊貼肉身和人性的主題竟會被貶低為“小”或“狹隘”,因為與風雲變化、轉瞬即逝的時代相比,這種東西畢競更為恒久。有意思的是,1997年索特的回憶錄《燃燒的日子》出版後,作家受到的批評之一就是他對自己的北韓戰争經曆太過輕描淡寫,也就是說,一些批評家仍因沒能在其中讀到他對戰争的控訴、反思而耿耿于懷。
一些批評家在索特小說裡看到了海明威、亨利·米勒的影響,但索特告訴他的傳記作者威廉·道威,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是安德烈·紀德和托馬斯·沃爾夫(另一個與歐洲關系密切的美國作家)。至少在主題和人物選擇上,索特的選擇遠不如海明威和米勒那麼耀眼。那些缺乏尖銳痛苦和波折的中産階級生活困境,無論用多麼細敏、精緻的語言去寫,對很多人來說都沒有足夠的吸引力。索特似乎早已預感到這一點。當時,他和家人定居在紐約郊區的哈德遜河灣,但在藝術家雲集的格林威治村有個小房間,并在那裡進行寫作。他覺得和其他藝術家相比,自己處于劣勢。他如此描述:“我住在郊區。我有妻子、孩子,全部的家當清單……即使待在城市裡,我也很難相信自己正在從事什麼有趣的工作。”
索特認為他最重要的小說是1967年出版的《一場遊戲一次消遣》和1975年出版的《光年》。而以他對自己的苛刻,他覺得隻有《一場遊戲一次消遣》接近自己所設定的那個标準。不過,倒是他的兩個短篇小說集分别為他赢得了一次福克納文學獎,以及一次福克納文學獎的提名。這并非偶然,索特精心錘煉的藝術風格也許恰好适合短篇體裁。我們很難想象用寶石來鋪路,但以寶石來雕刻一件精緻的珠寶,那就再合适不過。
《一場遊戲一次消遣》&《光年》
03. 僅用一個句子,
就足以令人心碎
《昨夜》這個集子裡的小說非常凝練、精美,每一篇都映射出生活不同切面的閃光,但每一篇又都觸及人性中幽暗而柔軟的深處:不得不抑制卻又不能不釋放的情欲,對青春及代表着生命欲望與活力的美好肉體的眷戀,失去與孤獨……如果以今天某一部分讀者對文學的“簡化”判斷标準而言,可以說,這十個故事裡的每一篇都涉及不忠或背叛的主題。但每一篇又都通過誠懇、精細入微的描述告訴我們:一切遠非那麼簡單。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是:究竟“背叛”了誰?是他人還是自己?如果說忠于自己反倒會背叛他人呢?一旦進入人性深處,一旦忠實于人性本身,我們會發現最值得關注的不是背叛本身,而是什麼導緻了背叛,以及背叛是怎樣改變一個人的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的……索特深谙此道:好小說本身是對“簡化”的嘲諷和反抗。
《昨夜》
[美]詹姆斯·索特 著,張惠雯 譯
這本書打動我的原因之一就是主題的反複呈現:真誠、集中、深刻地去寫情欲的掙紮、釋放和幻滅(其中飽含着對婚姻生活的質疑)。在這裡,既有一個男人全然的坦誠,一個暮年人對已逝歲月的眷戀,又有作家對人性弱點的了解、寬容與同情。情欲是個複雜的沖突體,它陰暗又柔軟,頑強又脆弱,爆發時像焰火般明麗,卻又極易破碎幻滅,它相當無恥卻又似乎忠實于本性。而當一個東西足夠真誠,它似乎就無可指責。在《鉑金》中,關于貪戀年輕女子帕梅拉而出軌的布賴恩,有這樣一段描寫:
那些日子裡,欲望如此深沉,讓他雙腿無力,但在自己家裡,他并沒有什麼不自然的表現…… 他帶着那種禁忌的喜悅,禁忌但無與倫比的喜悅回到家,擁抱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一起玩耍,或是為他們念書。禁忌的愛滿足了他所有未被填滿的欲望,他懷着一顆純潔的心,從一個人的身邊來到另一個人的身邊。
這段文字的驚人之處在于它寫出了背叛純潔動人的另一面。在人們通常的印象中,背叛者複雜、狡詐、對家庭懷着憎恨……無論如何,這些形容詞和“純潔”都不沾邊。而索特呈現出另一種真相:背叛令背叛者滿足、喜悅,他幾乎變得更純潔了,懷着更多的愛,也是以更親近他的家庭。
這裡的真實是動人的。但有時候,真實也是殘酷的。在《棕榈閣》裡,阿瑟是個冷靜、精明的男人,單身,但記憶中有個難以忘記的深愛的女人——諾琳。他在二十年後再次得到了當年錯失的、令他一直耿耿于懷的機會,但再見面時,他發現他完全無法接受諾琳老了的樣子。在兩人約定見面的電話裡,諾琳還是讓阿瑟心動神馳的當年的諾琳,他聲稱一下就感覺到她——完整的她,但最終決定結局的事實就是如此簡單:“難以相信,她老了二十歲。她發胖了,從她臉上都能看出來。而她曾是最漂亮的女孩。”
索特小說中的主人公通常是和他一樣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産階級,但他們顯然又不是那種意滿志得的中産階級,而是那部分對生活持有某種懷疑态度、在安穩的生活中不安分的中産階級。他們通常有個幸福家庭,而他們敏感,不滿足,眷戀美好事物,常常因情欲而背叛了婚姻和家庭。最後盡管仍受制于生活的秩序,他們卻選擇以其他方式堅持内在的反叛。
在《彗星》裡,菲利普與妻子及其他人争論有關感情“欺騙”這一話題,最後倔強地為自己的背叛辯護。在《給予》裡,“我”因妻子逼迫不得不終止和同性情人的關系。從表面上看,“我”失敗了,但精神的背叛從未終止:
我把他的一些照片藏了起來,當然,還有他的詩。就像那些永遠無法嫁給心愛男人的女人們一樣,我将遠遠地追随着他……
這些小說裡的主人公在内心依戀他們的“錯誤”、堅持他們的“錯誤”,似乎那個“錯誤”才是他們記憶裡最美好的東西。
索特的小說使用的都是相當簡單的詞彙,但這些詞語經過某種奇特的組合,具有了非同尋常的表現力,其畫面感和調性尤其令人羨慕。索特小說裡的畫面感更像電影而非繪畫的畫面感,這和他在好萊塢的經驗有關。他的小說裡經常出現類似電影中的場景切換、視角變換、鏡頭推移等手法造成的效果。是以,他的景物、人物很容易在人的意識中顯影成像,同時,這種心靈鏡像具有一種流動的美感。索特小說中的景物描寫不再是通常的對人物活動環境的交待或情節之間的潤滑,它具有電影中畫面的功能:畫面的意義在于畫面本身。
索特的短篇小說沒有長篇《光年》裡那種物件、畫面的堆疊排列,詩歌般語言的鋪陳,強烈的風格感,但這些短篇自有一種更為精簡、内斂的典雅。它的語言具有最好的簡潔語言所具有的那些優勢:因濃縮産生的密度、不動聲色的穿透力、奇妙的平衡感。密度構成那種抓住你、令你屏心靜氣沉下去的重力;穿透力會在你沒有任何提防的情況下直接進入你的内在,這或許就是美國作家邁克爾·德達所說的:“詹姆斯·索特僅用一個句子就能令人心碎。”至于平衡感,那是所有文體大家的秘訣,當語言均勻、平衡得恰到好處,文體再也沒有任何突兀的腫塊,達緻了整體的自然流暢。但正因為消除了突兀感,包括那種彰顯出來的炫技的突兀、煽情的突兀,平衡感反而是個最容易被不那麼内行的讀者所忽略的優點,因為它的功能不是“顯示”,而是撫平那些不該顯示的、違反美學意義上的和諧與平衡的東西。
我覺得這種技巧和索特最熟悉的飛行技巧極其相似:需在充滿突變的環境和行動中始終保持平衡與流暢。二者需要同一種直覺和天賦。此外,索特的語言不那麼美國,不那麼本土,他有一點别的什麼,我認為那是一種源自歐洲文化和生活方式影響的東西。索特的風格不同于菲利普·羅斯式的熱切怨訴,不同于約翰·契弗式的美式嘲諷,也不同于雷蒙德·卡佛過分骨感的美式極簡……詹姆斯·索特的簡潔裡有一種考究,一種冷冽而漫不經心的優雅。
在這些小說中,與小說集同名的《昨夜》也許是色調最陰郁、最令人感到不适的一篇。題目“昨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小說中因身患癌症而決定安樂死的妻子瑪莉特的“最後一夜”,是丈夫沃爾特意料中與妻子瑪莉特共度的最後一夜。但在第二天早晨,當沒能“成功”死去的瑪莉特下樓撞見偷情的丈夫和朋友蘇珊娜後,過去的這個“昨夜”在某種意義上也成了沃爾特和瑪莉特之間存有信任感的夫妻關系的最後一夜,成了沃爾特和蘇珊娜情人關系的最後一夜。
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篇幅極短的《阿靈頓》。小說的主人公是個因妻子而犯罪、喪失了名譽的軍人,小說通過他參加的一次葬禮和一些零星回憶,觸及了情欲、榮譽、友誼、沉淪、死亡……最終,置身于阿靈頓公墓這一軍人最高榮譽的象征,這位背叛者雖感到羞慚,卻仍選擇“忠于”妻子、獨自站在失敗者那邊:
最後,當他們全都站起來,手捂在胸口上,紐厄爾獨自站在另一邊,堅定地敬禮,滿懷忠誠,一如既往像個傻瓜。
在死亡與榮譽面前,一個失敗者固執的愚蠢也具有了某種莊嚴感,某種雖敗猶榮的悲劇性。這篇僅約四千字的小說冷峻、肅穆、深邃,對我來說,它是一個完美的短篇。
張惠雯
2020年4月24日于波士頓
排版:九筒
配圖及封圖來源:《一樹梨花壓海棠》
《午夜巴黎》《45周年》《愛的邊緣》
👇《昨夜》+《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