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擁有幾千年的文明傳承,曆史積澱的文化基因不僅烙印在我們的血脈中,在我們的姓氏文化中,同樣可以找到中華千年文明的縮影。
姓氏中烙印母系氏族的影子
姓,人所生也。因生以為姓,從女從生。——《說文解字》
在遠古部落時代,人與人之間并沒有固定的婚姻關系,由于男子負責打獵,需要長期在外奔波,而婦女則負責留下來照顧孩子,以及采集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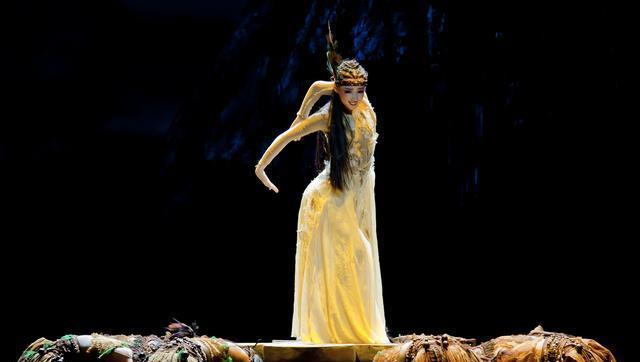
是以後出土的西周青銅明文上,能夠考證的姓大多帶有女字旁,如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嬴(沒錯,就是秦始皇的那個姓)等。是以說最開始一個人,他(她)的姓是由其母親決定的,後來随着生産力發展,人們逐漸從狩獵采集為主的生活方式,轉為農耕為主的生活方式,體力占優勢的男性成為社會核心勞動力。
母系氏族也是以發展為父系氏族,孩子們的姓也是以由随母改為随父親的姓了,而“姓”字的女字旁依舊被保留了下來,從中我們可以依稀看到,中國母系氏族的曆史痕迹。
分封制下的姓氏大爆發
告别原始社會,人們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不斷有新的土地被開墾出來,同時也有新的人口出生,原本依照母系氏族産生的姓氏已經無法滿足需要,于是新的姓氏創造方式誕生:
以先祖封地為氏,如陳姓,便是妫滿(舜的後人)被周武王封在陳地,并建立了“陳國”。後世子孫以故國為氏,稱陳氏。
以先祖的名或字為氏,如周靈王有一個兒子名為年夫,其後人便以年為氏。
以先祖官職為氏,如三國時期的司馬懿,“司馬”便是其先祖所授官職為氏。類似的還有太史、司徒等。
以上幾種是常見的姓氏來源,此外還有,以兄弟宗族排行順序為氏的,如伯、仲、叔、季等,以職業為氏的如巫、屠等。這一時期姓氏來源迅速增加,但常用的漢字數量畢竟是有限的,于是便出現了不同氏族,因為不同的原因都采用統一漢字為姓氏的現象。
如中國五大姓氏之一的張姓(見注釋1),既有一部分是源自先祖官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
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制弓矢,子孫賜姓張氏。
意思是說,黃帝的一個孫子因發明弓箭,被其封為弓正(官職),其後世子孫便以“張”為氏。此外春秋時期的晉國,有一位大夫名為解張,字張侯,他的一部分後代便以先祖的字為氏。是以當我們檢視百家姓時,往往會發現,同一個姓氏,會有多個來源。
以祖先封地為姓氏來源的,絕大部分都發生在黃帝到周朝時期,這期間的王朝往往都以分封制為主,到了秦始皇一統六國,實行郡縣制後,分封制便退出了曆史主舞台,後世随偶爾出現,但往往也是昙花一現,或僅僅是配角,這就解釋了為何秦朝以後,很少再有以祖先封地為姓氏來源的情況發生了。
民族大融合的見證
曆史的車輪進一步向前,中華民族來到了漢唐時期,這一階段華夏的文明火種開始逐漸成熟,并開始綻放璀璨的光亮。漢武帝為了親政,挂羊頭賣狗肉的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變相排擠窦太後的黃老一系官員,不成想卻在大儒董仲舒的運作下,促成了儒家文化的成型。而出生于豐縣(今江蘇省内)的張道陵,遊曆四方後在蜀中開始傳道,并建立了正一盟威道,成為後世道教的發端之一。而佛教東傳,玄奘取經,則促使形成與中國本土的禅宗誕生。
儒、釋、道,文明的火種成型,自然吸引向往光明的人們,是以漢唐時期成為中國曆史中一個多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匈奴、鮮卑等遊牧民族先後融入到華夏民族大家庭當中,這也促使了中國姓氏文化中另一個主要來源——少數民族借用漢字為氏。
如融入華夏民族中的匈奴人,便改姓為劉氏、呼延氏、郝連氏、宇文氏、高氏、衛氏等,匈奴人的改姓時間較為漫長,是以很多姓氏在最初依然保留了很多遊牧民族特色,但後來随着融入加深,以及為了使用友善,又進一步進行了簡化,如郝連氏逐漸簡化為郝氏、何氏,連氏,婁煩氏簡化為樓氏,烏維氏簡化為烏氏。
與匈奴相比,鮮卑族在魏孝文帝(467年-499年)從上至下的文化改革下,民族融合的更加幹脆和徹底,鮮卑皇族拓跋氏(黃帝後裔)的嫡出子孫改姓為“元”,庶出子孫則改姓為長孫氏、李氏(見注釋2)、王氏、鄭氏、金氏、趙氏等。
看到百家姓的這些新成員,有時便會覺得這是如今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的最好證明,因為在姓氏上便已經是一家了。
而這些姓氏也如文化符号般,見證着華夏民族大融合的曆史。
注釋1:曆朝曆代因為人口和風俗變化,都有不同的五大姓,目前單就人口占比最多的五個姓氏,分别為:李、王、張、劉、陳。
注釋2:拓跋氏的這次改姓中的“李姓”,便是後世李唐王朝的先祖,李淵、李世民皆來源于此,是以唐玄宗李隆基崇奉老子為先祖,并追封為“大聖祖高上金阙天皇大帝”,明顯是不尊重曆史(當然,後世帝王不少也這麼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