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語說的好:“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曆史上因為功高蓋主而受到皇上猜忌,最後不得善終的将領可謂是數不勝數。很多人把它歸咎于人性本質,認為“大丈夫可同患難,不可同富貴”。
其實不然,真正安身立命的功夫在于“知進知退,能屈能伸”,哪一個皇帝不喜歡一個在自己需要的時候能挺身而出,在自己不需要他的時候安穩老實的臣子呢?
郭子儀,他是民間傳說中最有出息的武狀元,他平定了安史之亂,還上演過“單騎退回纥”可謂是戰功赫赫,為大唐王朝建立了不世功勳,還被唐德宗尊稱為“上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裡面說:“他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及人臣,而衆不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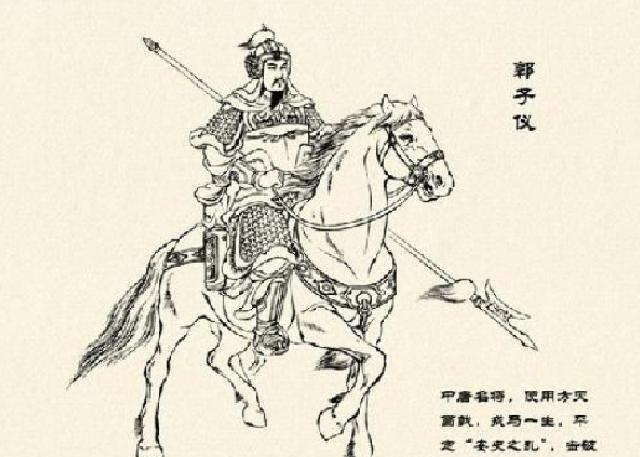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五福”指的是“長壽”、“富貴”、“康甯”、“好德”、“善終”。在曆史名臣中功高蓋主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夠做到善始善終、五福俱全的卻少之又少。以至于後來人們提到富貴壽考的名臣,基本上能想到的也就隻有郭子儀。
康熙皇帝說:“漢唐以來功名最盛而有福祚克全的首推郭子儀”。可見,無論是民間傳說還是貴為皇帝,對郭子儀都是推崇備至的。
“武狀元”出身
在郭子儀出生4年之後,一個偉大的天才詩人出生了,這個後來光芒萬丈的詩人叫做李白。
很多年後,郭子儀犯法,正是因為李白的求情,郭子儀才被赦免,再後來因為永王謀逆,而作為永王幕僚的李白,按照唐朝律法,也應該處斬。為了救李白,郭子儀不惜放棄高官厚祿,最後才讓李白免于一死,而他自己也被流放。
有時候曆史就是這麼神奇,很多人印象中他們是毫不相幹的兩個人,以為沒有什麼交集,卻沒想到郭子儀和李白是這樣的惺惺相惜。
公元697年,郭子儀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這一年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把年号改為“神功”,還在科舉制中增設“武舉”。
而“武舉”制度的開設,也為郭子儀後來的人生程序鋪平了道路,也正是通過武舉考試,郭子儀一舉高中,成了後來人們傳說中的“武狀元”。
當時的武舉考試,很多考生都是從娃娃抓起的,郭子怡也是自幼練習國術。當時的考試内容有7項,比如要射中150米開外的箭靶,要騎着馬射牆頭上的鹿皮,還要考站立射箭和移動射箭,還要把5米多長的門栓舉起來10次,類似于今天的舉重。
而且,除了對這些武力值的要求,還要求考生身材要高大魁梧,外表要體貌豐偉,甚至于口才上也要嚴辭辨證。在這麼嚴苛的考試标準之下,年方二十的郭子儀仍然高中武舉,不能不說是難得一見的人才。
但高中武舉隻是第一步,要想成為軍事統帥,還要經受時間的磨練和考驗。自從郭子儀高中武舉之後,他的仕途十分順利,一路升遷成了坐鎮一方的統領,但真正讓他光耀史冊的還要數他的赫赫戰功。
平定“安史之亂”
公元755年,郭子儀59歲這一年冬天,身兼三地節度使的安祿山以奉诏讨伐楊國忠為借口,在範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逐鹿起兵,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亂”。
習慣了開元盛世的唐朝百姓們都大驚失色,眼看着安祿山指揮着十五萬大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控制了河北。
危急關頭,唐宣宗急忙召回正在守孝的郭子儀,指令他率領朔方軍平亂。就這樣,年近花甲的郭子儀繼唐氏命脈于一身,開啟了他忠心大唐的榮譽之路。
郭子儀一出馬就斬殺了幾個叛将,戰事頻頻告捷,充分展示了大将風度,同時也牽制住了安祿山進攻的腳步。老皇帝唐宣宗十分欣慰,加封他為禦指大夫。
随後,郭子怡還不計前嫌,推薦和他向來不和的李光弼擔任河東節度使,他們強強聯手一舉收複了河北。
做出了這麼大的貢獻,郭子儀也受到了極高的封賞。他家大業大,每年的俸祿高達24萬貫良田,美器、珍玩更是數不勝數,他的私宅也非常大,家人走在裡邊甚至會迷路。
他的妻子被賜予“國夫人”的最高稱号,8個兒子也個個為官,到孫子那一輩,人實在太多了,連郭子儀自己都分不清,以至于在孫子們前來請安時,隻能點頭示意蒙混過關。
難得糊塗
盡管郭子儀位極人臣,但他一直都謹言慎行,75歲那年皇帝要給他升官,還要送他500親兵,他卻全都拒絕了,大概是為了避免被皇帝猜忌,他還特意向皇帝要了6個美女。
在古代,有頭有臉的人物都講究潔身自好,而郭子儀這樣身居高位的大臣卻反其道而行之,用“自污”的方式避免了皇上的猜忌。
根據史料記載,郭子儀雖已80高齡,但身邊妻妾成群,甚至平日會客時,也全然不顧及自己的形象,把她們帶在身邊。
對待人際關系方面,他更是用“難得糊塗”的态度處事。他和挖自己祖墳的人稱兄道弟,對待屬下的錯誤,隻要不是原則問題,他一般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朝廷為郭子儀建造了一個巨大的汾陽王府來犒勞他,他卻下令平日裡府門大開,任由百姓進進出出,全然一副大大咧咧的樣子。
而皇帝看到他如此縱情享受,貪圖富貴,一點也沒有遠大志向的樣子,是以對他從來不曾有所猜疑。
而著名學者黃樸民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他不這個樣子的話,就難逃韓信一樣被滅族的下場。”可見,郭子儀的确是大智若愚。
小結:
郭子儀在皇上對他的功勞充分肯定并大加封賞的時候,并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功臣自居。他看淡名利,用“自濁”的方式避免了皇上的猜忌,可謂是十分的高明。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一個人德高望重的時候,同時也就到了高度危險的時期,這個時候,全身而退的功夫,比開拓進取的功夫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