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吳王壽夢以來,吳國在會盟中的活動始見于《左傳》。我們都知道,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最主要的外交活動和手段,就是會盟。會盟雖然不是直接的兵刃交鋒,但是它卻對戰争有着實實在在的影響。
會盟可以暫時停止紛争,如弭兵之盟。但當會盟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也會引發戰争。戰争結束時,盟主仍然會舉行會盟,以達成協定。也正因如此,成為盟主的國家便有了話語權。
春秋時期戰争頻仍,且周天子王權旁落,由諸侯争先會盟的激烈程度就可以看出端倪。從這些會盟中,也可以觀察出各諸侯國之間的外交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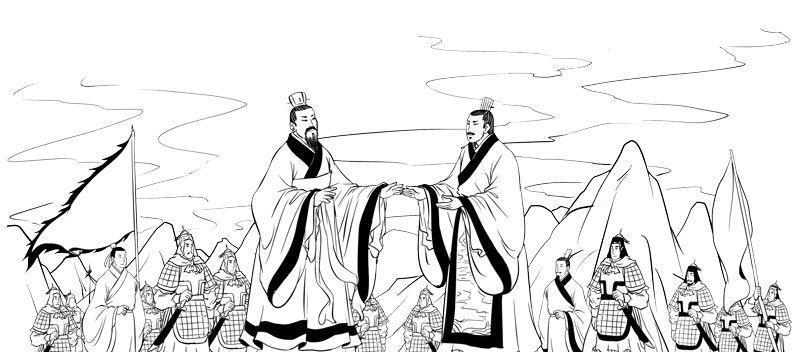
諸侯會盟
吳、楚兩國在春秋時期早期,也是有和平共處的記錄的。在齊、楚争霸時期,他們共同與齊國為敵,《管子》中有吳國人伐榖的記載。
齊桓公五年,吳國人曾偷襲齊國榖城,為了恐吓吳國,并讓他們停止進攻,齊桓公曾攻打到吳國,占據瓜分了吳國一半的土地。
從此吳國成為楚國的附庸。《左傳》雲:“楚滅舒蓼,盟吳、越而還。”楚國滅掉了舒蓼國。楚莊王有逐鹿中原、稱霸于諸侯的企圖,他先拉攏了東邊的小國,以南方為勢力據點,集結南方之力與北方的晉國集團對抗。舒蓼不服楚國,楚國滅之,并往更東方與吳、越結盟,楚莊王一方面鞏固着南方的局勢,另一面則讨伐陳國,為中原霸業布局。
由此可見,這段時期由于楚莊王稱霸,是以楚強吳弱的形勢是十分明朗的。直到晉國向吳國提供軍事援助,才一掃吳國以往卑微弱小的形象,局勢也為之改觀。
《東周列國·春秋篇》齊桓公劇照
魯成公七年,申公巫臣因為一己私怨,奔逃至晉國,并且心存報複,遂經過晉景公同意出使吳國,打破了吳楚聯盟。晉國采取聯吳制楚之政策,自此“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晉、吳兩國的地理位置距離遙遠,如果他們之間要聯系,必然要打通莒國。成公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入吳,假道于莒,作為兩國交通的要道。
在申公巫臣的一連串規劃下,晉國開始邀請吳國參加會盟。正因如此,才有了“蒲地之盟”。在成公九年,晉國将魯國的“汶陽之田”交給齊國,“諸侯二于晉”。晉人害怕這種情勢持續發展,便開啟了“蒲地之盟”,以尋“馬陵之盟”。
從季文子與範文子的對話——“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中可以看出,這一次“蒲地之盟”以失敗而告終。晉國雖然邀請吳國加盟,然而,吳國卻沒有參與。
《東周列國·春秋篇》楚莊王劇照
晉國方面并未放棄,于是在成公十五年開啟了“鐘離之盟”,終于“始通吳也”。但是這一次會盟并非是君主會盟,可見會盟的等級并不高。
晉國十分看重吳國擾楚的功效,于襄公三年舉行“雞澤之盟”,并且又向吳國發出了邀請。晉國看到了吳國的實力,因為這一年春天楚國主動出擊伐吳,但最終吳軍不僅擊敗了楚軍,還占領了楚國城邑。然而,同年夏天晉國會盟于雞澤,吳國又沒來。
“蒲地之盟”和“雞澤之盟”,吳國兩次都沒有來,中間的“鐘離之盟”也不是進階别的會盟,由此可見,這個時候的吳國,他們對中原諸侯國和外交事務仍舊沒有信心,他們也無法判斷如果依附晉國是否會影響自身的權益。而中原諸侯們因為吳國地處蠻夷之地,就草率地認為吳國是蠻夷之邦,他們對吳國也不重視。
但晉國卻心如明鏡,他們知道吳國的重要性,是以才不斷地派遣使者與吳國交好,數次邀請吳國會盟。
《吳越春秋》雲:“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此事展現出吳國對外交方面的重視程度有所提升,是以才提拔狐庸的官位。我們都知道,狐庸是晉國申公巫臣的兒子,由此可以看出吳國聯合晉國的念頭,在進一步地加深。
襄公十年,晉國舉行“柤地之盟”。這一次,吳王壽夢親自出馬,他想借此機會了解目前吳國在諸侯眼中的地位。吳王壽夢在位的倒數第二年,還在為吳國進行外交方面的努力。兩年之後,吳王壽夢就去世了,他“臨于周廟”。
《春秋左氏傳》
《左傳》中記載:“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迩廟。”
這就證明了吳國與周王室的血緣關系不容抹去,吳國更有謙讓不居位的美名,雖然他們曾被視為蠻夷,但仍然有王族後代的血統優勢。
吳王壽夢的外交計劃,讓中原諸侯們從根本上接納了吳國,也開始重視吳國。他也是《左傳》中記載的唯一一位“臨于周廟”的吳王。吳王壽夢親自參與“柤地之盟”,成就了“臨于周廟”這件大事,提醒後世子孫不忘其本,更看出吳國企圖融合中原、與諸侯協調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