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農村的院落長大,度過了平靜如水的童年。長大後走出了院落,卻常常懷念院子裡的生活,留戀院子裡的歲月,那種院落裡的文明和諧,鄰裡間的友好融洽,早已植入了我的心底,每當憶起總是溫暖如初,親切熟悉。
兒時居住的院落分兩進(裡天井外天井), 外院住着唐氏三家,裡院住着王家兄弟。
聽母親不止一次地叙述我出生的院落,1958年的夏秋,同一院落降生了我們三個男嬰,本來寂靜的院落頓時熱鬧起來,稚嫩的啼哭聲此起彼伏,不絕于耳。大人們出出進進,增添了無盡的忙碌與歡樂。晴日的早晨一塊塊雜色的尿布像奧運會場的萬國旗一串串地晾曬在院子裡的鐵絲上。因我們的到來,父母雖然辛苦勞累,但是人人臉上都洋溢着遮擋不住的笑容。
那個年代,農民家裡的糧食都要歸公,集中起來吃公社食堂。家家戶戶都是鍋裡無米,缸裡無糧。年輕的父母們歡喜過後是淡淡的憂愁,面對一個個嗷嗷待哺的男丁開始束手無策。乳水稀少,副食品奇缺……最後還是濃濃的鄰裡情意,互幫互助,同舟共濟度過了那段難熬的歲月。鄰居們無論誰家從親朋好友處讨來一碗半瓢的米面,都要分成三份,喂養我們無親無故的異姓兄弟。
接踵而來的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公社食堂随之解散,村民們的溫飽已難以維繼,吃樹葉扒樹皮,凡是山裡能吃的野菜、槐花、榆錢都千方百計地弄來當做主食充饑。大多數的兒童因缺乏營養而面黃肌瘦。
我也是如此,每日的主食基本是地瓜面煎餅或地瓜糊糊,隻有過年過節或者來了知己親戚,才能吃頓細糧。然而我們院落的鄰居們,卻從不吝啬自私,始終相敬如賓。無論哪家蒸一鍋馍馍,烙兩張油餅,首先想到的互相送一份,給幼小的我們。
同院落的小鄰居一起咿呀學語,一起扶礳邁步,不覺間三個幼小的生命悄然長大。後來我記事了,裡外院落便成了我們歡樂的“海洋”和打拼的“戰場”,時常被我們鬧得雞犬不甯,翻天覆地。風和日麗的春天,我們一起玩“占山為王”;烈日炎炎的夏夜,我們一起玩“老鷹抓小雞”;寒風蕭瑟的深秋,我們一起在柴草垛裡捉迷藏;大雪飄落的隆冬,我們一起堆雪人打雪仗。
到了上學的年齡,外院的唐叔是木匠,做了一模一樣的三個闆凳,我父親用毛筆在闆凳的反面分别寫上我們的名字。我們又一起走進了學校,坐進了教室。下午放學後我們牽手回家,在同一塊自制的黑闆上分别拼寫b、p、m、f……輪流運算加、減、乘、除……
七十年代中期,農村長大的孩子們開始厭倦了落後的家園和貧瘠的故土,渴望獨步他鄉異域,追求新的生活。年輕的人們成群結隊的走向工廠、礦山,走向商貿、教育(民辦教師)。我也是其中的一員,高中畢業後,期待外出謀生的情緒逐漸按捺不住,便打點行裝走出了生我養我的院落,走出了熟悉依戀的村莊,不是兄弟勝似兄弟的三個小鄰居也各奔東西。
現如今,随着城市建設的迅猛發展,成片成片的高樓日夜瘋長,成座成座的大廈森林般湧起。在我的家鄉,兩三層的小樓遍地開花,僅有的院落也翻修一新,變成單門獨院,那種賦有詩意的院落文明已被新農村建設的号角吹盡。那些和諧溫馨的鄰裡情意随時代的變遷已漸漸遠去。
自從搬到城裡,住進樓房才感到困惑,已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鄰居。雞犬相聞,熱情相待的親密,已變成老死不相往來;和諧友好的鄰居關系,已變成同一樓(一座樓)不相識,久住對門不相認的冷漠;一張張麻木的表情晃來晃去,總讓人感到世事的悲涼。
時常讓我懷念留戀的那段院落文明,已封存在記憶的源頭,溫馨親密的鄰裡關系,已掩埋在塵封的歲月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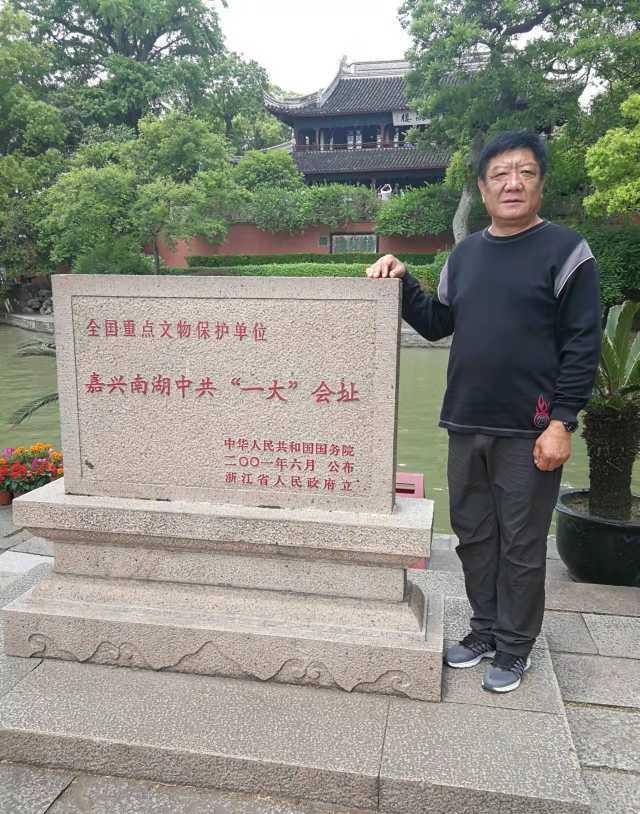
作者簡介:王其玉,山東沂源縣人,農發行沂源縣支行(退休),中國金融作協會員,作品散見于《散文》《金融文學》《齊風》及山東金融文學等媒體,多部作品收入《銀星璀璨》等文學合集。
壹點号 柳泉金融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