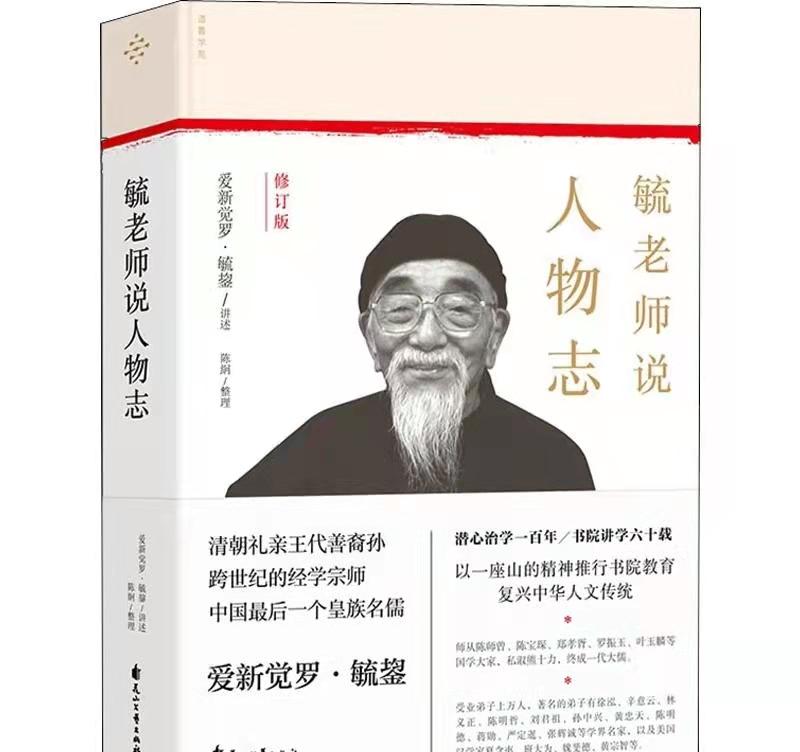
蓋善以不伐為大,賢以自矜為損。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跻;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終于出奔。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
因為善不以自誇為大,賢以獨占為損。是以舜能夠以禮讓成就德行讓天下人知曉,湯自謙不敢懈怠日進聖功;春秋晉大夫郤想要處于他人之上就瘋狂打壓下面的人,周襄王季父王子虎喜歡争鬥最後出逃晉國。這便是以貴為賤能謙卑處下,人際關系通達的原因。驕傲自誇欺淩他人,是自取滅亡的原因。
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淩軌等;内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是以怨難不在于身,而榮福通于長久也。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然害之,有功者人毀之,毀敗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奪,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由是論之,争讓之途,其别明矣。
是以君子舉止不敢逾越禮儀标準,欲望不敢蔑視法則。平時勤于修德進業,對人謙讓有禮表示敬畏。仇怨和困難就不會纏繞着自己,繁榮和福祿就會永久存在。小人就不這樣。持功打壓有才能的人,喜歡淩駕别人之上。是以處于人上就會加害别人,有功勞的人就會被小人毀掉,别人不幸就幸災樂禍。是以旗鼓相當就會互争先卻不能得到利益,兩敗俱傷就會被後來的人超越。由此看來,争讓得到規律,其中差別已經清晰了。
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留滞,以下衆為卑屈,以蹑等為異傑,以讓敵為回辱,以陵上為高厲。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以抗遇暴必構敵難。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釁也,必依讬于事飾成端末。其于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己之校報,亦又如之。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着于遠近也。然則,交氣疾争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并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毆,為惑缪豈不甚哉?
但是争強好勝的人,不以為然,以超越别人為積極進取;落在下風為停滞不前,覺得謙遜就是卑躬屈膝,以踩着别人往上爬為人傑,以讓對手屈辱為驕傲,以敢于犯上為勇敢無畏。是以奮進向前勇猛無比,不知反思。如果以高傲接觸賢人賢人必然謙遜處下,以高傲接觸暴躁必然構成仇敵劫難。互相敵對,就會是非混攪難無法明斷。是非混攪無法明斷那麼和自毀有什麼差別呢?并且被他人诋毀攻擊,都會心生怨恨,進而挑釁攻擊,然後利用某件事陷害對方再把故事編造的有頭有尾,讓聽的人即使不信也會覺得有可能是這樣。自己要是去計較報複對方,也是如此。别人一隊,會根據遠近來選擇相信與否。探究其中原因,互相争鬥怄氣的人,都是以污蔑對方自毀。言語上互相競争指責對方,這和借他人之手來毆打自己有什麼差別嗎?真是對這種謬誤産生迷惑啊!
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緻變訟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己。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别,則能讓者為隽矣。争隽未别,則用力者為憊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車決勝于廉頗,寇恂以不鬥取賢于賈複。
論其原因,如果我能自我反思檢讨還會導緻出現争端麼?都是自己心胸不夠,别人也不肯讓步。或者埋怨對方輕視與我,或者對方想要超越我。如果我沒有能力被對方輕視,那是我的不對對方沒錯;如果我有才能對方不知道,那就不是我錯了;如果對方的能力處于我之上,是我還需要努力的緣故。如果能力差不多但是對方超過我,那也是我的能力僅次于他,那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并且兩個人賢能上沒有差别,能夠謙讓對方的是更為俊秀。争名無法取得上下時,那麼誰用力去搶奪誰受到的傷害就會更大。是以蔺相如看看到廉頗的車子就能回避。寇恂不和賈複争鬥而獲得賢名。(寇恂和賈複都是東漢光武帝名臣名将領。)
君子所行的道,是反着勢去做啊。
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終極,乃轉禍為福,屈雠而為友,使怨雠不延于後嗣,而美名宣于無窮。君子之道,豈不裕乎!
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鬥之大訟;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變在萌而争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彭寵以朱浮之隙,終有覆亡之禍。禍福之機,可不慎哉!
君子所行的道,不願意憑借自身的強大去争鬥的。因為,君子能夠知道屈縮而後可以伸展,就會能忍受侮辱不會去計較。知道謙讓才可以戰勝對手,是以能謙讓處下不會遲疑。發展到最後,能轉禍為福。化解仇恨成為朋友。使怨仇不延續到後代子嗣,美名也會無窮無盡。君子之道,越走越寬闊麼!
并且君子面對再纖細微小的間隙也會彌補,是以再小的争鬥也不會發生。小人一點氣憤都不能容忍,終将受到更大的挫敗被侮辱。仇怨微小時候,尚可以用謙德化解。但演變成争鬥就會禍害已成不死不休。陳餘(秦末大梁人,于張耳刎頸之交)因為張耳受利益驅使而背叛,最終受到分屍之害。兩位東漢光武大将軍彭寵與朱浮結怨,最終導緻兵敗身死。福禍之間的微妙關系,不可以不慎重啊。
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以自修為棚橹。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是以戰勝而争不形,敵服而怨不構。若然者,悔吝不存于聲色,夫何顯争之有哉?彼顯争者,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為險诐者。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
《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獨行于三等之上。
是以,君子求勝的方法,都是以推脫謙讓别人為進攻為銳器,以修德進業自我強大為防禦。無事就沉默不語不顯露出非凡智慧。有争端就會以恭順開路暢通無止。是以戰勝對方也不會顯示出競争的意圖。敵人臣服就不會結怨。能夠做到這樣的人,喜怒不形于色,更何況大的争鬥呢?顯示出争鬥的人,都覺得自己有能耐,但是别就會覺得陰險不正氣。沒有冒險意圖,就不會受到傷害。若是相信富貴險中求,那麼幹嘛和他争鬥呢?冒險和争鬥,是關在籠子裡挑逗老虎,還能有活下來的可能麼?發怒傷害人,也是一樣道理。
《易》說“冒險就會有争端,争端都是由互相競争産生。”《老子》說“如果不去争,那麼天下沒有能争的過你的。”是以君子的為人處世是不應該去和别人鬥争的。這樣就可以超越凡夫俗子,獨立于三種人之上了。
何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勝,一等;賢而尚人,二等;賢而能讓,三等。緩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寬人,三等。
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逮也。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
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
什麼是三等呢?沒有本事卻自持自傲的人,第一等;有本事卻自誇其功的人,為第二等;功高蓋世卻不自誇自傲的,為三等。第一等人,愚蠢好勝。第二等人,有能力卻喜歡居人之上。第三等人,有能力但是卻能夠謙讓。第一等人,對自己寬松卻嚴格要求别人。第二等人,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别人。第三等人,嚴格要求自己卻能寬厚待人。
上面這些人,都不是中正的,會随着事态發展而變。多次變化後,就會迷失本性了。隻有知道規律變化的人,而後才能中正。
是以說,《論語》:孟之反策而奔殿。将門入,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得進也’”是不自誇,進而被孔子贊揚。管仲以辭去賞賜,是以受到更大的賞賜。名利豈能有不正當的手段來謀求呢?都是自身修養得到的,能與自然相契合。(孟做的太明顯了,有痕迹非真心。僞,人為的。自然形成的是真的。發乎于性情自然而然的表現出來。孟的演技和小鮮肉有一拼孔聖會看不出來?是以此處是批評孟的行為;管仲自己家的院子比諸侯的都大都氣派,使臣去得先拜見管仲才行。管仲德行是知道大義。)
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君子誠能睹争途之名險,獨乘高于玄路,則光晖煥而日新,德聲倫于古人矣。
君子之道通過謙遜處下為益。是以功勞都一樣,但是又獲得了美名。小人不知道益便是謙遜處下,是以功勞最後也被人奪走了。由此推論,不自誇的人最後都會被贊美,不争就是争。謙讓對手,最後都能勝利。處于下,最後都處于上了。
君子目睹為了名利不斷紛争産生的種種危害,是以能夠獨自踏以謙遜退讓這條路(以退為進這條路),則光輝顯著日新其德,美名就會等同古代聖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