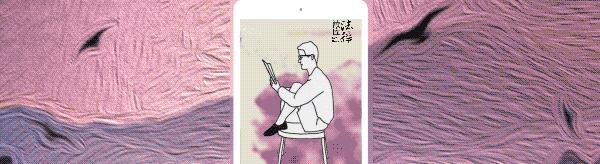
作者:李鳳鳴
來源:檢察日報
“合血法”不可靠,傳統中國又不允許法官不作裁判,唯一的辦法隻有兩害相權取其輕了。紀曉岚評曰:“必不能斷之獄,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此言所及的倫理沖突,确為其時難以破解的難題。
紀曉岚在《閱微草堂筆記》(以下簡稱《筆記》)中記錄了很多疑案,其中既有事實真相不明的原因,又有法律适用難定的因素,正如柏拉圖的洞穴,所見的往往隻是真相的影子。紀氏筆下的疑案,是傳統中國司法觀念、特點與精神的文學反映,綜撷其要,可分如下三類:因倫理沖突而導緻的疑案,因法律确定性缺失而導緻的疑案,因司法技術落後而導緻的疑案。
北京紀昀故居,曾懸有“閱微草堂”匾額,後被直隸會館取走,改懸啟功書“閱微草堂舊址”匾額
1
傳統中國法的核心是綱常,相較于法律規範,倫理具有優勢地位。在倫理沖突的情況下,如果不同倫理之間沒有确定的位階,選擇就成為難題。紀氏《筆記》即錄有多起諸如此般的案件,如童養媳案:此案兩造年齡皆在十六七歲,原告訴稱被告是其童養媳,如今他父母雙亡,被告欲棄之别嫁。被告則對此指控予以否定,稱兩人系同胞兄妹。因兩造父母皆為流丐,一亡一失,故姓氏鄉裡均無法确證。問其丐友,隻言他倆向以兄妹相稱,其他一概不知。不過,是以種關系相稱兄妹是本地慣例,丐友的證言也就沒有足夠的證明力。事也至此,要想查清,似乎隻有血緣鑒定一途了。但是,權威的法醫學著作《洗冤錄》中隻載有“滴骨法”,本案顯然不能采用。如此,唯有通過民間傳聞的“合血法”即以兩血相融或相斥來判定了。
然而,本案并沒有使用“合血法”來鑒定。其中緣由也許是:“合血法”并非司法中的規範性手段,即使有深厚的文化基礎,實踐中也不輕易采用。如此設想,從《筆記》所載的另起案件中似乎可以窺其一斑。此案中,弟弟不願将兄長外出經商前托付照管的資産歸還,遂誣其兄在外所生之子為抱養,欲以此排斥此子的繼承權。官府用“合血法”進行鑒定,兄長及其子兩血相合。其弟不服,刺血與己子相驗而兩血不融,遂以“合血法”不能為據為由上訴。這一尴尬的境地,正如時人所言:滴血不足成信谳。
“合血法”不可靠,傳統中國又不允許法官不作裁判,唯一的辦法隻有兩害相權取其輕了。兩相比較,斷離而誤,不過是誤破婚姻;斷合而誤,則是破壞人倫。換言之,誤破婚姻,不過有違父母之命的孝倫理;破壞人倫,則是禽獸行。孰輕孰重,一目了然。
案子雖然解決了,但本案裁判既沒有查清事實,依據也不是法律,顯然留有遺憾。《筆記》之是以記載,本意也在于此。對于此案,紀曉岚評曰:“必不能斷之獄,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此言所及的倫理沖突,确為其時難以破解的難題。
2
法律确定性是法律理想國的基本要求,對于防止恣意和保障公平至關重要。缺乏确定性,留下法律漏洞,往往導緻裁判無所适從。《筆記》中有這樣一起假想案件:一婦人至孝而至淫,如何處理?圍繞這個問題,有兩種意見。第一種是兩者可否互相吸收,隻論其重者。對此,有三種觀點。其一,孝福吸收淫罪。其依據是:犯淫罪最高僅為杖刑,而不孝罪當誅,可見不孝罪重于淫。由此反證,孝重則福也重,輕罪不能削去重福,故應舍淫而隻賞孝。其二,淫罪吸收孝福。服勞奉養隻是小孝,虧行辱親即淫則是不孝之大者,是以應舍孝而隻罰淫。其三,不能互相吸收。孝和淫分别為大德和大罰,兩者不能互相吸收,而應各受其報、分别賞罰。第二種意見是兩者可否相抵。對此也有兩種觀點。其一,不可相抵。如果因淫罪而減孝之福,會使人認為孝無福報;反之,以孝福而減淫之罪,會讓人認為淫而無罪。其二,應該相抵。如果因為孝而緻其人雖至淫而不加罪,不是更能促人盡孝嗎?如果因為淫而緻其人雖至孝而不獲福,不是使人更知戒淫嗎?
這個假想案最終沒有得出一緻的結論,主要在于孝與淫的行為規範未能具體化,對于是否可以乃至如何吸收或相抵也沒有具體規定,實踐中往往付之法官的自主裁量,其結果自然莫衷一是。
如果說這隻是一起假想案,《筆記》中的另一起案件則更具實在性。此案中,丈夫因災荒外出乞食,将父母托付于妻子。多年的艱難度日,在實在無法養贍的窘迫下,妻子隻好賣身度日。賣身本為盡孝,然丈夫歸來後,她卻自殺了。此案的問題是:死者該如何安葬?糾纏不下,隻得告官。
縣令的裁判較為清朗:可以葬之于祖墳,但将來不可與其夫合葬。準允前者,是因為孝順公婆,已不負祖宗;不允後者,是因為賣身失節,有負其夫。此判看似情法兩盡,但此婦猶不瞑目。見此情景,其公婆号泣申辯:媳本貞婦,子不養父母而委之于媳,是子之過也;因為盡孝而賣身,非媳之過也。此我家事,不必外人操心。語訖而媳目瞑,似乎昭示了如此定論的正确性。但是,邑人依然議論紛紛。
3
因刑偵、鑒定等司法技術落後,緻使無法查清案件事實,是一個逾時代的難題,古代尤其突出。《筆記》中有這樣一起奇葩案件:某官宅被籍沒,官府令三個步軍看護,深夜雪冷,三人飲酒取暖,不知不覺個個沉醉,不經意間燈被踢滅,三人就此暗中互毆,直至最後倦怠而息。本來這可能隻是一場酒後相戲,誰知早起一看,其中一人死了,兩個幸存者是以被拘押訊問。
案子審理起來并不難,兩人皆承認共毆傷斃人命,判其抵命也皆認命。問題是,死者一人不能由兩人抵命,畢竟這不是大逆搶盜等有法定不分首從情節的案件。雖然兩人都認可抵命,但并不意味着兩人都争着讓自己去抵命,官府必須兩擇其一。但是,讓誰抵命呢?
黑暗中,不知由誰起釁,也不知誰毆誰,更不知誰下的緻命傷。雖然可以刑訊,找個理由擇其重者論抵,但這不是理想的結局。幸好,時間是最好的法官,一個月後,其中一人因傷死于監獄,案子就此了結。
如果有現代法醫或痕迹鑒定技術,本案也許并不複雜,但因為缺乏技術,很多能夠簡單定性的案件也打上神秘色彩。如《筆記》中的這起案件就很玄乎:此案因某廟的兩僧接受兩道借宿而起,這本尋常之事,豈料一夜過後四人皆無所蹤,而廟中财物及道士所攜數十金皆在。更蹊跷的是,四人屍體竟在十餘裡外的一口枯井中被一牧童發現了,且經檢驗遍體無傷。
斷案的老爺遇到了難題:一物不失則非盜,年老皆衰則非奸,身無寸傷則非殺,門扃不啟,何以能出?距井十裡,何以移至?百思不得其解,最後隻得以疑案上報,而上官竟也無從駁诘。此案如系真實發生,之是以成疑,主要原因還在于司法技術的落後,托之玄怪,顯然是不确的。
上述三種疑案的分類,隻是就其大略而歸之。實際上童養媳案也事關司法技術,黑夜互毆緻死案也關涉“一命一抵”的傳統生命倫理,而孝淫兩難的問題,本質上也有因倫理位階不明而導緻法律不确定的因素。反思其間,可體會傳統中國司法邏輯之一二,明了其失其偏,于今日之法律進步不失為一種參考。
投稿轉載說明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公号非營利性 不支付稿酬
投稿即視為同意本公号對文章進行轉載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