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古代的絲綢之路東西萬裡,跨越了小半個地球,最東段的中國東部和最西段的歐洲西部之間,是有很長時差的。但是,古人能發現時差麼?他們如何看待時差?
老巴認為,由于古人的通訊不發達,也沒有很準确的計時工具和很快速的交通工具,導緻相隔很遠的兩地之間無法适時溝通,是以,他們沒法通過直接觀察發現時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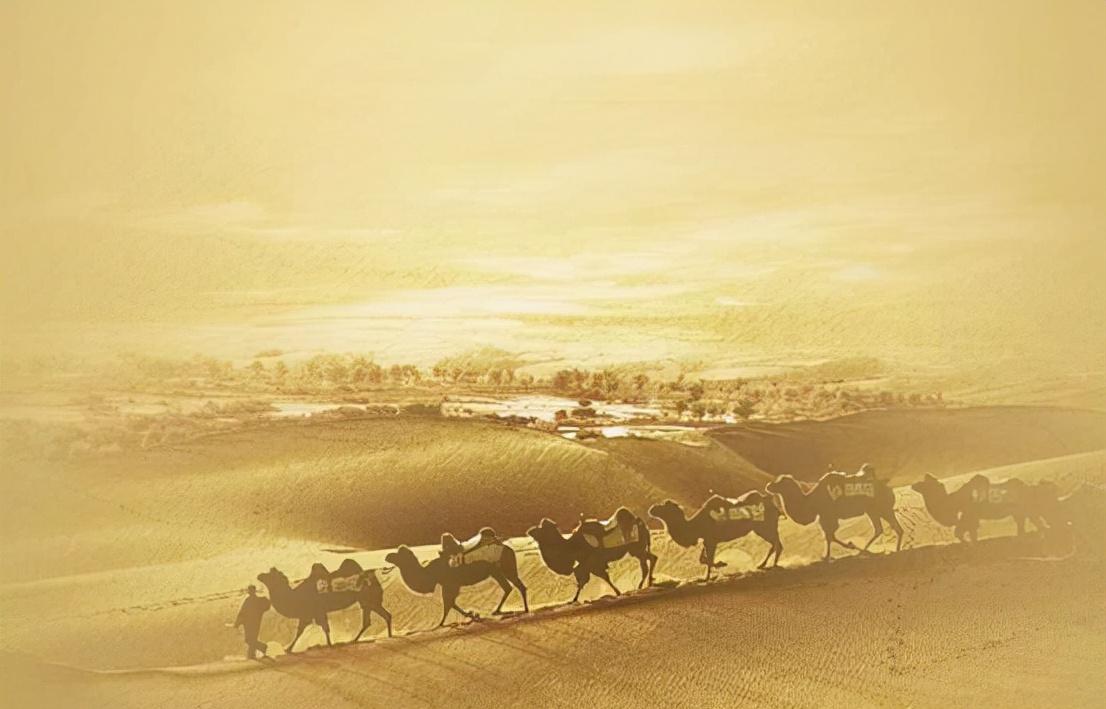
為什麼呢?這裡咱們先要說說什麼叫時差,弄清楚時差的原理。
簡單說,因為地球是在不停自轉,或者說以地球為參照系來看,太陽在繞着地球運動,不停從東向西轉動。這就使得,地球上東西相隔一定距離的兩個地方,他們各自所處本地的目前時間(指早晨、中午、晚上這種時間)不一樣。
靠近東邊的地方,先被太陽照到,時間上就比西邊的人要早。東邊比西邊早天亮,早太陽當頂,早天黑。如果兩地東西距離跨越了半個地球,那麼他們的時差為半天(12小時),白天黑夜正好相反:一個地方的正午,恰好是另一個地方的午夜。
再比如絲綢之路的終點英國,屬于0區,北京是東八區,時差為八小時。就是說英國在中午12點時,北京是晚上八點。或者說,北京太陽當頂之後的八小時(三分之一天)左右,英國才會太陽當頂。
那麼,人類如何能發現這種時差現象呢?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直接比較兩地的時間狀況。
舉個例子說,英國時區比北京晚了八個小時。那麼,如果我們能同時比較英國和北京的目前時間,就能覺察到時差。可是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在英國與北京啊,怎麼比較呢?就隻能由英國和北京兩地建立通信方式來同步。
一個英國人約翰和一個北京人張三,約好打電話聊天氣。他們通話的時候,張三告訴約翰,這會兒北京是晚上八點。而約翰告訴張三,這會兒英國是中午12點。這種差别,讓他們明白了時差。
或者,在沒有鐘表的情況下,張三告訴約翰,這會兒北京太陽當空,大約是正午。約翰告訴張三,這會兒英國天還沒亮,東方剛隐隐發白呢。過了八小時(一天的三分之一)左右,約翰告訴張三,這會兒英國是正午了,張三告訴約翰,北京太陽已經落山好一陣了。這樣,雙方也能明白時差。
簡單說就是,你得比較兩地在目前的時刻差距,或者比較兩地達到某個共同時刻的先後時間差距,才能覺察出時差。
另一種方式,攜帶某個精準的時刻或時間記錄工具,親身往返兩地,通過往返兩地所花的絕對時間長短,與出發前甲地和到達後乙地的時刻差距,從兩者之間的差額計算出時差。
比如,張三有一塊手表,走得基本上準确(比如每天誤差不超過幾分鐘)。他在北京調好了這一塊手表,然後帶着跑到英國去。這時候,他發現他的表明明指着晚上八點,說明這時候正是北京的晚上八點,可英國卻是太陽當頭的正午。這樣,他就能明白,北京和英國的時差。
或者更簡單的,張三在北京晚上八點上飛機,用了6個小時左右飛到倫敦(假設),按說此時北京應該是淩晨2點左右。可他卻發現英國此刻還是黃昏。這樣他也發現了時差。
然而對古人來說,這兩種情況都是不可能的。
那時候東西方之間的交通,騎行或者船行就是速度的上限。送消息的速度基本受制于人的行進速度。北京到英國之間的距離,在沒有電話、電報的情況下,送一條消息也需要許多天。這時候,張三在北京,絕不可能知道此時在英國是怎樣的早晚狀态。既然無法同步,那自然無法比較出時差。
第二種方法,理論上還是可以使用,但實際很困難。古人的計時工具大緻有兩類,一類是日晷,這個本來就是根據太陽運作來的,你跑到不同的時區,日晷也就失去了準确度。第二類是利用實體現象計時,比如更香、沙漏、水滴計時器等。這些東西主要是誤差比較大。
我們假設一下,張三有一個非常精确的沙漏,漏完一次正好是24小時(或者一小時、二小時都可以)。那麼,張三從北京一路向西,沿途不斷讓他的沙漏計時,每一次24小時候立刻重新計時。張三會發現。原本他是正午出發的時候開始第一次沙漏計時,但随着他不斷往西行進,漸漸當他開始新一輪沙漏計時的時刻,不再是正午,而是正午前面的上午。越往西,開始新一輪沙漏計時的時刻就越“早”。等他到了英國,這時候每一輪沙漏計時開始的時候,已經是天不亮的淩晨了。如此,張三得出結論,英國時間比北京晚了大約三分之一天。
以上是理想化的情況。但實際上,古人制作不出這麼精巧的沙漏,能恰好24小時,張三的操作不可能絕對精準。按照 古人的交通,從英國跑到北京,至少要好幾個月。八小時的時差,平攤到幾個月的旅程中,等于每天出現幾分鐘左右的時差。這個按照當時的統計工具,是完全沒法察覺出來的。張三在路上奔走時颠簸沙漏造成的誤差影響,都可能比這個要大。即使張三真的發現到英國後沙漏開始的時間和在北京不同,他也隻會懷疑自己這個所謂“一晝夜的沙漏”其實不是真正精确的一晝夜,而出現了偏差而已。
是以,古人沒法觀察到時差。
但是,不要把古人想象成傻子,認為古人就不知道時差的存在。
觀察不到,還可以推測。
畢竟,太陽東升西落,那麼西邊的将比東邊的更晚迎來黎明,也更晚送走黃昏,這個壓根不需要精确計算時差,就能直接從腦子裡獲得想象。
姑且不說西方人很早就提出了“地球”的概念,就連“天圓地方”說的中國古人,也完全能了解東部和西部的時差。
早期的神話故事《誇父逐日》,就是描寫巨人誇父向西邊緊緊追趕太陽。他固然是想用力量來留住太陽,但又何嘗不是企圖利用自己的速度追趕太陽行進的速度,利用時差,向西邊搶奪時間。
而宋朝詞人辛棄疾,更是以一首《木蘭花慢》,非常生動形象地描繪出了東西方的時差:
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别有人間,那邊才見,光影東頭?……
詞人看到月亮向西邊落下了,猜測會不會另有一處人間,剛剛才看到月亮從東邊升起來。這不就是時差麼?而且是很簡單的模型,隻要把傳統“天圓地方”的大地西邊再補上一塊居住着人的土地,那麼西下的月亮自然會去了那邊。
可見,盡管古人受制于技術,難以直接觀察時差,但時差對他們并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