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儒释道之间相互激荡,渐成合一之势。然而,三教合一的发展历程非常漫长,情形也很复杂,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特点。金代是三教关系史的重要节点,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的三教关系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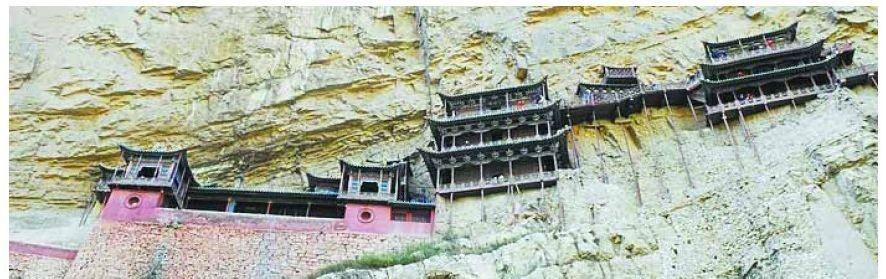
三教融合更加紧密
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自魏晋以来,三教之间经过长期磨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的格局。金代,三教之间的融合更加紧密,突出表现为彼此认可、互相肯定。李钧是金代儒士,他撰写的《修大云院记》开篇即阐述了三教合一之理:“释氏以凝寂不昧谓之禅定,老氏以有无一致谓之无为,孔氏以离形去智谓之坐忘。三者户牖虽殊,其揆一也。”李纯甫是金代著名佛教居士,平生以维护佛法为己任,但他也认同三教合一,认为三教“其心则同,其迹则异,其道则一,其教则三”。在他看来,三教理论虽有不同,但所证妙果归一,“道冠儒履,同入解脱法门;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戏”。
相比儒、释两家而言,全真道在三教融合方面的立场更为积极。创始人王重阳将“三教合一”作为立教原则,“不主一相,不拘一教”。他在传道实践中也一直贯彻这一主张。大定七年(1167)赴山东传道后,他明确提出“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建立的道教社团分别称为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王重阳非常注重用三教经典劝化道众,他劝门人诵读的书目中,既有道教的《道德经》,也有儒家的《孝经》、佛家的《般若心经》。关于三教之间的关系,王重阳还做了生动的比喻,“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其后继者继承了三教合一主张,丘处机诗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马钰亦云:“虽有儒生为益友,不成三教不团圆。”
金朝时期,儒释道顺应三教合一的历史潮流,在强调个性的同时更肯定三教的共性,进而对自己的理论体系做了一定调整,这种理论上的彼此融合为三教合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未出现强烈抵斥佛老的思潮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虽然三教合一是总体趋势,但彼此的冲突在所难免,特别是儒家为维护其正统地位,时有硕学大儒对佛道大加鞭挞。在彼此斗争中,文字、理论层面的讨伐尚在其次,唐代三武一宗灭佛对佛教的打击更为酷烈。
金代一些士人中间也存在排佛思潮,黄裳榜进士、应奉翰林文字宋九嘉不喜佛法,“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说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辞学之士多好译经润文,三恨大才而攻异端”。文学家王郁认为,“孔氏能兼佛老,佛老为世害”。文学名士刘从益在翰林院时,每与诸儒谈儒佛异同,“相与折难”。可见,金代儒士阶层的确存在排斥佛老的思潮,问题在于,这种思潮是否带有普遍性?对儒释道的关系产生了多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是否奉行排斥佛老的政策?
金代达官显贵乃至皇家帝室信仰佛老者不在少数,像李纯甫、元好问那样为佛老的生存和发展大声疾呼的儒者亦不乏其人。与此相反,儒士排斥佛老的声音却相对微弱,甚至从现有史籍上看不出代表性人物及思想流派。由此可知,金代儒士的反佛老言论是个别的、暂时的。
从国家层面来看,三教并用是金代统治集团的重要政策。以执政时间最长的金世宗为例,他在位期间兴学校、开科举、崇信儒学,但对儒学的尊宠并不意味着对佛道的轻视。相反,当时是金代佛道发展的重要阶段。就佛教来看,世宗即位之初,为筹措经费以应付军政开支,广开投状纳缗之路,度牒、师号、寺观名额均在出售之列,这一政策为创建寺观、壮大僧尼队伍、扩大佛教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就道教来看,金初创立的太一、大道、全真三个教派在这一时期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其重要表征是世宗屡次召见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例如,大定七年,召大道教始祖刘德仁居京城天长观,赐号东岳真人;大定二十七年,召王重阳弟子王处一于内殿,给三品俸,赐冠简紫衣;大定二十八年,召长春真人丘处机进京,并赐中袍。世宗之所以如此厚待佛老,是因为佛老宣扬的忠君体国、仁爱抑己、上报皇恩、下资邦福等主张,从根本上有助于巩固女真人的统治。在这一点上,佛老的功用与儒教完全一致,世宗皇帝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万机余暇,三教俱崇”。
综上所述,虽然金代社会存在某些儒者排斥佛老的现象,但这仅仅局限于泛泛而谈的层次,并未形成唐宋时期对佛道强烈抨击的局面。由于统治阶层奉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金代也没有出现类似三武一宗反佛、灭佛的极端事件。
儒家处于主导地位
三教合一意味着儒释道在理论体系上更为接近,相互关系更为融洽,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者的地位完全平等。自汉武帝以来,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与诸多大儒的提倡,儒学逐渐成为不可撼动的主流学说。尽管魏晋以来三教合一渐成趋势,但未能改变儒家主导三教关系的基本格局,金代亦然。
由于全真道的加入,金代三教合一思潮分外引人注目。王重阳、马钰、丘处机等人大力提倡三教合一,固然有其顺应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但未尝不是面对儒佛两教的强大压力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实际上,王重阳等人提倡三教合一,是为新道教的生存发展服务的,终极旨归是推动新道教居于儒释之上。在他们看来,“儒则博而寡要,道则简而易行,但清静无为,最上乘法也”,因此,王重阳所谓“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一家”不过是道家而已,三教合一应是道家主导下的三教合一。
在儒释道的地位之争中,佛教当然不甘落后。佛教发展到金代,已有近千年的深厚历史积淀,足以与儒道一争高下,名僧万松行秀认为佛法高于儒说,“吾门显诀,何愧于《大学》之篇哉”,既然佛经不输于儒典,佛教自然不低于儒教。因此,在佛门中人看来,佛家所谓三教归一是“会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终指归佛祖而已”,即佛家的三教归一当是在佛教主导下的三教归一。
面对佛道两教的竞争与挑战,儒学究竟能否继续维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儒家是否能够继续主导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金代儒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他们坚信儒家之说远高于佛道二教。金末刘祁曾对三教做过详细比较,在他看来,道教不过是方士之术,佛家是西方之教,唯有儒教,如“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礼文粲然,而治国治家焕有条理。赏罚绌陟立见,荣辱生死穷通”。在刘祁看来,佛道大谈因果轮回,但其前世今世、地狱天堂渺不可知,无可稽考;唯儒家之学可以修身理政、治国治家,其畅晓明白、治绩焕然,非佛道虚妄之说可比。在金代儒者眼中,佛道二教虽有可借鉴之处,但与孔子之学不可同日而语,“于圣人之教也,若饥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三教之中,只有儒学才是修身根本、治世良方。正因为如此,虽有佛教的发展、道教的兴盛,但金代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金代一方面承袭了魏晋隋唐以来的三教合一思潮,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三教合一思潮的内在取向与外在理路,从而形成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新景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代佛教研究”(12bzj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