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儒釋道之間互相激蕩,漸成合一之勢。然而,三教合一的發展曆程非常漫長,情形也很複雜,在不同曆史時期展現出不同特點。金代是三教關系史的重要節點,與以往相比,這一時期的三教關系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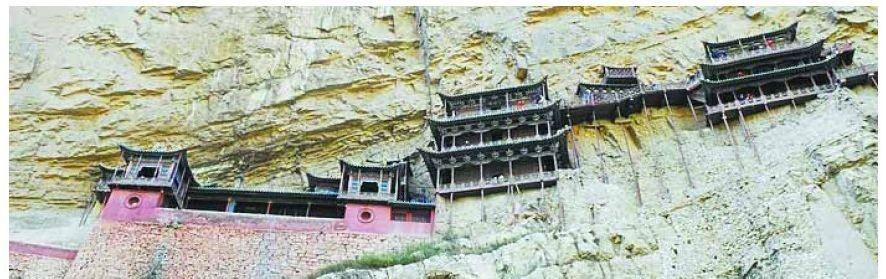
三教融合更加緊密
儒釋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幹部分,自魏晉以來,三教之間經過長期磨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為補充、共同發展的格局。金代,三教之間的融合更加緊密,突出表現為彼此認可、互相肯定。李鈞是金代儒士,他撰寫的《修大雲院記》開篇即闡述了三教合一之理:“釋氏以凝寂不昧謂之禅定,老氏以有無一緻謂之無為,孔氏以離形去智謂之坐忘。三者戶牖雖殊,其揆一也。”李純甫是金代著名佛教居士,平生以維護佛法為己任,但他也認同三教合一,認為三教“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在他看來,三教理論雖有不同,但所證妙果歸一,“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遊戲”。
相比儒、釋兩家而言,全真道在三教融合方面的立場更為積極。創始人王重陽将“三教合一”作為立教原則,“不主一相,不拘一教”。他在傳道實踐中也一直貫徹這一主張。大定七年(1167)赴山東傳道後,他明确提出“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在文登、甯海、福山、登州、萊州建立的道教社團分别稱為三教七寶會、三教金蓮會、三教三光會、三教玉華會、三教平等會。王重陽非常注重用三教經典勸化道衆,他勸門人誦讀的書目中,既有道教的《道德經》,也有儒家的《孝經》、佛家的《般若心經》。關于三教之間的關系,王重陽還做了生動的比喻,“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三教者,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其後繼者繼承了三教合一主張,丘處機詩雲:“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馬钰亦雲:“雖有儒生為益友,不成三教不團圓。”
金朝時期,儒釋道順應三教合一的曆史潮流,在強調個性的同時更肯定三教的共性,進而對自己的理論體系做了一定調整,這種理論上的彼此融合為三教合一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未出現強烈抵斥佛老的思潮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來,雖然三教合一是總體趨勢,但彼此的沖突在所難免,特别是儒家為維護其正統地位,時有碩學大儒對佛道大加鞭撻。在彼此鬥争中,文字、理論層面的讨伐尚在其次,唐代三武一宗滅佛對佛教的打擊更為酷烈。
金代一些士人中間也存在排佛思潮,黃裳榜進士、應奉翰林文字宋九嘉不喜佛法,“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辭學之士多好譯經潤文,三恨大才而攻異端”。文學家王郁認為,“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為世害”。文學名士劉從益在翰林院時,每與諸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可見,金代儒士階層的确存在排斥佛老的思潮,問題在于,這種思潮是否帶有普遍性?對儒釋道的關系産生了多大影響?更為重要的是,統治者是否奉行排斥佛老的政策?
金代達官顯貴乃至皇家帝室信仰佛老者不在少數,像李純甫、元好問那樣為佛老的生存和發展大聲疾呼的儒者亦不乏其人。與此相反,儒士排斥佛老的聲音卻相對微弱,甚至從現有史籍上看不出代表性人物及思想流派。由此可知,金代儒士的反佛老言論是個别的、暫時的。
從國家層面來看,三教并用是金代統治集團的重要政策。以執政時間最長的金世宗為例,他在位期間興學校、開科舉、崇信儒學,但對儒學的尊寵并不意味着對佛道的輕視。相反,當時是金代佛道發展的重要階段。就佛教來看,世宗即位之初,為籌措經費以應付軍政開支,廣開投狀納缗之路,度牒、師号、寺觀名額均在出售之列,這一政策為建立寺觀、壯大僧尼隊伍、擴大佛教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就道教來看,金初創立的太一、大道、全真三個教派在這一時期都得到進一步發展,其重要表征是世宗屢次召見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例如,大定七年,召大道教始祖劉德仁居京城天長觀,賜号東嶽真人;大定二十七年,召王重陽弟子王處一于内殿,給三品俸,賜冠簡紫衣;大定二十八年,召長春真人丘處機進京,并賜中袍。世宗之是以如此厚待佛老,是因為佛老宣揚的忠君體國、仁愛抑己、上報皇恩、下資邦福等主張,從根本上有助于鞏固女真人的統治。在這一點上,佛老的功用與儒教完全一緻,世宗皇帝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才“萬機餘暇,三教俱崇”。
綜上所述,雖然金代社會存在某些儒者排斥佛老的現象,但這僅僅局限于泛泛而談的層次,并未形成唐宋時期對佛道強烈抨擊的局面。由于統治階層奉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金代也沒有出現類似三武一宗反佛、滅佛的極端事件。
儒家處于主導地位
三教合一意味着儒釋道在理論體系上更為接近,互相關系更為融洽,但這并不意味着三者的地位完全平等。自漢武帝以來,經過曆代統治者的推崇與諸多大儒的提倡,儒學逐漸成為不可撼動的主流學說。盡管魏晉以來三教合一漸成趨勢,但未能改變儒家主導三教關系的基本格局,金代亦然。
由于全真道的加入,金代三教合一思潮分外引人注目。王重陽、馬钰、丘處機等人大力提倡三教合一,固然有其順應曆史發展的合理性,但未嘗不是面對儒佛兩教的強大壓力而采取的權宜之策。實際上,王重陽等人提倡三教合一,是為新道教的生存發展服務的,終極旨歸是推動新道教居于儒釋之上。在他們看來,“儒則博而寡要,道則簡而易行,但清靜無為,最上乘法也”,是以,王重陽所謂“吾将來使四海教風為一家”,“一家”不過是道家而已,三教合一應是道家主導下的三教合一。
在儒釋道的地位之争中,佛教當然不甘落後。佛教發展到金代,已有近千年的深厚曆史積澱,足以與儒道一争高下,名僧萬松行秀認為佛法高于儒說,“吾門顯訣,何愧于《大學》之篇哉”,既然佛經不輸于儒典,佛教自然不低于儒教。是以,在佛門中人看來,佛家所謂三教歸一是“會三聖人理性蘊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即佛家的三教歸一當是在佛教主導下的三教歸一。
面對佛道兩教的競争與挑戰,儒學究竟能否繼續維持自己的獨尊地位?儒家是否能夠繼續主導三教合一的曆史程序?金代儒者給予了肯定回答,他們堅信儒家之說遠高于佛道二教。金末劉祁曾對三教做過詳細比較,在他看來,道教不過是方士之術,佛家是西方之教,唯有儒教,如“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粲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绌陟立見,榮辱生死窮通”。在劉祁看來,佛道大談因果輪回,但其前世今世、地獄天堂渺不可知,無可稽考;唯儒家之學可以修身理政、治國治家,其暢曉明白、治績煥然,非佛道虛妄之說可比。在金代儒者眼中,佛道二教雖有可借鑒之處,但與孔子之學不可同日而語,“于聖人之教也,若饑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三教之中,隻有儒學才是修身根本、治世良方。正因為如此,雖有佛教的發展、道教的興盛,但金代儒學一直居于主導地位。
綜上所述,金代一方面承襲了魏晉隋唐以來的三教合一思潮,另一方面又呈現出一些新的時代特征,豐富和發展了三教合一思潮的内在取向與外在理路,進而形成了中國社會思想史的新景觀。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金代佛教研究”(12bzj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遼甯大學曆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