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华问渠
来源丨《贵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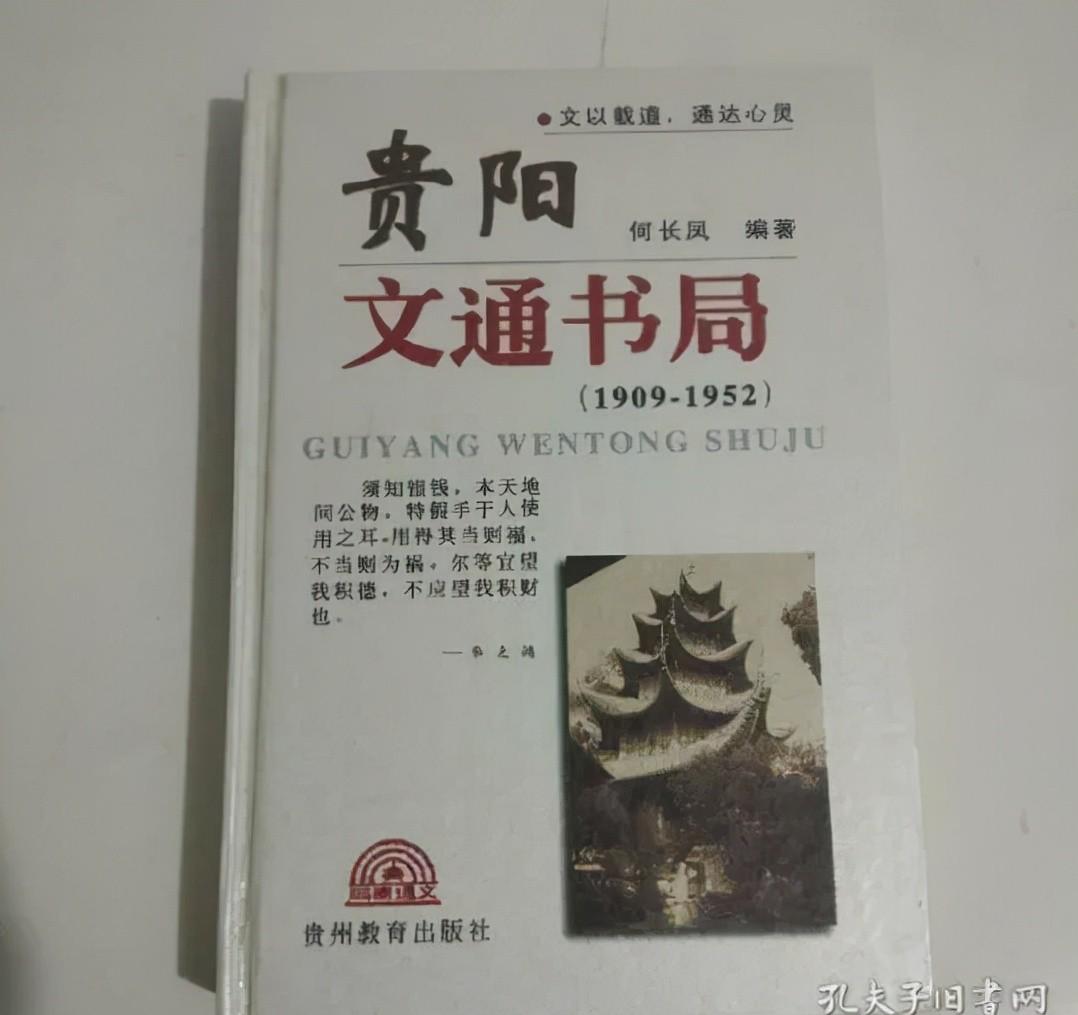
(一)
吾家原籍江西,清康熙间,祖人以行医来黔,两世而后,医道巾辍,后代以负贩食盐为主。迄先祖联辉号柽坞,仍继续业盐。适黔人丁葆桢任四川总督,特聘先祖赴川筹谋整顿盐政。后先祖承担黔边仁岸盐号一所,名永隆裕,告辞回黔,自行经营。
先祖一生,克已甚严,乐人为善,常刊印《六事箴言》及《菜根谭》诸书多部,分赠亲友,出门则挑载以从,遇有相信之人,即便赠送,以励德行。因赠送既多,感到刊版不便,闻上海巳有活字印刷,特选派同乡某某前往学习。不意所派非人,只图个人眼前私利,舍印刷而改学修理钟表,且不还乡。先祖之志未达,遽尔逝世。
先父之鸿号延厘,继承先祖遗志,以商以读,后曾任仁怀厅儒学训导。时永隆裕盐号经营数十年,颇有积蓄。先父以贵州地瘠民贫,欲为地方谋一点福利。会清廷停止科举,兴办学校,同时提倡兴办工业。适有乡先辈唐尔镛号慰慈、任可澄号志清,约先父创办。贵阳中学堂”,逾年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唐先生任监督,越年,先父亦任监督。因思贵州交通阻塞,新知识传播到黔,旷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若欲传播新知识,端赖书籍,莫若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竟之遗志,且印刷厂可以容纳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业之旨。于是下定决心,作抛砖引玉之图,创办了“贵阳文通书局”。时有遵义人田庆霖号雨亭,具干练才,办理遵义府遵义官书局中,为遵义中学印供讲义,成绩甚佳。先父商得田君及遵义府太守袁季九之同意,遂邀田负筹办之责。
(二)
一八九八年,田庆霖君率领学生二人,远赴日本东京,先行购得铅印部分全套设备,计有铅印对开机四部,四开,六开印机各二部,圆盘机四部。铸字排版部门,电镀制模纸型俱全。踩炉二部,手摇炉五部,书边铅条刨床—二部,切铅条刀一部。铸字铜模,宋体字、楷体字头号至六号铜模;日文、英文头号至五号铜模,楷体及印刷体各号俱备。此外,标点符号、大小花边,均属齐全。装订部分,切纸、切书刀,洋装圆背、烫金、打排眼、挂线等机,应有尽有。逾年运到,即着手安装。
至于技术工人,田君于去日本之前,即在遵义招有学生七十人,附学于遵义官书局,并且铸字、印刷、装订都各聘有教师训导。以故,机器一到,将学生调省,由教师指导,从事安装。工作进展神速。
文通书局印刷厂房,设置于贵阳市中心王家巷(今勇烈路)。首先第一部印刷之书,为乡前贤郑子尹先生所辑《播雅》。
田君待铅印开工之后,又另率学生三人,再赴日本东京,采购石印部分,又购网全张纸石印大机一部,对开机一部,落石、制版机二部,手机五部,石油动力引擎二部,轧墨机二部。并聘有日本技术工人三人,来局指导。所派去之学生,指定学习影印,及制造锌、铜版。三色玻璃版,及雕刻金属等。需用照相机及药品,均备置齐全。石印部分首先印刷之书,为影印英文教科书。彩色印刷为本局成立刊发了广告。
开工后所用纸张,舶来品占大多数,至于国产毛边、龙章、宣纸之类,为数不多。
书局之组织,先父任局主,田庆霖君任经理。工务部分,有铅印部、铸字部、检排部、装订部、影印及金属制版部。石印部分,有石印绘图部、制版部、石印机器部,每部设部长一人,管理本部工作分配及记录工作与业务情况。部长之上,均各设教习一人,教导技术。另有校对室,专司校书缮写。事务部分,只有一人负银钱出入之责。无论创办资金、营业收入、按月工薪支付,原材料收购,伙食杂用支出等等,统系此人负担全责。另派数人帮同写算,兼作门市营业。此外,一人专负当地采购零星材料,以及办理伙食等杂务。仓存购进整批材料之保管取用,别有专责保管登记三人。
全局机器之运转,除石印大机使用石油引擎而外,其余无论大小机器,概赖人工摇动,有副工若干入专司其事。伙食一日三餐,全部由书局供应。职工全部住宿局内,厨房供应菜饭。负责全局各地清洁卫生的工友,经常有十人以上。工作方面时时需要木工,制作大小木料制件,复经常雇用木工二、三人。开局之初,全局职工,约有一百人左右。
职工之待遇,除局主不支薪外,日本技工订有合约,其余教习、部长,统系每人每月生洋十五两或十四两;技术工人,由六两至十两,按其技术之情况酌定;学徒每人每月发给浆洗费铜钱一千文;校对员等于部长;副工每人每月生洋四两;事务部分的职员等于技工;厨房杂务各工友二两至四两,视事务之繁简酌定。
创办之初,但求设备完全,资金并无限制。就机器之购买与搬运而言,由于当时贵州公路未通,凡属外购机器、材料,纸张等,均由日本起运至上海,再由长江溯流轮运到重庆后,便需改用人力或马驮运来贵阳。一般小件起码需时十六、七天;至于六抬、八抬,则需二十余天;十二抬以上;需时尤多。故搬运费用超过购置费用。此外购置和修建厂房宿舍以及往来旅费等等,截至铅、石两部完全开工之日止,总计花费资金约生银二十万两左右。
(三)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贵州亦于是年秋间宣布反正,成立贵州军政府。不久中华民国成立。至此中国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全国政治面貌,有所变更,陆续颁布了许多新的政令,都必需广为传播,普告全国。各级政府推行政令和财政税收所需一切票据、文件、表册等,都要随时赶行印刷,贵州军政府并未办有印刷厂,凡有印件,均委托文通书局代印。袁世凯:窃国称帝,滇黔首义,兴师讨逆,财政收入不敷,曾委托文通书局代印黔币三百万元。当时新闻杂志,政府公报,民办日报,以及民众团体定期刊物等,印件日益增加。原有工人不敷应用,乃陆续招生训练,兼收女生。新生学习时间,并不额定三年,只要专心学习,基本能独立操作,即视其能力之强弱,酌给适当工资,以资鼓励.此时最感困难者,乃纸张供应异常紧张。
华之鸿
文通开工以来,用纸多向省外购运,往往缓不济急,而且质量规格多不合需要。只有派人四出采购本省生产的纸张,如都匀、遵义、郎岱、兴义之构皮白纸,绥阳之竹料纸。但质量粗劣,尺码参差,大小宽窄不一。经协助改进,勉强可以济用。但因各地造纸坊户,概属农村副业,农忙时间即便停产,故随时仍感供不应求。为彻底解决纸张供应问题,文通乃特派人赴四川夹江,雇请多名手工抄竹料纸工人来黔,与在修文西山地区僧庙住持,签订合同,租借厂地,于山上华严寺、瞿昙寺及山麓小鹿窝三地,成立了三个手工造纸厂。收购山上竹木,以作原料、燃料之用。合计三厂纸槽,约有三十余架,正、副工近百人,每日可产纸三万多张,名曰西山纸.随后有西山厂工人去黔西天灵寺,仿照西山纸办法,造出一种竹料纸,名曰天灵纸。西山、天灵两种纸张,质地均紧细光滑,而且系专业造纸,产量稳定。其他各县之构料白纸,经文通派人协助改进操作后,质量有所提高,亦渐能符合需要。普通印件用纸问题,至此大致得到解决。至于精致印刷,以及必需的重磅套色纸张,仍感困难。先父乃请田庆霖君,又率学生数人,去日本采购造纸机器,准备自行设厂自造。经过数年奔走,略有眉目。乃就大南门外虹桥,成立永丰机器造纸厂,于一九一九年正式开工。用木料、稻草、构皮、竹料、废纸等作原料,造出了超贡、超光、庆霖、混同各种厚薄纸张,质量甚佳,在全国造纸业中,独树一格。惟是造纸机耗费甚巨,田庆霖君复去上海,聘请制造机器的技术工人,自行绘图、设计制作。田君尚拟重赴日本入造纸机器制造厂学习,旋因病未果,后竟客死上海。
袁世凯败死而后,中央政权落入北洋军阀之手。各省军阀,据地自雄。连年相互混战,军用自感不足。于是,不惜增加苛税,以至民生日惫。贵州自不例外。文通在此情况下,乃决定营业方针,即在托印件较少时,便从事翻印地方文献,意在发前人之幽光,启后生之观感。计先后印成如《巢经巢诗钞》,《母教录》,《鄙亭诗钞》、《桐埜诗钞》、《平黔纪略》、《成山庐稿》、《并陇纪程诗》、《四川官运盐岸汇编》、《农政全书》,及贵州通志局后改为文献征辑馆托印之《黔南丛书》,每集十本,共印八集。随后又代印续修《贵州通志》整部,计有一百零五册。此外约有十县,委托代印地方志。后来又接受委托,翻印佛教经律论三藏典籍为数亦多。
(四)
二九二七年,书局增设图书部,专事贩运京沪各书局及出版社发行的教科图书、文具、体育用品等来黔,供应文教界采用。先与上海中华书局订立合同,由文通担任该局对贵州推销各级学校教利用书。在此之前,惟赖商务印书馆在贵阳所设分馆一家供应。但因国内战事不休,运途多阻,教科书运到过迟,甚至有整个学期已经终了,而教科书犹未运到,教育界深以为苦,而莫可如何。自文通代销中华书局教科书后,重视时效,供应情况有所改善。于是,上海之世界、开明、大东各书局,先后亦委托文通代为推销其出版物。因之商务印书馆之业务,遂为各书局所分润,较之过去一家独揽,营业自然锐减,便决定撤销贵州分馆。惟该馆历史悠久,出版书籍亦多,若果听其断然离去,则对贵州书业之繁荣不无影响。文通乃特向该馆商洽承顶,另行约伙筹设商务印书馆贵阳特约经销处,代该馆继续在贵州推售。至此,凡属国内书局出版之图书,文通均可运黔代销。贵州文教界从此不特有书可读,而且有取舍之余地,咸谓为文通对地方文化之一大贡献。
一九二九年春,天候亢旱,因储藏包运书籍之油纸保管不慎,突然起火焚烧,适当例假日,抢救不及,致将印刷厂房烧毁十之七、八,铅印活字,完全熔化。所幸铸字铜模,损伤不大,印刷、装订、铸字各种机器,亦无多大毁损。石印部门,得免波及。总的情况,是铅印部分有待于恢复整理,一时不能继续工作。当时承印政府文件,自然不能中辍;而承印的一份大型日报,若果停歇,社会势必顿成喑哑。尤其机关办公以及财政税收票据之类印件,每日必需,不容延缓。公私各方,交相督促,希望文通早日复工;而文通本身,亦感到对社会责任綦重,亟当努力恢复。但铅印厂房一时赶修不及,乃将铅印部门暂迁至东门附近大觉精舍,轮派工人,日夜赶铸铅字。日报改用石印,减少篇幅,日出一大张;政府公报则转托湖北宜昌印刷厂代印。经三个月的努力,设备始逐渐恢复。是年秋,贵州省政府拟办地方银行,委托文通代印凹凸版钞票一百万元。
文通特派人到上海雕刻原版,顺便购回铅印对开机两部,大元盘机两部,硬印机四部,电镀用一瓧发电机一部,空气爆炸柴油机引擎一部,以充实生产能力。印完钞票后,于一九三七年,就被烧厂房原址,将厂房修复,仍将铅印部门迁回原地,业务渐趋正常。
从一九三五年起,蒋介石政权控制了贵州,国民党各派人物,分居省政枢要,为争权夺利,每暗中相互抨击。各办有大型日报一份,借报纸作为攻诘对方的工具,而这些报纸又都是委托文通代印。其后随伪中央军来黔者,还有许多文化人,亦兴办小报多种,同样系文通代印。加上其他印件,工作之紧张繁杂,莫过此时。工人增至四百以上,仍感不敷用,尚需去重庆雇聘检排工人多人来黔帮助。但一切印刷、工料等费用,均先垫付,事后又未能如期收回,宕延日久,积欠愈多。而且政权经常易主,欠费往往随之化为乌有,文通以此受累至深,欲谢绝承印而不可能,甚至有派兵持枪迫令代印之举。然而全局职工一日三餐,未能或缺。不得已,认息挪借,以维现状。数字既大,为时不短,举债亦难。只好谋诸职工,节衣缩食,共度难关。工资不能按月关发,仅就实际困难者,酌量支付。伙食方面,不吃油肉。职工之穷困,可谓极矣。先父一九三二年逝世之后,我负责文通之经营管理,回忆当年遭受反动统治者之种种压迫,迄今犹觉心悸。
(五)
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以来,蒋介石持不抵抗主义,节节退让,沿江、沿海一带国土,相继陷敌。很多文化教育机构和工商企业,纷纷向贵阳搬迁。即以出版印刷事业而言,上海之商务、中华、开明各书局,均在贵阳成立分局,文通以前代理各局之推销业务,均由其自行办理。同时由各地迁来彩印、铅印、大小印刷同业,不下十余家。而贵阳地区业务有限,骤然增加许多书店和印刷厂,营业自不景气,文通书局亦深受影响。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贵阳遭受日寇飞机轰炸,市中心顿成焦土。文通乃暂迁至大西门外华家山继续开业。
此时,黔人马济华(曾任教育部秘书长)、谢六逸(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均为文化教育界颇负盛名者,两人皆随大夏大学迁至贵阳。我为发展文通业务,乃商谋马、谢两君,筹组编辑所,为文通增添出版部门。马、谢两君应允之后,特将文通原有机构,另行改组,采取总管理处制。我任总经理,聘蓝平辅君任协理,负责统筹全局一切事宜。下设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机构,分工负责。马济华任编辑所所长,谢六逸任副所长。马在大夏担任总务长,兼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职务,不时往返川黔,因便代文通向各方面学人广事宣传联系,由文通书局发出聘书,聘为编辑、审查委员等之专家学者达三、四百人,并陆续交来稿件很多。谢六逸经常住所,偕张永立,浦鸿基主持编务。
文通改组后,曾编印综合性《文讯月刊》一种,报道学术动态以及国内外重要事件,还刊登一些出版消息。闻一多之死,曾出专刊以悼之。不期年,文通出版书刊,包括大学从书、夫文,教学、理化,建筑工程、铁道各方面著作,尤其于医学方面较多,总计二百余种。为了争取学术地位,对黄色书刊稿件,一律谢绝,亦不接受印刷。还编印发行了小学教科书语文,算术两种课本。业务由是蒸蒸日上.但资金方面,确实深感不敷。我乃下定决心,集中一切力量,务期将文通办好。于是陆续变卖我家祖传之不动产,以资济用。
后来伪教育部为了统一编印发行“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乃指令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文通等七家书局,组成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供应数函按各局资历和资金情况协商分配。计商务、中华、正中各占百分之二十三,世界、开明、大东、文通依次分别各占百分之十二、九、七、三。用纸均由伪教育部贷给外汇,统一向国外进口。文通在“七联”负担供应任务的比例虽小,但从全国统计,为数仍大。为搞好发行,除增设驻渝办事处外,并且设了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四个分局。
一九四三、四五年,编辑所正、副所长马济华,谢六逸两君先后病逝,乃于四六年聘顾颉刚、白寿彝为编辑所正副所长。顾为国内有名的历史学家,当时在重庆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伪中央参议员;白寿彝亦系历史学者,在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这时,全国学者多集中重庆,编辑所乃由贵阳迁渝。所内实际工作,白君负责较多。但昆、渝相距遥远,往返不便,又决定将编辑所再由重庆迁到昆明。
一九四六年,“七联”迁沪,文通乃增设驻沪办事处,先后又设上海、长沙、广州三个分局。编辑所由昆明迁至苏州,副所长白寿彝辞去云南大学教授职务,常往苏州,协同所长顾颉刚主持文通编务,继续出版学术性新书数百种。书籍印刷,除由贵阳本局印刷厂自印外,并在上海委托他代厂印。编辑所同人中,具有先进思想者颇不乏人。迫于反动统治淫威,不敢公然暴露,特选印外国译本,输送先进思想,每于《文讯》月刊中,转载国外评论,暗示国人。
反动统治临近崩溃一、二年间,苛捐杂税层出不穷,通货膨胀,物价日增。文通经营,常常感到周转不灵。此时不动产变卖殆尽,全局薪金伙食之费,刻不容缓。迫不得已,只好出付重息,设法贷款,维持现状。末了,反动政府以改定国家金融、实行金本位为名,发行金元券、银元券,规定旧日货币,须四百元方能折合新券一元。文通借贷之款,除按当时反动政府规定折还而外,别无可偿之物。许多亲朋,不免遭受拖累。至今每一念及,无不介介于怀也。
一九四九年春,上海解放,文通驻沪办事处与内地联络常生梗阻。编辑所同人,多离开本所另就新职,于是编辑所无形停歇。是年冬,贵阳解放,文通印刷厂及各地分局,虽仍照旧开办,但鼎革之初,社会仍处动荡之中,业务稀少,欲其安定恢复,必然有一定之过程。当时收入不敷抵偿支出,深感维持之不易。
(六)
一九五〇年秋,中央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文通曾蒙大会特邀参加。此次大会决定,今后出版,应由出版总署统筹主持。各书局之出版稿件,必须呈送出版总署审定方能出版。并由各书局先行认定出版科目,报署存查。文通承诺继续出版医学书籍。至于各书局原设各地分局,统行合并,同时改组发行机构。文通因分局无多,以后合并改组之会议,便未参加。不久,文通之上海分局,并入卫生出版社;广州、重庆分局,参加当地联营;成都、昆明分局,则申报停业。贵阳总管理处、印刷厂、分局,因资金竭尽,且有债务无法清偿,当造具资产负债清册(除文通企业以外,我家所有在云南个旧锡务公司,中国银行、世界书局、四川建国机器造币厂等股分,一并列入资产之内),呈请贵州省人民政府处理。荷蒙政府派遣工作小组到局清理,并准予接收。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文通书局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厂。
贵阳文通书局,自一八九八年创建,迄一九五二年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厂,经历五十有四年。原有文通业务记录多半散失,上述概况,仅凭我个人记忆,语焉不详,只其概略耳。
一九六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