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華問渠
來源丨《貴陽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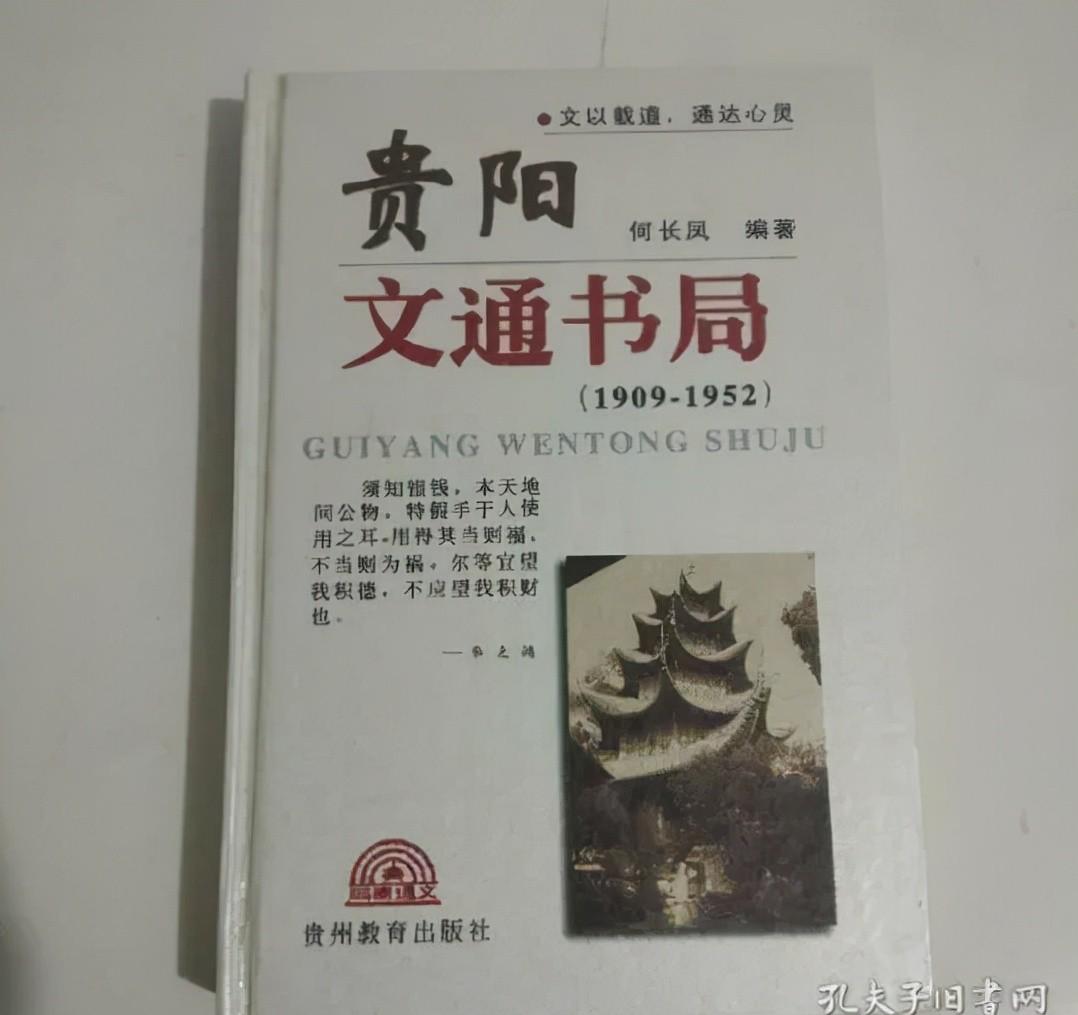
(一)
吾家原籍江西,清康熙間,祖人以行醫來黔,兩世而後,醫道巾辍,後代以負販食鹽為主。迄先祖聯輝号柽塢,仍繼續業鹽。适黔人丁葆桢任四川總督,特聘先祖赴川籌謀整頓鹽政。後先祖承擔黔邊仁岸鹽号一所,名永隆裕,告辭回黔,自行經營。
先祖一生,克已甚嚴,樂人為善,常刊印《六事箴言》及《菜根譚》諸書多部,分贈親友,出門則挑載以從,遇有相信之人,即便贈送,以勵德行。因贈送既多,感到刊版不便,聞上海巳有活字印刷,特選派同鄉某某前往學習。不意所派非人,隻圖個人眼前私利,舍印刷而改學修理鐘表,且不還鄉。先祖之志未達,遽爾逝世。
先父之鴻号延厘,繼承先祖遺志,以商以讀,後曾任仁懷廳儒學訓導。時永隆裕鹽号經營數十年,頗有積蓄。先父以貴州地瘠民貧,欲為地方謀一點福利。會清廷停止科舉,興辦學校,同時提倡興辦工業。适有鄉先輩唐爾镛号慰慈、任可澄号志清,約先父創辦。貴陽中學堂”,逾年更名為“貴州通省公立中學堂”,唐先生任監督,越年,先父亦任監督。因思貴州交通阻塞,新知識傳播到黔,曠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則貴州文化,将永遠落于全國各省之後。若欲傳播新知識,端賴書籍,莫若創辦一所規模較大之書局,既可繼承先祖未竟之遺志,且印刷廠可以容納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業之旨。于是下定決心,作抛磚引玉之圖,創辦了“貴陽文通書局”。時有遵義人田慶霖号雨亭,具幹練才,辦理遵義府遵義官書局中,為遵義中學印供講義,成績甚佳。先父商得田君及遵義府太守袁季九之同意,遂邀田負籌辦之責。
(二)
一八九八年,田慶霖君率領學生二人,遠赴日本東京,先行購得鉛印部分全套裝置,計有鉛印對開機四部,四開,六開印機各二部,圓盤機四部。鑄字排版部門,電鍍制模紙型俱全。踩爐二部,手搖爐五部,書邊鉛條刨床—二部,切鉛條刀一部。鑄字銅模,宋體字、楷體字頭号至六号銅模;日文、英文頭号至五号銅模,楷體及印刷體各号俱備。此外,标點符号、大小花邊,均屬齊全。裝訂部分,切紙、切書刀,洋裝圓背、燙金、打排眼、挂線等機,應有盡有。逾年運到,即着手安裝。
至于技術勞工,田君于去日本之前,即在遵義招有學生七十人,附學于遵義官書局,并且鑄字、印刷、裝訂都各聘有教師訓導。以故,機器一到,将學生調省,由教師指導,從事安裝。工作進展神速。
文通書局印刷廠房,設定于貴陽市中心王家巷(今勇烈路)。首先第一部印刷之書,為鄉前賢鄭子尹先生所輯《播雅》。
田君待鉛印開工之後,又另率學生三人,再赴日本東京,采購石印部分,又購網全張紙石印大機一部,對開機一部,落石、制版機二部,手機五部,石油動力引擎二部,軋墨機二部。并聘有日本技術勞工三人,來局指導。所派去之學生,指定學習影印,及制造鋅、銅版。三色玻璃版,及雕刻金屬等。需用照相機及藥品,均備置齊全。石印部分首先印刷之書,為影印英文教科書。彩色印刷為本局成立刊發了廣告。
開工後所用紙張,舶來品占大多數,至于國産毛邊、龍章、宣紙之類,為數不多。
書局之組織,先父任局主,田慶霖君任經理。工務部分,有鉛印部、鑄字部、檢排部、裝訂部、影印及金屬制版部。石印部分,有石印繪圖部、制版部、石印機器部,每部設部長一人,管理本部工作配置設定及記錄工作與業務情況。部長之上,均各設教習一人,教導技術。另有校對室,專司校書繕寫。事務部分,隻有一人負銀錢出入之責。無論創辦資金、營業收入、按月工薪支付,原材料收購,夥食雜用支出等等,統系此人負擔全責。另派數人幫同寫算,兼作門市營業。此外,一人專負當地采購零星材料,以及辦理夥食等雜務。倉存購進整批材料之保管取用,别有專責保管登記三人。
全局機器之運轉,除石印大機使用石油引擎而外,其餘無論大小機器,概賴人工搖動,有副工若幹入專司其事。夥食一日三餐,全部由書局供應。職工全部住宿局内,廚房供應菜飯。負責全局各地清潔衛生的工友,經常有十人以上。工作方面時時需要木工,制作大小木料制件,複經常雇用木工二、三人。開局之初,全局職工,約有一百人左右。
職工之待遇,除局主不支薪外,日本技工訂有合約,其餘教習、部長,統系每人每月生洋十五兩或十四兩;技術勞工,由六兩至十兩,按其技術之情況酌定;學徒每人每月發給漿洗費銅錢一千文;校對員等于部長;副工每人每月生洋四兩;事務部分的職員等于技工;廚房雜務各工友二兩至四兩,視事務之繁簡酌定。
創辦之初,但求裝置完全,資金并無限制。就機器之購買與搬運而言,由于當時貴州公路未通,凡屬外購機器、材料,紙張等,均由日本起運至上海,再由長江溯流輪運到重慶後,便需改用人力或馬馱運來貴陽。一般小件起碼需時十六、七天;至于六擡、八擡,則需二十餘天;十二擡以上;需時尤多。故搬運費用超過購置費用。此外購置和修建廠房宿舍以及往來旅費等等,截至鉛、石兩部完全開工之日止,總計花費資金約生銀二十萬兩左右。
(三)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貴州亦于是年秋間宣布反正,成立貴州軍政府。不久中華民國成立。至此中國結束了二千餘年的封建統治,全國政治面貌,有所變更,陸續頒布了許多新的政令,都必需廣為傳播,普告全國。各級政府推行政令和财政稅收所需一切票據、檔案、表冊等,都要随時趕行印刷,貴州軍政府并未辦有印刷廠,凡有印件,均委托文通書局代印。袁世凱:竊國稱帝,滇黔首義,興師讨逆,财政收入不敷,曾委托文通書局代印黔币三百萬元。當時新聞雜志,政府公報,民辦日報,以及群眾團體定期刊物等,印件日益增加。原有勞工不敷應用,乃陸續招生訓練,兼收女生。新生學習時間,并不額定三年,隻要專心學習,基本能獨立操作,即視其能力之強弱,酌給适當工資,以資鼓勵.此時最感困難者,乃紙張供應異常緊張。
華之鴻
文通開工以來,用紙多向省外購運,往往緩不濟急,而且品質規格多不合需要。隻有派人四出采購本省生産的紙張,如都勻、遵義、郎岱、興義之構皮白紙,綏陽之竹料紙。但品質粗劣,尺碼參差,大小寬窄不一。經協助改進,勉強可以濟用。但因各地造紙坊戶,概屬農村副業,農忙時間即便停産,故随時仍感供不應求。為徹底解決紙張供應問題,文通乃特派人赴四川夾江,雇請多名手工抄竹料紙勞工來黔,與在修文西山地區僧廟住持,簽訂合同,租借廠地,于山上華嚴寺、瞿昙寺及山麓小鹿窩三地,成立了三個手工造紙廠。收購山上竹木,以作原料、燃料之用。合計三廠紙槽,約有三十餘架,正、副工近百人,每日可産紙三萬多張,名曰西山紙.随後有西山廠勞工去黔西天靈寺,仿照西山紙辦法,造出一種竹料紙,名曰天靈紙。西山、天靈兩種紙張,質地均緊細光滑,而且系專業造紙,産量穩定。其他各縣之構料白紙,經文通派人協助改進操作後,品質有所提高,亦漸能符合需要。普通印件用紙問題,至此大緻得到解決。至于精緻印刷,以及必需的重磅套色紙張,仍感困難。先父乃請田慶霖君,又率學生數人,去日本采購造紙機器,準備自行設廠自造。經過數年奔走,略有眉目。乃就大南門外虹橋,成立永豐機器造紙廠,于一九一九年正式開工。用木料、稻草、構皮、竹料、廢紙等作原料,造出了超貢、超光、慶霖、混同各種厚薄紙張,品質甚佳,在全國造紙業中,獨樹一格。惟是造紙機耗費甚巨,田慶霖君複去上海,聘請制造機器的技術勞工,自行繪圖、設計制作。田君尚拟重赴日本入造紙機器制造廠學習,旋因病未果,後竟客死上海。
袁世凱敗死而後,中央政權落入北洋軍閥之手。各省軍閥,據地自雄。連年互相混戰,軍用自感不足。于是,不惜增加苛稅,以至民生日憊。貴州自不例外。文通在此情況下,乃決定營業方針,即在托印件較少時,便從事翻印地方文獻,意在發前人之幽光,啟後生之觀感。計先後印成如《巢經巢詩鈔》,《母教錄》,《鄙亭詩鈔》、《桐埜詩鈔》、《平黔紀略》、《成山廬稿》、《并隴紀程詩》、《四川官運鹽岸彙編》、《農政全書》,及貴州通志局後改為文獻征輯館托印之《黔南叢書》,每集十本,共印八集。随後又代印續修《貴州通志》整部,計有一百零五冊。此外約有十縣,委托代印地方志。後來又接受委托,翻印佛教經律論三藏典籍為數亦多。
(四)
二九二七年,書局增設圖書部,專事販運京滬各書局及出版社發行的教科圖書、文具、體育用品等來黔,供應文教界采用。先與上海中華書局訂立合同,由文通擔任該局對貴州推銷各級學校教利用書。在此之前,惟賴商務印書館在貴陽所設分館一家供應。但因國内戰事不休,運途多阻,教科書運到過遲,甚至有整個學期已經終了,而教科書猶未運到,教育界深以為苦,而莫可如何。自文通代銷中華書局教科書後,重視時效,供應情況有所改善。于是,上海之世界、開明、大東各書局,先後亦委托文通代為推銷其出版物。因之商務印書館之業務,遂為各書局所分潤,較之過去一家獨攬,營業自然銳減,便決定撤銷貴州分館。惟該館曆史悠久,出版書籍亦多,若果聽其斷然離去,則對貴州書業之繁榮不無影響。文通乃特向該館商洽承頂,另行約夥籌設商務印書館貴陽特約經銷處,代該館繼續在貴州推售。至此,凡屬國内書局出版之圖書,文通均可運黔代銷。貴州文教界從此不特有書可讀,而且有取舍之餘地,鹹謂為文通對地方文化之一大貢獻。
一九二九年春,天候亢旱,因儲藏包運書籍之油紙保管不慎,突然起火焚燒,适當例假日,搶救不及,緻将印刷廠房燒毀十之七、八,鉛印活字,完全熔化。所幸鑄字銅模,損傷不大,印刷、裝訂、鑄字各種機器,亦無多大毀損。石印部門,得免波及。總的情況,是鉛印部分有待于恢複整理,一時不能繼續工作。當時承印政府檔案,自然不能中辍;而承印的一份大型日報,若果停歇,社會勢必頓成喑啞。尤其機關辦公以及财政稅收票據之類印件,每日必需,不容延緩。公私各方,交相督促,希望文通早日複工;而文通本身,亦感到對社會責任綦重,亟當努力恢複。但鉛印廠房一時趕修不及,乃将鉛印部門暫遷至東門附近大覺精舍,輪派勞工,日夜趕鑄鉛字。日報改用石印,減少篇幅,日出一大張;政府公報則轉托湖北宜昌印刷廠代印。經三個月的努力,裝置始逐漸恢複。是年秋,貴州省政府拟辦地方銀行,委托文通代印凹凸版鈔票一百萬元。
文通特派人到上海雕刻原版,順便購回鉛印對開機兩部,大元盤機兩部,硬印機四部,電鍍用一瓧發電機一部,空氣爆炸柴油機引擎一部,以充實生産能力。印完鈔票後,于一九三七年,就被燒廠房原址,将廠房修複,仍将鉛印部門遷回原地,業務漸趨正常。
從一九三五年起,蔣介石政權控制了貴州,國民黨各派人物,分居省政樞要,為争權奪利,每暗中互相抨擊。各辦有大型日報一份,借報紙作為攻诘對方的工具,而這些報紙又都是委托文通代印。其後随僞中央軍來黔者,還有許多文化人,亦興辦小報多種,同樣系文通代印。加上其他印件,工作之緊張繁雜,莫過此時。勞工增至四百以上,仍感不敷用,尚需去重慶雇聘檢排勞工多人來黔幫助。但一切印刷、工料等費用,均先墊付,事後又未能如期收回,宕延日久,積欠愈多。而且政權經常易主,欠費往往随之化為烏有,文通以此受累至深,欲謝絕承印而不可能,甚至有派兵持槍迫令代印之舉。然而全局職工一日三餐,未能或缺。不得已,認息挪借,以維現狀。數字既大,為時不短,舉債亦難。隻好謀諸職工,節衣縮食,共度難關。工資不能按月關發,僅就實際困難者,酌量支付。夥食方面,不吃油肉。職工之窮困,可謂極矣。先父一九三二年逝世之後,我負責文通之經營管理,回憶當年遭受反動統治者之種種壓迫,迄今猶覺心悸。
(五)
一九三七年抗日軍興以來,蔣介石持不抵抗主義,節節退讓,沿江、沿海一帶國土,相繼陷敵。很多文化教育機構和工商企業,紛紛向貴陽搬遷。即以出版印刷事業而言,上海之商務、中華、開明各書局,均在貴陽成立分局,文通以前代理各局之推銷業務,均由其自行辦理。同時由各地遷來彩印、鉛印、大小印刷同業,不下十餘家。而貴陽地區業務有限,驟然增加許多書店和印刷廠,營業自不景氣,文通書局亦深受影響。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貴陽遭受日寇飛機轟炸,市中心頓成焦土。文通乃暫遷至大西門外華家山繼續開業。
此時,黔人馬濟華(曾任教育部秘書長)、謝六逸(曾任上海複旦大學教授),均為文化教育界頗負盛名者,兩人皆随大夏大學遷至貴陽。我為發展文通業務,乃商謀馬、謝兩君,籌組編輯所,為文通增添出版部門。馬、謝兩君應允之後,特将文通原有機構,另行改組,采取總管理處制。我任總經理,聘藍平輔君任協理,負責統籌全局一切事宜。下設編輯所、印刷所、發行所三機構,分工負責。馬濟華任編輯所所長,謝六逸任副所長。馬在大夏擔任總務長,兼有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職務,不時往返川黔,因便代文通向各方面學人廣事宣傳聯系,由文通書局發出聘書,聘為編輯、審查委員等之專家學者達三、四百人,并陸續交來稿件很多。謝六逸經常住所,偕張永立,浦鴻基主持編務。
文通改組後,曾編印綜合性《文訊月刊》一種,報道學術動态以及國内外重要事件,還刊登一些出版消息。聞一多之死,曾出專刊以悼之。不期年,文通出版書刊,包括大學從書、夫文,教學、理化,建築工程、鐵道各方面著作,尤其于醫學方面較多,總計二百餘種。為了争取學術地位,對黃色書刊稿件,一律謝絕,亦不接受印刷。還編印發行了國小教科書國文,算術兩種課本。業務由是蒸蒸日上.但資金方面,确實深感不敷。我乃下定決心,集中一切力量,務期将文通辦好。于是陸續變賣我家祖傳之不動産,以資濟用。
後來僞教育部為了統一編印發行“國定本”中、國小教科書,乃指令商務、中華、世界、開明、大東,正中、文通等七家書局,組成中、國小教科書“聯合供應處”。供應數函按各局資曆和資金情況協商配置設定。計商務、中華、正中各占百分之二十三,世界、開明、大東、文通依次分别各占百分之十二、九、七、三。用紙均由僞教育部貸給外彙,統一向國外進口。文通在“七聯”負擔供應任務的比例雖小,但從全國統計,為數仍大。為搞好發行,除增設駐渝辦事處外,并且設了成都、重慶、昆明、貴陽四個分局。
一九四三、四五年,編輯所正、副所長馬濟華,謝六逸兩君先後病逝,乃于四六年聘顧颉剛、白壽彜為編輯所正副所長。顧為國内有名的曆史學家,當時在重慶任複旦大學教授兼僞中央參議員;白壽彜亦系曆史學者,在昆明任雲南大學教授。這時,全國學者多集中重慶,編輯所乃由貴陽遷渝。所内實際工作,白君負責較多。但昆、渝相距遙遠,往返不便,又決定将編輯所再由重慶遷到昆明。
一九四六年,“七聯”遷滬,文通乃增設駐滬辦事處,先後又設上海、長沙、廣州三個分局。編輯所由昆明遷至蘇州,副所長白壽彜辭去雲南大學教授職務,常往蘇州,協同所長顧颉剛主持文通編務,繼續出版學術性新書數百種。書籍印刷,除由貴陽本局印刷廠自印外,并在上海委托他代廠印。編輯所同人中,具有先進思想者頗不乏人。迫于反動統治淫威,不敢公然暴露,特選印外國譯本,輸送先進思想,每于《文訊》月刊中,轉載國外評論,暗示國人。
反動統治臨近崩潰一、二年間,苛捐雜稅層出不窮,通貨膨脹,物價日增。文通經營,常常感到周轉不靈。此時不動産變賣殆盡,全局薪金夥食之費,刻不容緩。迫不得已,隻好出付重息,設法貸款,維持現狀。末了,反動政府以改定國家金融、實行金本位為名,發行金元券、銀元券,規定舊日貨币,須四百元方能折合新券一進制。文通借貸之款,除按當時反動政府規定折還而外,别無可償之物。許多親朋,不免遭受拖累。至今每一念及,無不介介于懷也。
一九四九年春,上海解放,文通駐滬辦事處與内地聯絡常生梗阻。編輯所同人,多離開本所另就新職,于是編輯所無形停歇。是年冬,貴陽解放,文通印刷廠及各地分局,雖仍照舊開辦,但鼎革之初,社會仍處動蕩之中,業務稀少,欲其安定恢複,必然有一定之過程。當時收入不敷抵償支出,深感維持之不易。
(六)
一九五〇年秋,中央出版總署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出版會議,文通曾蒙大會特邀參加。此次大會決定,今後出版,應由出版總署統籌主持。各書局之出版稿件,必須呈送出版總署審定方能出版。并由各書局先行認定出版科目,報署存查。文通承諾繼續出版醫學書籍。至于各書局原設各地分局,統行合并,同時改組發行機構。文通因分局無多,以後合并改組之會議,便未參加。不久,文通之上海分局,并入衛生出版社;廣州、重慶分局,參加當地聯營;成都、昆明分局,則申報停業。貴陽總管理處、印刷廠、分局,因資金竭盡,且有債務無法清償,當造具資産負債清冊(除文通企業以外,我家所有在雲南個舊錫務公司,中國銀行、世界書局、四川建國機器造币廠等股分,一并列入資産之内),呈請貴州省人民政府處理。荷蒙政府派遣工作小組到局清理,并準予接收。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文通書局并入貴州人民印刷廠。
貴陽文通書局,自一八九八年建立,迄一九五二年并入貴州人民印刷廠,經曆五十有四年。原有文通業務記錄多半散失,上述概況,僅憑我個人記憶,語焉不詳,隻其概略耳。
一九六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