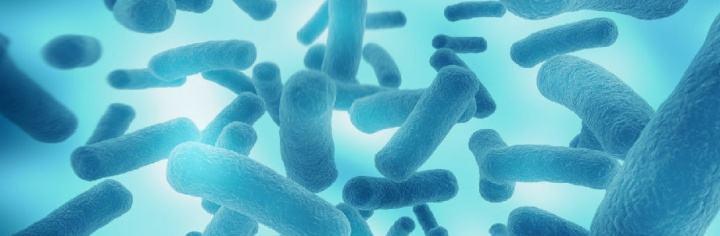
春节期间,明明是应该享受阖家团圆的时刻,却偏出现了病毒疫情这档子坏事。
起初是不看,逃避,一心一意地过节,何况,那疫情离我们还很遥远,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未尝不可。
随着朋友圈转发的信息越来越多,营造出人人都如惊弓之鸟的气氛,愤怒、悲观、绝望的情绪充斥着网络。新闻报道、疫区故事、媒体态度、自媒体观点,还有各类谣言,大量的信息涌现出来,让人避之不及。
于是也便跟着转发一些,与此同时,疫情从武汉逐渐向全国蔓延,确诊病例每天都在增加,从省到市到县,病毒一步步向我们靠近。
惊恐之余,口罩之下,疫情成为我们每天都必谈的一个话题,相关文章也必会点开浏览。
这几天,有的自媒体骂武汉红十字会,有的骂武汉官员,有的替当初那勇于说真话的八位医生打抱不平,有的希望武汉人早日能够吃上热干面,还有的教人独立思考。
面对这些嬉笑怒骂、说理说教的信息,渐渐的,又将人挤压进能够躲避世事的洞穴之中。可又分明是躲不开的,无非是觉得这些过载的信息多无意义。
无意义的或许不是那些文章本身,而是认为那些阅后即焚的文章无法改变现状,从而让人陷入某种虚无的情绪之中。
这种短暂的虚无情绪,是源于自我的无能,进而对一切进行否定。
于此,个人原因无疑充当着主动力量,舆论环境则被动地发挥作用,最终在个体身上造成了这一时的虚无局面。如果仅有我一人如此,那权且当作是矫情之言吧。
1918年,38岁的鲁迅整日抄写古碑,那时他大概也是处于某种虚无境地的。他明白,喊醒其他人毫无用处,大家都会死于这间封闭的铁屋。
后来钱玄同对他说:“然而几个人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他写出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如今,到底是谁起来了?有多少人起来了?那些起来了的人,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思和意图构造一篇文章的呢?
精准的叙事技巧往往包裹着消费主义的外衣,哪怕发挥了实际效能,退潮之后,那洋洋洒洒的文字便沦为荒漠中的颗颗沙粒。
如果说形式和过程不重要,只要毁坏了铁屋,产生这样的结果才重要,这类观点似乎又会令一帮人陷入虚无主义。
当代文学层面的叙事危机,只能在浅薄的信息流之中找到临时出口,哪怕这果真是个出口,望向前方,却依然看不到出路。
在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之前,总之是离不开虚无的。
尽管如此,虚无也只属于一帮人,对于沉浸在信息中的人来说,恰好又是在对抗虚无。虚无者都是在对抗中败下阵来的人,只能另谋出路,且避免与胜利者达成共识。
贾樟柯曾在某访谈中说:“如果停滞在共识的讨论之中,那是某种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艺术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无法提供共识性的服务。”
他还提到,情感是人最后的密码。
以我之见,情感有表层和深层之分,那情感表层的密码几乎人人皆知,深层的密码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能够引起共鸣的文字信息,正是解开表层情感的密码,充当着教育世人的作用。
灾难性事件,展现在文学或电影艺术中总是滞后的,起码会退居二线。但这也只是存在于当代的一种现象,是信息飞速传播带来的结果,而这信息本身也便位列于一线。
反面案例是,鲁迅的小说在当时就能引起轰动效应,在那个信息传播相对滞后的时代,文学艺术方能充当反应社会现状的排头兵。
总之,虚无者是对那些即时的、狂轰滥炸的信息怀有敌意和不满的,并对过往文学艺术掌控话语权的那个时代持有执念。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落败者的一种不屑于顾的情绪伪装。
好在情绪总是摇摆不定的,这一时的遁逃无法衡量一个人的绝对性格,大概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但也不排除好不起来的可能,不排除会有更多人逐渐进入这种虚无的状态,从而形成一种虚无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