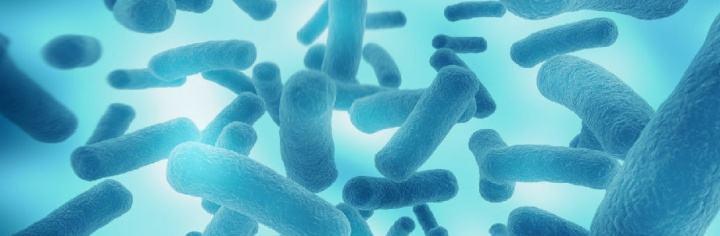
春節期間,明明是應該享受阖家團圓的時刻,卻偏出現了病毒疫情這檔子壞事。
起初是不看,逃避,一心一意地過節,何況,那疫情離我們還很遙遠,做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也未嘗不可。
随着朋友圈轉發的資訊越來越多,營造出人人都如驚弓之鳥的氣氛,憤怒、悲觀、絕望的情緒充斥着網絡。新聞報道、疫區故事、媒體态度、自媒體觀點,還有各類謠言,大量的資訊湧現出來,讓人避之不及。
于是也便跟着轉發一些,與此同時,疫情從武漢逐漸向全國蔓延,确診病例每天都在增加,從省到市到縣,病毒一步步向我們靠近。
驚恐之餘,口罩之下,疫情成為我們每天都必談的一個話題,相關文章也必會點開浏覽。
這幾天,有的自媒體罵武漢紅十字會,有的罵武漢官員,有的替當初那勇于說真話的八位醫生打抱不平,有的希望武漢人早日能夠吃上熱幹面,還有的教人獨立思考。
面對這些嬉笑怒罵、說理說教的資訊,漸漸的,又将人擠壓進能夠躲避世事的洞穴之中。可又分明是躲不開的,無非是覺得這些過載的資訊多無意義。
無意義的或許不是那些文章本身,而是認為那些閱後即焚的文章無法改變現狀,進而讓人陷入某種虛無的情緒之中。
這種短暫的虛無情緒,是源于自我的無能,進而對一切進行否定。
于此,個人原因無疑充當着主動力量,輿論環境則被動地發揮作用,最終在個體身上造成了這一時的虛無局面。如果僅有我一人如此,那權且當作是矯情之言吧。
1918年,38歲的魯迅整日抄寫古碑,那時他大概也是處于某種虛無境地的。他明白,喊醒其他人毫無用處,大家都會死于這間封閉的鐵屋。
後來錢玄同對他說:“然而幾個人起來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于是,他寫出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
如今,到底是誰起來了?有多少人起來了?那些起來了的人,又是懷着怎樣的心思和意圖構造一篇文章的呢?
精準的叙事技巧往往包裹着消費主義的外衣,哪怕發揮了實際效能,退潮之後,那洋洋灑灑的文字便淪為荒漠中的顆顆沙粒。
如果說形式和過程不重要,隻要毀壞了鐵屋,産生這樣的結果才重要,這類觀點似乎又會令一幫人陷入虛無主義。
當代文學層面的叙事危機,隻能在淺薄的資訊流之中找到臨時出口,哪怕這果真是個出口,望向前方,卻依然看不到出路。
在找不到真正的出路之前,總之是離不開虛無的。
盡管如此,虛無也隻屬于一幫人,對于沉浸在資訊中的人來說,恰好又是在對抗虛無。虛無者都是在對抗中敗下陣來的人,隻能另謀出路,且避免與勝利者達成共識。
賈樟柯曾在某訪談中說:“如果停滞在共識的讨論之中,那是某種教育應該承擔的責任,不是藝術家應該承擔的責任,我們無法提供共識性的服務。”
他還提到,情感是人最後的密碼。
以我之見,情感有表層和深層之分,那情感表層的密碼幾乎人人皆知,深層的密碼卻充滿了不确定性。能夠引起共鳴的文字資訊,正是解開表層情感的密碼,充當着教育世人的作用。
災難性事件,展現在文學或電影藝術中總是滞後的,起碼會退居二線。但這也隻是存在于當代的一種現象,是資訊飛速傳播帶來的結果,而這資訊本身也便位列于一線。
反面案例是,魯迅的小說在當時就能引起轟動效應,在那個資訊傳播相對滞後的時代,文學藝術方能充當反應社會現狀的排頭兵。
總之,虛無者是對那些即時的、狂轟濫炸的資訊懷有敵意和不滿的,并對過往文學藝術掌控話語權的那個時代持有執念。它是自然而然産生的,是落敗者的一種不屑于顧的情緒僞裝。
好在情緒總是搖擺不定的,這一時的遁逃無法衡量一個人的絕對性格,大概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但也不排除好不起來的可能,不排除會有更多人逐漸進入這種虛無的狀态,進而形成一種虛無的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