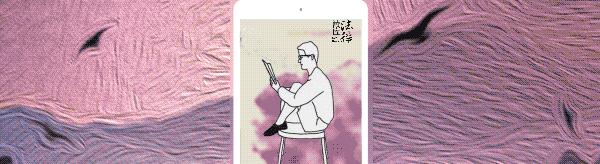
作者:周安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
来源:微信公众号 叽呱叽呱
《十二怒汉》是一部美国老电影,也是法律人几乎必看的一部电影。故事讲述了一起午夜凶杀案——一名男孩涉嫌杀害父亲、被控一级谋杀罪,最终被陪审团认定为无罪的故事。
12名陪审员来源于各个职业,有建筑师、钟表匠、证券经纪人、广告公司经理、还有卖桔子酱的推销员,等等。
陪审团的合议规则是:如果对被告的罪行存在合理怀疑,必须作出无罪的判定;如果没有合理怀疑,也必须判定被告有罪。既可以先讨论,也可以不经过讨论直接投票判定;既可以举手表决,也可以秘密投票。但无论是认定无罪或有罪,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陪审团成员都必须作出一致结论,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大多数陪审员一开始对案件态度并不严肃,有的觉得运气好,碰到的是谋杀案,新奇刺激,有的甚至想尽快“走一下过场”,好赶回去看球赛。加之此前已经参加了六天的庭审,对案件过程已有了解,陪审团成员一致同意先不进行讨论,直接进行投票,如果结论一致,就可以立即结束合议。
表决结果很快就出来了。12名陪审团成员中,11人判定被告有罪,仅有1名叫戴维斯的陪审员最后作出了反对意见。他表示,对被告有罪,他也不知道自己信或不信。但因为是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能5分钟就作出决定呢?没有经过讨论,就把一个孩子送上死刑椅,自己很难做到!万一我们错了呢!
正是这位“关键少数”,推进了案件的反转。
由于未能作出一致结论,陪审团同意对案件事实展开讨论,每一名陪审员开始陈述自己的理由。
“这种人很容易犯罪”,因为男孩出生、成长于贫民窟,而且有打架斗殴等前科劣迹,有的陪审员在发言中显示出对男孩的偏见;有的则表示“我就是觉得他有罪,没有人证明他无罪”;有的根本就说不出理由,表示庭审一开始就认定被告有罪,现在只是寻找其犯罪动机。
其实,上述认定男孩有罪的理由并不充分。恰恰相反,很多错案的发生,正是司法工作人员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者是有罪推定、将无罪证明责任强加给被告一方,或者是未审先定、先定后审,“从人到证”而不是“从证到人”等原因造成的。
当然,也有的陪审员“理直气壮”,认为被告人事先购买了凶器——一把看起来非常特别的弹簧刀,现场也查获了同样的弹簧刀,而且还有两名证人一致证明是被告人就是凶手。
由于大家均认定被告有罪,个别陪审员甚至情绪激烈,指责戴维斯纯粹是在浪费大家时间。重压之下,戴维斯进行了妥协。他提议进行第二轮表决,表决采取秘密投票方式,如果大家仍然一致判定被告有罪,他将服从大家的意见。但只要有一名陪审员也认为被告无罪,他就将保留观点,案件仍必须讨论下去。
主持合议的陪审员一张一张地宣读着投票结果,就在大家以为大局已定、被告人将被判有罪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张“无罪”票。
谁又在“捣蛋”?一位年老的陪审员表示,是自己投了反对票。他说,戴维斯先生独自一人对抗大家的反对、嘲笑很不容易,“他孤注一掷争取支持,我就支持他。”“我也接受这个男孩可能有罪,但我想多听听证词!”
案件再次进入讨论环节,更多的细节被发现、争论。
粗略的来看,似乎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占有很大优势,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两名证人证明被告有罪。
第一名证人是住在被告楼下的一位老人。他证明自己听见被告大叫“我要杀了你”,接着听到了被告父亲倒地的声音,然后他看到被告逃了出去。
第二名证人是住在被告楼对面的一位女士。她表示,透过当时刚好经过的高架列车车窗,她看到被告用刀捅向父亲,自已受到惊吓还报了警。
但经过深入讨论,这两名证人的证明都有问题。
如果如第二名证人所言,被告杀害其父亲的时候,正好有高架列车通过,因为列车通过时会有很大的噪声,第一名证人是不太可能听清被告“我要杀了你”的叫声;而且,该证人腿部有残疾,根据讨论现场的模拟,他不可能在其声称的15秒内,从床上爬起来并走到走廊尽头,进而目睹被告逃走。
陪审员们接着又发现,第二位女邻居是一名近视患者,在夜晚灯光昏暗,她失眠在床、未戴眼镜的情况下(根据生活经验,陪审员们基本都同意任何人在睡觉的时候戴眼镜可能性很小),是不太可能透过刚好驶过的列车车窗看到男孩行凶的。
另一方面,被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尽管从法律上被告无需自证清白,但其能否对自己的行为作合理解释,直接会影响到陪审员们的内心确信)。被告称自己买了一把弹簧刀,可能是在看电影的路上从口袋里滑掉了,犯罪现场杀害其父亲的正是同样的一把弹簧刀。被告称自己晚上去看了电影,但是电影叫什么名字、主角是谁,第一次讯问时他都讲不清。
不过,这里面也并非无懈可击。陪审员戴维斯现场出示了一把其在被告家附件所买、与凶器一模一样的弹簧刀,说明这把刀“并不特殊”。被告还是一名孩子,父亲突然遇害、自己又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被抓,在极度恐惧、慌张的情况下,一时记不清所看电影的名字和主角也是可能的。
其实,通过深入分析,大家发现案件还有不少其他疑点。
男孩在夜里三点多钟回到家里被抓获,如果是其杀人,他为什么不逃跑,而是回来自投罗网?既然自投罗网,为什么又不认罪?
如果是想取走弹簧刀,但经检查,刀上并没有男孩的指纹。如果凶手是他,犯罪后仔细擦掉指纹,说明他很冷静。既然已擦掉指纹、消除证据,为什么又回来取刀?如果要取刀,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携刀逃走?
再退一步说,如果男孩认为是在深夜,回来有可能不被发现,但女邻居声称自己发出了尖叫。既然相信证人听到男孩声称要杀害父亲,也就应当相信男孩可能听到尖叫,此时男孩应当知道犯罪已被人发现,况且他很冷静,为什么要返回犯罪现场?
证明男孩有罪的链条在崩溃,陪审员们的内心确信受到了动摇。讨论过程中,又进行了几轮投票,最后只有一名陪审员仍坚持认为男孩有罪。但这名陪审员突然放弃,同意男孩无罪,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把对儿子的气愤投射到了男孩身上,他也有一个很不争气的儿子。
12:0,最终陪审团一致判定男孩无罪。
可能有人会问,从开始大家几乎都判定男孩有罪,后来只是因为一个人的反对,逐渐改变了案件结果,难道开始大家都错了,难道男孩真的无罪吗?
其实,合议结果也并不是说男孩就是无罪的。只是因为存在合理怀疑,不能认定他有罪。任何人都不能穿透时空回到案发现场,司法官也没有上帝视角。虽然可以通过证据发现、粘贴、构建事实,但现实中,证据短缺是一种常态。认定当事人是否有罪,其实都是在赌一种概率。也许赌对、也许赌错。但是只要存在合理怀疑,就应当放过。这实际上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放过一个真正的罪犯,是做错了一道题。但如果错抓错判,是做错了两道题,因为既冤枉了一个好人,又放过了一个坏人。
可能还有人要问,陪审团合议规则合理吗?为什么要形成一致意见?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同一件案件,不同的人看法不同是正常的,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更合理吗?
尊重少数意见,在此基础上谋求共识,可能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我的理解是,在此规则下,每个人无论是认定被告有罪或无罪,不但要说服自己,而且要说服别人。这就促使大家深入了解案件,加强观点交流、碰撞,“真理越辩越明”,有利于最大化地“逼近”案件事实。
对上述规则应用的极致是:没有反对意见,一致意见就不能通过。
通用汽车的传奇CEO阿尔弗雷德·斯隆在某一次高管会议上问:“先生们,我们已经对这个决定达成了统一的意见,对吗?”大家都点头表示赞同。
令人惊讶的是,斯隆接着说:“好吧!这样的话我建议我们把这个问题的后续讨论推迟到下一次会议。让我们多些时间来提出不同的看法,也许大家能对这个决定有更多了解。”
斯隆就敏锐地认识到:一致认同,很可能并不是好事。
为了保证兼听则明,使决策更加科学,有些机构包括一些大的公司,会设置一些反对派角色,就像天主教会中的魔鬼代言人制度。魔鬼代言人的职责是,对教会的封圣候选人进行调查和质疑,从而形成更严格的考察。
我在想,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制度设计中,律师的角色不就像是反对派?律师并不是为所谓的“坏人”说话,而是为了让司法机关“兼听则明”。对死刑等犯罪实施强制辩护,不也正是“没有反对意见,一致意见就不能通过”原理?!所以,尊重和保障律师权益,正是司法公正、司法文明的应有之义。
投稿转载说明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