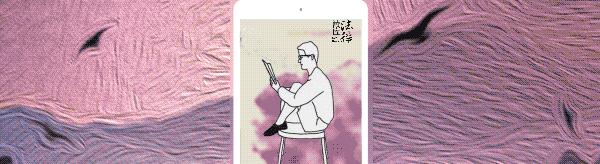
作者:周安甯淮安市人民檢察院
來源:微信公衆号 叽呱叽呱
《十二怒漢》是一部美國老電影,也是法律人幾乎必看的一部電影。故事講述了一起午夜兇殺案——一名男孩涉嫌殺害父親、被控一級謀殺罪,最終被陪審團認定為無罪的故事。
12名陪審員來源于各個職業,有建築師、鐘表匠、證券經紀人、廣告公司經理、還有賣桔子醬的推銷員,等等。
陪審團的合議規則是:如果對被告的罪行存在合理懷疑,必須作出無罪的判定;如果沒有合理懷疑,也必須判定被告有罪。既可以先讨論,也可以不經過讨論直接投票判定;既可以舉手表決,也可以秘密投票。但無論是認定無罪或有罪,無論采用哪種方式,陪審團成員都必須作出一緻結論,而不是少數服從多數。
大多數陪審員一開始對案件态度并不嚴肅,有的覺得運氣好,碰到的是謀殺案,新奇刺激,有的甚至想盡快“走一下過場”,好趕回去看球賽。加之此前已經參加了六天的庭審,對案件過程已有了解,陪審團成員一緻同意先不進行讨論,直接進行投票,如果結論一緻,就可以立即結束合議。
表決結果很快就出來了。12名陪審團成員中,11人判定被告有罪,僅有1名叫戴維斯的陪審員最後作出了反對意見。他表示,對被告有罪,他也不知道自己信或不信。但因為是人命關天的事,怎麼能5分鐘就作出決定呢?沒有經過讨論,就把一個孩子送上死刑椅,自己很難做到!萬一我們錯了呢!
正是這位“關鍵少數”,推進了案件的反轉。
由于未能作出一緻結論,陪審團同意對案件事實展開讨論,每一名陪審員開始陳述自己的理由。
“這種人很容易犯罪”,因為男孩出生、成長于貧民窟,而且有打架鬥毆等前科劣迹,有的陪審員在發言中顯示出對男孩的偏見;有的則表示“我就是覺得他有罪,沒有人證明他無罪”;有的根本就說不出理由,表示庭審一開始就認定被告有罪,現在隻是尋找其犯罪動機。
其實,上述認定男孩有罪的理由并不充分。恰恰相反,很多錯案的發生,正是司法從業人員先入為主的偏見,或者是有罪推定、将無罪證明責任強加給被告一方,或者是未審先定、先定後審,“從人到證”而不是“從證到人”等原因造成的。
當然,也有的陪審員“理直氣壯”,認為被告人事先購買了兇器——一把看起來非常特别的彈簧刀,現場也查獲了同樣的彈簧刀,而且還有兩名證人一緻證明是被告人就是兇手。
由于大家均認定被告有罪,個别陪審員甚至情緒激烈,指責戴維斯純粹是在浪費大家時間。重壓之下,戴維斯進行了妥協。他提議進行第二輪表決,表決采取秘密投票方式,如果大家仍然一緻判定被告有罪,他将服從大家的意見。但隻要有一名陪審員也認為被告無罪,他就将保留觀點,案件仍必須讨論下去。
主持合議的陪審員一張一張地宣讀着投票結果,就在大家以為大局已定、被告人将被判有罪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張“無罪”票。
誰又在“搗蛋”?一位年老的陪審員表示,是自己投了反對票。他說,戴維斯先生獨自一人對抗大家的反對、嘲笑很不容易,“他孤注一擲争取支援,我就支援他。”“我也接受這個男孩可能有罪,但我想多聽聽證詞!”
案件再次進入讨論環節,更多的細節被發現、争論。
粗略的來看,似乎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占有很大優勢,其中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有兩名證人證明被告有罪。
第一名證人是住在被告樓下的一位老人。他證明自己聽見被告大叫“我要殺了你”,接着聽到了被告父親倒地的聲音,然後他看到被告逃了出去。
第二名證人是住在被告樓對面的一位女士。她表示,透過當時剛好經過的高架列車車窗,她看到被告用刀捅向父親,自已受到驚吓還報了警。
但經過深入讨論,這兩名證人的證明都有問題。
如果如第二名證人所言,被告殺害其父親的時候,正好有高架列車通過,因為列車通過時會有很大的噪聲,第一名證人是不太可能聽清被告“我要殺了你”的叫聲;而且,該證人腿部有殘疾,根據讨論現場的模拟,他不可能在其聲稱的15秒内,從床上爬起來并走到走廊盡頭,進而目睹被告逃走。
陪審員們接着又發現,第二位女鄰居是一名近視患者,在夜晚燈光昏暗,她失眠在床、未戴眼鏡的情況下(根據生活經驗,陪審員們基本都同意任何人在睡覺的時候戴眼鏡可能性很小),是不太可能透過剛好駛過的列車車窗看到男孩行兇的。
另一方面,被告似乎難以自圓其說(盡管從法律上被告無需自證清白,但其能否對自己的行為作合了解釋,直接會影響到陪審員們的内心确信)。被告稱自己買了一把彈簧刀,可能是在看電影的路上從口袋裡滑掉了,犯罪現場殺害其父親的正是同樣的一把彈簧刀。被告稱自己晚上去看了電影,但是電影叫什麼名字、主角是誰,第一次訊問時他都講不清。
不過,這裡面也并非無懈可擊。陪審員戴維斯現場出示了一把其在被告家附件所買、與兇器一模一樣的彈簧刀,說明這把刀“并不特殊”。被告還是一名孩子,父親突然遇害、自己又被當成犯罪嫌疑人被抓,在極度恐懼、慌張的情況下,一時記不清所看電影的名字和主角也是可能的。
其實,通過深入分析,大家發現案件還有不少其他疑點。
男孩在夜裡三點多鐘回到家裡被抓獲,如果是其殺人,他為什麼不逃跑,而是回來自投羅網?既然自投羅網,為什麼又不認罪?
如果是想取走彈簧刀,但經檢查,刀上并沒有男孩的指紋。如果兇手是他,犯罪後仔細擦掉指紋,說明他很冷靜。既然已擦掉指紋、消除證據,為什麼又回來取刀?如果要取刀,當時為什麼不直接攜刀逃走?
再退一步說,如果男孩認為是在深夜,回來有可能不被發現,但女鄰居聲稱自己發出了尖叫。既然相信證人聽到男孩聲稱要殺害父親,也就應當相信男孩可能聽到尖叫,此時男孩應當知道犯罪已被人發現,況且他很冷靜,為什麼要傳回犯罪現場?
證明男孩有罪的鍊條在崩潰,陪審員們的内心确信受到了動搖。讨論過程中,又進行了幾輪投票,最後隻有一名陪審員仍堅持認為男孩有罪。但這名陪審員突然放棄,同意男孩無罪,原因是他發現自己把對兒子的氣憤投射到了男孩身上,他也有一個很不争氣的兒子。
12:0,最終陪審團一緻判定男孩無罪。
可能有人會問,從開始大家幾乎都判定男孩有罪,後來隻是因為一個人的反對,逐漸改變了案件結果,難道開始大家都錯了,難道男孩真的無罪嗎?
其實,合議結果也并不是說男孩就是無罪的。隻是因為存在合理懷疑,不能認定他有罪。任何人都不能穿透時空回到案發現場,司法官也沒有上帝視角。雖然可以通過證據發現、粘貼、建構事實,但現實中,證據短缺是一種常态。認定當事人是否有罪,其實都是在賭一種機率。也許賭對、也許賭錯。但是隻要存在合理懷疑,就應當放過。這實際上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放過一個真正的罪犯,是做錯了一道題。但如果錯抓錯判,是做錯了兩道題,因為既冤枉了一個好人,又放過了一個壞人。
可能還有人要問,陪審團合議規則合理嗎?為什麼要形成一緻意見?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同一件案件,不同的人看法不同是正常的,少數服從多數不是更合理嗎?
尊重少數意見,在此基礎上謀求共識,可能是這個案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我的了解是,在此規則下,每個人無論是認定被告有罪或無罪,不但要說服自己,而且要說服别人。這就促使大家深入了解案件,加強觀點交流、碰撞,“真理越辯越明”,有利于最大化地“逼近”案件事實。
對上述規則應用的極緻是:沒有反對意見,一緻意見就不能通過。
通用汽車的傳奇CEO阿爾弗雷德·斯隆在某一次高管會議上問:“先生們,我們已經對這個決定達成了統一的意見,對嗎?”大家都點頭表示贊同。
令人驚訝的是,斯隆接着說:“好吧!這樣的話我建議我們把這個問題的後續讨論推遲到下一次會議。讓我們多些時間來提出不同的看法,也許大家能對這個決定有更多了解。”
斯隆就敏銳地認識到:一緻認同,很可能并不是好事。
為了保證兼聽則明,使決策更加科學,有些機構包括一些大的公司,會設定一些反對派角色,就像天主教會中的魔鬼代言人制度。魔鬼代言人的職責是,對教會的封聖候選人進行調查和質疑,進而形成更嚴格的考察。
我在想,在國家追訴犯罪的制度設計中,律師的角色不就像是反對派?律師并不是為所謂的“壞人”說話,而是為了讓司法機關“兼聽則明”。對死刑等犯罪實施強制辯護,不也正是“沒有反對意見,一緻意見就不能通過”原理?!是以,尊重和保障律師權益,正是司法公正、司法文明的應有之義。
投稿轉載說明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