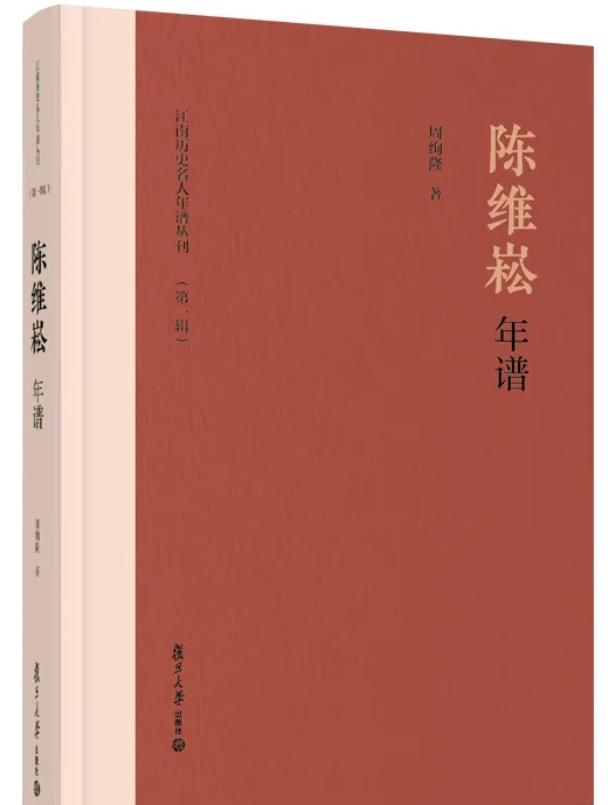
《陈维崧年谱》
周绚隆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维崧(1625—1682)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以诗词享誉清初文坛。本谱以清人陈维崧《湖海楼诗集》《湖海楼诗稿》《迦陵词全集》等为主要资料依据,旁征陈氏诸多亲友、交游的别集、年谱、方志编纂而成,运用文献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将谱主生平主要事迹、交游、著述等系年。通过对各类文献的相互考索、排比参证,详尽地勾画了陈维崧一生的行迹,反映了陈维崧的思想及文学创作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对其文学创作、学术活动、唱和交游等作了细致的考订。
相关内容
陈维崧1625—1682年
绚隆十馀年来于人文社编辑工作之馀暇,留心清代大词人陈维崧的著作及有关其人其事的文献,广泛阅览,细心爬梳剔抉,日积月累,作成一部新的《陈维崧年谱》。绚隆曾经跟我学习,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主要研究陈维崧的词,在年谱写作中亦时而有所交流商讨,文稿初成我有先读之快,也就难逃推毂之责了。
为名人作年谱,属于史学工作。
为名人编写年谱,逐年记出谱主一生的经历、行事、交游、著述,是为完整、深入认识、评论其人的功德、业绩、历史地位,提供出一份坚实的事实依据。按梁启超的说法,属于史学工作。
为文学家作年谱,侧重其文学创作情况。
为主要以文学创作而著称于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家作年谱,虽然仍重在记出谱主一生的事迹,但却要侧重其文学创作的情况,记出若干重要作品的写作年月,以便于联系当时的时事和谱主的处境,理解作品的意旨、意义,中国的年谱肇始于宋人为韩愈文、杜甫诗进行编年,就是这个道理。
为文学家作年谱,尽力搜求有关的文献史料。
另一方面,文学家的一生往往是比较平淡无奇,无缘参与国事,没有做出过值得称道的事业,而关系到其人的生存状况、生命历程的事情,又往往蕴含于文学作品里,要发掘出来。
文学作品里蕴含的人事,有的比确知其生卒年月,仕历、游历的具体状况,还更为重要,对了解作为文学家的谱主更有意义。所以,为文学家编写年谱,既要尽力搜求有关的文献史料,也要研读谱主的诗文,揭示出其中蕴含的人事和谱主的心理心态,这才能够丰富、深化对谱主其人的认识。
绚隆作此《陈维崧年谱》,于文献资料的搜求上是很用心费力的,谱后所附“参考书目”多达千种,谱中都有所征引,便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的是以前研究者没有参考引用过的书,如传本极少的《亳里陈氏家乘》、以前研究者没有使用过的《迦陵词》手稿本、民国抄本《商丘县续志资料》,绚隆都假之稽考出有意义的内容。
如亳里陈氏世系表的绘制,对陈维崧祖、父两代人的记述,由陈维崧的《贺新郎·弓冶弟万里省亲,三年旋里,于其归也,悲喜交集,词以赠之,并怀卫玉叔暨汉槎吴子,用赠柳敬亭原韵》词,抉出其族叔陈玉铸受南闱科场案或通海案株连而流放宁古塔的事情,就是依靠这部在陈维崧的家乡宜兴找到的书做出的。
《商丘县续志资料》等几部河南的地方志,使绚隆开拓了对陈维崧在河南漂泊生涯的考察,更有意义的是加深了对宜兴陈氏与商丘侯方域家族至为密切的关系的了解。这是已往研究者不甚关顾的事情。
迦陵词的刊本都是以词调为类分别编排的,许多篇什作期不明。绚隆找到了基本上以写作时间为序的《迦陵词》手稿本,这便使许多作期不明的词作的作期得以确定下来,分别系入各个年月中,有助于对词作的理解和诠释。如《水龙吟·咏杜鹃花》,载于《迦陵词全集》卷二十三,作期不明。此词在这部手稿本中载于第八册,下面紧接的一首是《夏初临·本意》,题下注:“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
癸丑是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十九日为明末帝崇祯忌日,玩味词之本意,是假伤春暮而抒悼明亡之哀思。《水龙吟·咏杜鹃花》下阕有云:“距料年年,每当开日,便成春暮。”词末又有评语云:“是花?是鸟?是蜀帝灵光?惝恍不可捉摸。”实则是让人“捉摸”所咏花、鸟、蜀帝个中的意思,不可停留在字面上的花、鸟及其作为典故的蜀帝上。可见此词也是寄托遥深,与作于作为明亡之重要标志的崇祯帝忌日的《夏初临》所抒之情是一样的,也当为同一年的暮春所作。
绚隆汇集的有关陈维崧的材料非常繁富,于其自述和他人所记其行迹外,又注重从其自作诗、词、文和友人所赠答诗词文勾稽出其行事和身心状态,遂使这部年谱的内容延展得很宽,记述到的人物多达上千人。
把谱主陈维崧的家世、一生经历行迹和文学创作的情况,依时序记载得空前的细致、具体,展示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历史文化名人的一生实况。
亳里陈氏世系表
谋求出仕
《年谱》记出陈维崧在明末成年前后,便曾随其父陈贞慧到南京,认识了那群以意气名节相矜持的复社文人,不独受其感染,还先后从吴应箕学制艺文,从陈子龙学诗,侯方域在明清易代之际,为避难曾躲在宜兴陈家,也曾与之研讨文章。
清兵渡江,吴应箕、陈子龙先后殉国难,更对他造成沉痛的心灵创伤,成为终生抹不掉的痛苦回忆。这便不难理解,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他已经在努力谋求出仕的时候,还记得崇祯帝的忌日,“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作《夏初临》等词,抒写内心兴亡之悲。
学习
陈维崧在明末是进了学的,入清曾绝意进取,放弃了诸生籍,而后来又恢复了学籍,并且日益迫切地谋求出路。这个中缘故,如果只归因于清王朝已经巩固,社会安定了下来,作为封建文人的功名心改变了原来的人生价值取向,固然不错,但却失于笼统,缺乏陈维崧个人生命历程的实际内容。
灾难
《年谱》中记载了他入清后遭遇的多种灾难,如家族矛盾,强人的绑架勒索,族人的侵产夺舍,仇家(与之有世仇的周延儒家)的生衅滋事,受亲戚周鍭谋反案株连,父亲陈贞慧及二弟陈维嵋曾被捕入狱,家产损毁殆尽,又时时受到官府的威胁,不得不经常外出依人。
他最初恢复诸生籍,如陈维嵋所说,是由于“邑中有仇者乘隙构难端”而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因为这样可以表示与新王朝无异心,还可以享受到做秀才的一些优待。然而,情况没有发生改变,到“科场”、“通海”、“奏销”三案发生,多位亲友受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自已也受到威胁、迫害,有赖在扬州做推官的王士禛致书常州推官毕忠吉予以照抚,方才免于追查。
此后,为了寻求个安身立命之所,才认真地去应乡试,乞求相识的朝官提携、援引,个中包含了许多的辛酸、无奈,是不可以用功名利禄心说明得了的。
交友
陈维崧是文学家,以词和骈文成为文学史研究论著中不可不论及的人物。由于他出身于当时文风极盛的江南地区和甚有名望的家族,一生结识的文化人众多,而且多是文学史上往往要论及的大小文学名流。
早年师从的陈子龙、侯方域,先于他的文学重镇吴伟业、龚鼎孳,都曾称扬其文才。同辈的诗人朱彝尊、王士禛、施闰章、宋琬、汪琬、杜濬、尤侗,稍后的纳兰性德等,与他都有深浅不同的交往。
《年谱》也势所必然但又应当说是甚为用心地,记出陈维崧与他们的关系和交际情况,并且记载得颇为周到、具体,其中就有已往一般研究者习而不察、语焉不详、不甚知其所以然的事情。
与陈维崧关系最深的是父执冒襄。冒襄笃于与陈贞慧的同志至交之情,邀生存艰难的陈维崧来住家中,八年间照拂周至。陈维崧也是由这位饶有清名的父执的携带,进入了文学圈子,结识了王士禛、龚鼎孳等文学名家,成为了名士。
陈维崧不安于长久地依赖这个境况也日益衰落的家庭,欲离去自谋出路,冒襄曾写信给在扬州的王士禛 ,请其加以劝阻;陈维崧离开冒家后,冒襄还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藏。
康熙七年(1668),陈维崧去北京营谋,龚鼎孳设法为之谋得河南学政幕宾一职,特地驰书向冒襄做说明、解释。后来陈维崧病卒于北京,冒襄于如皋定惠寺设位哭之,悼诗披露之情至深至痛,就包含着诗句没有尽能表现出来的意思。
《年谱》记出陈维崧从少年时候便以诗文受到前辈的称赞。如果说,陈子龙、李雯等人的称扬还含有对后生的勉励意味,而到陈维崧盛年时候,遗老姜垓读其诗集赞不绝口,说“黄门(陈子龙)后一人也”,并为之作序;吴伟业在江南十郡士子大集会期间,称他与吴兆骞、彭师度为“江左三凤凰”;龚鼎孳在南京广宴宾客,限韵赋诗,见陈维崧作诗先成,叹赏掷笔,心折定交,后来还誉之为“天人才”。
这表明陈维崧确有过人的文学天赋,诗是写得极好的。王士禛在扬州做官期间颇欣赏其人其诗,饮宴唱酬,甚相得,后来编《感旧集》收其诗33首,在全书所载人物中属于篇什最多的一类,便可以说明。
依据这种情况,研究、评述清初的诗,就不应该忽视陈维崧,以他词坛盛名掩盖了他的诗歌成就。
清初文学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词的复兴。《四库全书》收《十五家词》,《总目提要》说存此“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当时与陈维崧并称的朱彝尊,曾约略地说明词复兴的原因。
《年谱》记出陈维崧作词和与其他词人交往唱酬情况,可以大体看出陈维崧作词和清词复兴的历史轨迹。陈维崧少年时便染指于词,多绮丽语,入清后十馀年间,曾与常州喜填词的邹祇谟、董以宁相倡和。由于他吟咏倡酬喜用诗,于词并不专注,虽时有所作,却如朱彝尊后来所说:当时“予未解作词,其年亦未以词鸣”。
顺治未康熙初,他参加了王士禛在扬州发起的倡酬活动,词友邹祇谟与王士禛以词相交,选辑《倚声初集》,孙默选刻《国朝名家诗馀》(后来题名《十五家词》),他亦有“红桥倡和词”之作和《乌丝词》之结集。可见此时填词者已众多,反映出词在清代复兴之初相。此后,陈维崧也不再主要倾情于诗,而是诗、词兼行,词之境界也扩大起来。
到康熙十二年(1673)之后,更是倾力于词,诗则少有所作,一切感怀遣兴、赠答倡酬都付之于词,篇什爆出,词名雀起,先后之词作者纷纷请其品题作序。
康熙十七年(1678)进京应博学词科试前后,为其《迦陵填词图》题词者多达数十家,其中多是文学名流和著名词人,如王士禛、朱彝尊、彭孙遹、尤侗、曹贞吉、纳兰性德等。
此事表明当时文学界共尊陈维崧为词坛圭臬,个中也可以想见那个时段词坛的盛况。如果联系此后不久,陈维崧、纳兰性德便相继谢世,数十家为陈维崧一像题词之际,该是清词复兴的高潮。
在这中间,《年谱》记载了孙默编刻《国朝名家诗馀》,首批为邹祇谟、王士禛、彭孙遹三家,第二批为曹尔堪、王士禄、尤侗三家,第三批为陈世祥、陈维崧、董以宁、董俞四家,第四批为吴伟业、龚鼎孳、梁清标、宋琬、黄永、陆求可六家,凡十六家。
又记龚鼎孳《香严词》是陈维崧在康熙十二年(1673)校过寄给孙默的。可知《国朝名家诗馀》是孙默历时十多年分批刻出,第四批书卷首邓汉仪序署康熙十六年(1677)作,刻成当在其后一二年间。此书后来收入《四库全书》,题名《十五家词》,缺龚鼎孳《香严词》,编次亦不依原刻顺序。
《年谱》据中国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查得,因龚鼎孳所著全集业经销毁,不应复存此词,故抽毁之,改为《十五家词》。这便辨明了此书之名称、所收家数之变易的问题。
《年谱》记入的人事极多,或许应当做些剪裁。然而,其中一些不关谱主大体者,却有使我感到兴趣的人事。
譬如,我考察《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生平时,了解其坐馆三十年之久的馆东毕际有,也曾在文中写到蒲松龄曾代毕际有作《答陈翰林(其年)》一文,文采斐然,足与毕、陈两家身份相副,却没有深究两家的关系。
《年谱》记出毕际有官南通州知州时,陈维崧为避通海案、奏销案的株连,曾一度寓居毕际有的官署中;毕际有罢官过扬州,宴别故老友好,陈维崧亦与会,并为之作《归田倡和序》。
是以陈维崧举博学鸿词官翰林院检讨之初,即致书毕际有以通问候,遂有蒲松龄代作答书之事。更有趣的是中间还推出了一位小人物刘孔集。刘孔集是蒲松龄在宝应县孙蕙衙门中的幕友,我在考察蒲松龄南游做幕的文章中,曾讲及他与刘孔集惺惺相惜,蒲松龄还乡后,还有怀念、悼亡之诗,我却不知其名及里籍。
《年谱》记载到他也是毕际有这次宴集中的一位,而且他还单独招陈维崧去酒楼饮酒晤谈。陈维崧称他为“山东刘孔集大成”,他当名大成,字孔集,山东人,他也当与陈维崧前已相识。由此推断刘孔集是随毕际有做幕的,他与陈维崧相交是在陈维崧寓居南通州署中时,毕际有罢官归里后数年,又应毕际有的同邑人孙蕙之聘,到了江苏宝应,与蒲松龄成了幕友。
我读《陈维崧年谱》有这种意外收获,我想别的研究清初文学的人也会从中发现有兴趣的材料。譬如《年谱》康熙十三年(1674)目下,记载到陈维崧和杜濬同赋《贺新郎》词自嘲不善点戏,接着杜濬讲述了一位官员观演闯王攻破北京,兵部尚书某跪地迎降的戏剧,剧中的兵部尚书其实就是那位观戏的官员,弄得他好不尴尬的故事,陈维崧又赋《贺新郎》一首咏其事。
此官员显然就是曾经资助李渔刊行《无声戏二集》的张缙彦,小说中有段张缙彦在闯王破北京时间自缢获救,自称“不死英雄”的情节或话头,张缙彦便被人弹劾,说他伪造历史,遂流放宁古塔。杜濬所讲的故事当是由张缙彦之事附会生发出来的。研究李渔的小说者,对此事会感到兴趣的。
再如,《年谱》记载到陈维崧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对康熙十七年(1678)葡萄牙进贡黄狮子群臣皆有称贺一事,做了认真考证,更具有多个方面的参考价值。
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