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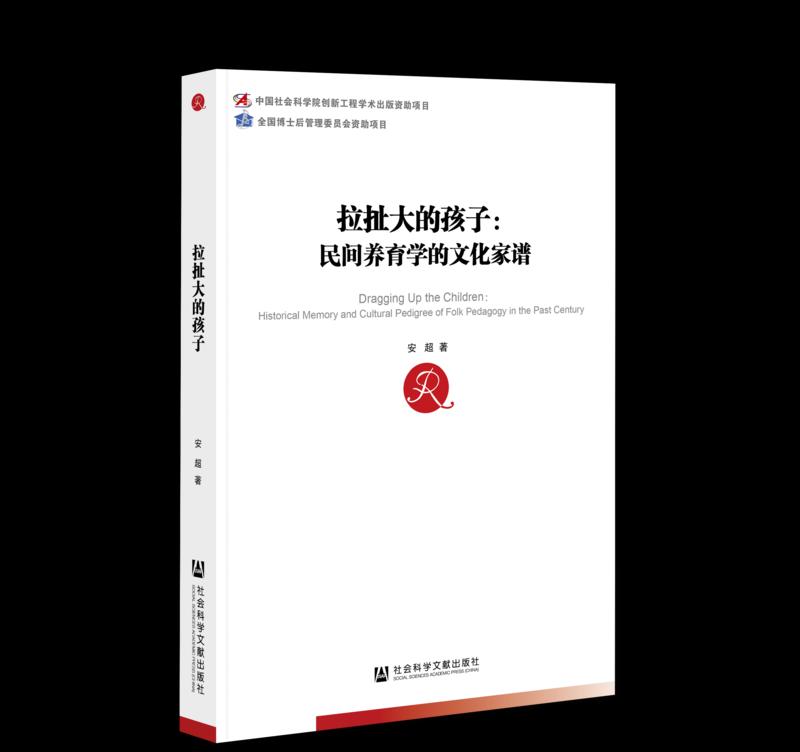
《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个乡村女孩在成为母亲之后,通过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写就的中国乡村百年传续的教育家谱,对家庭教育中的亲缘共育、恩德训育、吃苦伦理、青春期悸动、贵人相助、阶层摆渡、现代养育焦虑、完美母职、象征性父权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里,我们既能看到一个农村家族的五代人在百余年间如何面对苦厄、动荡、无常把孩子“拉扯大”的复杂经验,也能看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野孩子”们的长大成人的多条路径。
不同于卢梭学派对乡村生活及自然主义教育之乌托邦式的精英怀旧,也不同于布迪厄学派对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纯粹目光和实用目光的二分化理解,作者揭开了她所亲历的民间养育学的多副面孔和深层结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教育与生计相结合的家庭劳动教育;“说谅”与“圆成”——游戏、世俗交谈与社会欢腾所构造的公共闲暇教育;“举头三尺有神明”——对文字、读书、教师、爱情、善业等所承载的“天道”持道德敬畏的神圣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基于生计考量的实用目光始终存在,但每一代人都保持了“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后者才是支持平民子弟实现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民间养育学既是苦难教育学,也是希望教育学,而在最终意义上,是“大器晚成”的教育学。
“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还反了你了,养了个白眼狼!”这句话一直伴随我从小与母亲斗智斗勇的成长过程。每次母亲气急败坏地撂下这句话,我也只能偃旗息鼓,虽然心里很不服气。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理解“拉扯孩子”的意思,心里默默嘀咕,不就是洗洗尿布吗?由于父母工作非常忙,我和弟弟的童年大多是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度过的,与母亲并不“亲”。
来到城里上小学后,我对母亲的管教又恨又爱。在农村野惯了的我,恨她坚持让我剪短发像个假小子,恨她不给我穿漂亮裙子,恨她学费不能及时交上让我被老师羞辱,恨她不让我看闲书,恨她不让我带好朋友来家里玩,恨她总是冷冰冰地责备我……可是,懂事后的我也很心疼她。母亲是个瘦小的南方女性,从小家庭条件优越,作为备受疼爱的小女儿,没怎么吃过苦,高中毕业后在当地的事业单位上班,属于“坐办公室”的人。1998年事业单位改革的时候,母亲为了赚更多的钱来养活一大家子人,停薪留职从单位里出来“下海”做起了买卖。父亲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工作,爷爷奶奶有很多地要种但收入微薄,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母亲就独自承担了进货、摆摊、售卖、收摊、算账的生计活,洗衣、做饭、打扫的家务活,还有亲戚走动、人情来往的家族事务。在忙碌的间隙,她才能顾得上我,偶尔回农村看望老人和弟弟。
每次放学,我都会到母亲窄小杂乱的衣服摊子旁边,支个小凳子,与母亲一起吃附近饭摊上买到的饭菜。母亲总是飞快地扒拉几口饭,或者吃几口就要停下来应付来来往往的顾客。母亲眼光好、口才好,因此生意格外的好。生意越好,母亲就越吃不上几口热饭,因此落下了胃病。我要帮一下忙,母亲就不耐烦地摆摆手,赶着我去温书、写作业,语气生硬地对我说:“你别伸手帮倒忙,做好你自己的作业就行!”我缩在摊子的角落里,看她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衣服卖得好或遇到老主顾的时候,母亲的眉头就舒展一些;遇到难缠或者找麻烦的主顾,母亲就需要小心翼翼地赔不是;遇到来收保护费的凶神恶煞,母亲就不得不低三下四、忍痛割爱。有时候,母亲周转不灵,保护费无法及时给,摊子就被坏人砸得乱七八糟。我几次撞见母亲默默扶起东倒西歪的架子,她偶尔会坐在椅子上长久地沉默或叹息,但她从没为这些事情当着我的面流过一滴眼泪。
无论遇到什么事,母亲都不让我吱声,只让我待在角落里做功课,或者让我走开。渐渐地,母亲攒钱租到了门面,后来又买下了一个门面。我藏缩的角落也越来越好,从衣服堆旁边的小凳子,到一个楼梯间改造的试衣间边上逼仄的一角,再到一个明亮宽敞的门面入口处的收银台底下。始终不变的是,母亲瘦小的身影挡住了一切,人来人往的热闹处有一个安静的小角落,我在“市井中的孤岛”上洞察却无法陪着母亲尝遍人间冷暖。后来听夏林清老师讲到一个劳动家庭里的父亲,他是给领导开车的,作为司机,他养成了一种“在场而又不在场”的能力,这种时刻在“自我流放”、在孤独与想象中游走的生命体验,我心有戚戚焉。
父亲远在外地工作,我们一家团聚的机会总是很少。偶尔团聚,父母的交流也缺少温情。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充斥着谈话和生活。想起来,我与父亲的互动记忆非常少,但家里到处散落着父亲读过的书。父亲年轻时长得高大、帅气,是个极爱读书的人,写的字也极好。假期无聊的时候,家里寂寥无声,反复翻阅父亲的藏书成了我的消遣,就连父亲在医科大学进修时枯燥无味的厚厚教材《内科学》《外科学》都被我翻得卷了边儿。我无数遍地模仿他书上龙飞凤舞的钢笔签名,当然很多时候是为了代替家长签字。渐渐地,我的字越来越像他写的字,虽然他从来没有手把手教过我写字。偶尔,我也翻翻家里珍藏的老照片,父亲年轻时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的模样英俊极了。可惜,父亲的脾气总是很暴戾、冲动,对待孩子不苟言笑,对待母亲不够温柔体贴。我更多的是通过父亲的物件、书籍来敬仰父亲的才华,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埋怨他对母亲和我们照顾太少。
直到我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女儿变成了母亲,看着孩子逐渐长大,自己在学业和家庭中痛苦挣扎,才感受到母亲当年说“上有老、下有小”“拉扯大孩子”的切肤之痛。我试着去体会父母是如何在时代大潮中抓住任何一块浮木,又拖着拽着嗷嗷待哺的幼儿或横眉怒目的叛逆少女,保护孩子们每天不会冻着、饿着。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这种反身性的思考,并不能消解我在成长过程中对他们累积的怨念。人们常说“至近至远东西,至亲至疏夫妻”,亲子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母亲离我很近,但精神上离我很远;父亲离我很远,但精神上离我很近。我对他们又恨又爱,而这两种感情又是无法通约的。
这种中国式的复杂亲子关系和亲职实践,是我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思考起点。一开始,我想写的是“拉扯大的孩子:文化互嵌时代的养育实践”。我的研究对象是像我这样的三代抚幼家庭。这时候,我天天斗智斗勇的对象已经换成了导师康永久教授。康老师毫不留情地怼我:“你的研究问题呢?你的理论对手呢?”我也毫不客气地跟他翻白眼,之后马不停蹄地偷偷用功,争取下次能跟他吵个平手。在这个时期,我阅读了大量与养育相关的书籍,对我聚焦问题启发最大的是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拉鲁的《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哈里斯的《教养的迷思》、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李银河、郑宏霞的《一爷之孙》、景军主编的《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河合隼雄的《孩子与恶》、萨洛韦的《天生反叛》。书看得津津有味,但离找到一个明确的理论对手还差很远。开题的时候,我甚至引用了康老师的理论,好歹证明一下师承关系嘛!不出意外地我又被康老师骂了,“我看见学生引用我的东西就脸红”“你就这点出息吗”“老师的东西不是用来引用的,是用来给你们当垫脚石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书看的挺多,但我的论文迟迟没有进展。我的副导师(学部实行双导师制)也是我的女性主义启蒙老师郑新蓉教授着急了。她常常替我们这些迟迟无法毕业、带着拖油瓶的女博士们发愁,希望我们不要总是“输入”,不要总是“消费”,更要“生产”。她希望我跳出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看见更多的普通女性、普通母亲。为此,郑老师带着我们一起精读了《斗室星空:家的社会田野》,这本书成为我由关注孤立的个体家庭转向关注家族和历史的关键。我第一次从这本书中看到了与我同样有着痛苦经历,但最后实现经验回溯、叙事疗愈、结构反思和文化超越的“同伴”们。我开始觉得没那么孤独,开始感到自己的选题在走出了个体家庭的局限时,还有一点时代共通性。我试着走出女儿的角色,从一个知识女性的角色去看待父亲、母亲和自己。我的论文开始于一个自我研究,但最终又不是一个自我研究,或者说,真正的“自我研究”绝不拘囿于自我。
这个时候,我刚好在“康门”读书会导读了布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泽利泽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最初,我是作为布迪厄和泽利泽的“迷妹”、带着粉丝崇拜大神的敬仰之情来导读的。怼天怼地的康老师又忍不住了,他认为布迪厄最终没有突破结构决定论,而泽利泽最终也未能走出儿童的经济价值决定论。一众同门迅速分为两派唇枪舌剑,最后谁也没能说服谁。但关键的是,康老师打碎了我对布迪厄和泽利泽的“滤镜”,敦促我完成了对布迪厄理论的再反思,最终我在《“文化区隔”与底层教育的污名化》一文中,开始了对“布迪厄神”的批判,也找到了关键的理论对手。
沉默而敏感的我,天生适合在社会田野里撒欢儿、打滚儿,做了母亲的我又多了几分体物入微的本领,听故事讲故事已变成“长”在我身上的能力,但还没有内化为一种使命。彼时,家族的大爷爷还健在,接近百岁高龄。我抚着他干枯如虬枝的手,听他模糊不清的吐字,看他眼角冒出的眼泪,不知不觉间已动容、动心。大爷爷说:“灵芝(我的小名),等我死了你烧给我。”他是想说,我等不到你毕业了,如果有一天,你写成书了,就在坟上烧给我。后来我毕业的时候,大爷爷已经去世了,始终未看到他的故事成文。生命与时间,哪一样都不等人。
就在与老一辈人谈天说地的过程中,文化生命的流转让我叹息、扼腕、沉醉、爱慕、神往。每次我哄孩子入睡后,起身披衣,儿子睡眠的鼻息在侧,我在电脑上整理录音稿的时候,有如夜灵附身。对,我爱上了这件事,我爱上了这样的我。很快,我的田野资料已逾40万字。跨越百年的历史,几十个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我要怎样去呈现?我怎样才能完成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托付?文字之爱是一回事,文字的理性是另一回事。
我只好从这些故事和热爱里暂时抽身,再一次“自我流放”。独学而无友,必孤陋而寡闻。接下来的一整年,我辗转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的课堂,听渠敬东老师的《论法的精神》精读课、李康老师的西方社会学史、陈建翔老师的家庭教育课,雷打不动地参加康永久、陈向明、郑新蓉老师的读书会。这段时间一点儿都不轻松,我头脑里各种观念在打架。尤其是在“技术”“自然”“资本”“市场”“劳动”“焦虑”等关键概念上,康老师是自恋乐天派,郑老师是苦大仇深派,陈建翔老师是自然佛系派,陈向明老师是温和行动派。他们也天天在“吵”,君子动口不动手,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天天吵架。这些恩师观念、立场各不相同,我精神上受折磨极了,经常为此怀疑人生。但本质上,是我自己的观念根本没有生长出来,所以只能当理论的“墙头草”,觉得谁说的都有道理。
突破口在哪里呢?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传说中幽深的柏拉图洞穴,接近洞口的地方, 一定是岔路丛生的。选择恩师走过的,或者指给我的任何一条理论之路,都可能会通向出口。可是,我想自己刨一条路出来。原因是,我的读书之路已经太过于倚仗师长了,而我需要一次精神上完整的分离,来完成一个完全由我独立制作的艺术品,哪怕是笨手笨脚地只能雕刻一个“丑陋的小板凳”呢,哪怕就这一次呢!我要完成一个久违的精神意义上的成人礼。不过,虽然屏蔽了老师们的“唠叨”,这个突破依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实现的。康老师带领我们阅读了《道德情操论》和《善恶的彼岸》,向明老师带领我们阅读了《教育的美丽风险》,这时,我的学业生涯恰已步入尾声。这三本书出现的刚刚好,帮助我完成了对底层社会一套基于“匮乏”的底线性教养和道德性敬畏的总结性思考。同时,我也看到了几代乡村读书人在为了“不在地里刨食”的奋斗过程中,在被无数精英称为“内卷”的焦虑社会中,所存续的一种基于天性之爱、基于心灵托付、基于投身阿伦特意义上“言说与行动”之人性实践的纯粹目光。这一次,母亲的、父亲的……很多人佝偻的身躯和高昂的头颅终于在模糊的历史中,和我的文字合而为一。那些与我一起共同完成这些文字的人,还活着的或已经逝去的,他们的面孔也在此时一一清晰起来。当然,对于民间养育学的思考和书写还有很多遗憾,那些没有完成的,亲爱的读者们,还会在你们的理解上继续完成。
安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2020年12于清华大学明斋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