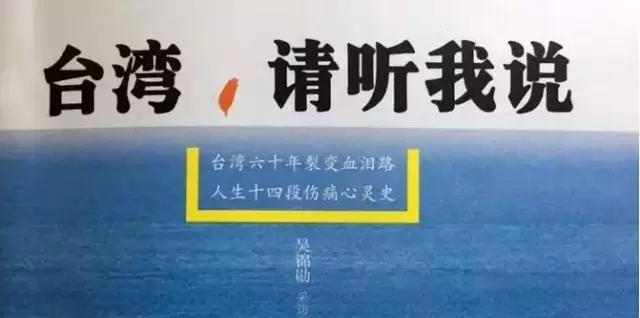
《台湾,请听我说》(吴锦勋撰述,华夏出版社,2015年1月)
钮承泽,1966年6月23日出生于台湾,成长于将军府邸和书香门第,外公是将军,父亲也从军,外婆与母亲则在大学教中文。而其外婆的父亲是民国军阀,自己的身上更是流淌着满族八旗“钮祜禄”氏的血液。自谑“满清余孽、军阀后代”。
他是生于台湾、长于台湾的“大陆二代”,“外省人”的身份曾令他非常伤感。
他认同台湾,他爱台湾,他甚至离不开台湾的食物文化,离不开他在台湾的朋友和猫。但他同样割舍不了的是,来自基因、来自血液的一份连结。
我流着"满清欲孽、军阀后代"的血
我的钮姓,源自于满族最古老的姓氏“钮祜禄氏”,在清朝是八大姓氏之一。我们姓钮的在清朝做了四次皇后,生了两个皇帝。
在我爷爷那一代,据说现在的北京火车站就是我们家,后来家道中落了,没钱就卖了房子,吃老本。后来我爸进了军校,在时代的安排下,就这样来到台湾,来了也没有想到会回不去。
全家只有他一个钮姓的来,我在成长的经验里,没有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堂兄弟,只有表亲,像是阿姨、舅舅、外公、外婆、表哥、表弟、表妹。
我外婆是安徽人,她的爸爸是冯玉祥的拜把兄弟,姓孔,人称孔大帅,做过陕西、甘肃二省督军。我爸在北京时就认识我外婆,叫她二阿姨;后来我爸来台,举目无亲,只好到他唯一的长辈家,也就是我外婆那里走动,之后和我妈谈起恋爱结婚。所以我常说,我家的血缘是“满清余孽、军阀后代”。
外公是将军,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他是朝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法律系毕业的,在抗战时投笔从戎。从军法官开始干起,主管撤退业务,他的直属长官就是宋楚瑜的爸爸宋达。
外公住在汀州路附近的百坪(几百平米)的官舍,因为房子大,爸妈结婚后,就叫我爸住在他家,我十五岁之前都在那个大宅里住,后来才搬出去。
外公后来被派去“革命实践研究室”担任总务长之类的官,那时党政军不分,所有人都要受训,院长就是蒋介石。我外公有边缘性格,耿直温厚,不钻营、不结党,他对下属远比对长官好。之前他是八二三炮战的运输署署长,八二三炮战打的就是运输战,可是他却是穷当当的,他给我们很好的教育示范。
钮承泽一家
我的渐冻人父亲
1949年那波大移民潮,那么多人离乡背井,连根一拔就来了,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爹娘、自己的妻儿,这怎么会没有伤口?
我爸自己一个人来台,比较悲惨的是,他是渐冻人。我十二岁时,他开始生病,到我十八九岁,他的肌肉慢慢萎缩到喉部以后,失去呼吸能力。被送到医院那天,我为他做人工呼吸,医生告诉我,他还剩两个礼拜的生命,没想到,他又活了十八年才走。
通常渐冻人只有三到五年生命,但爸爸从发病到离开,整整活了二十五年,而且有近二十年躺在床上,靠呼吸器呼吸。他是全世界我所知最惨的生命状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意识清醒,全身动弹不得,却一直受回忆折磨。
他出现病症但还没进医院的那几年,我已演过《小毕的故事》了,每天我都穿得很骚,在外面有很多马子朋友,每天都只想玩,想出去混。
那时我大约十六七岁,刚好是青少年的叛逆期。对爸爸的印象永远是,他坐在饭桌前,铺着一叠纸,用拳头握紧笔,手会抖,几乎没有办法拿笔了,但他就是要写信给家里。他每天就只做这件事:写信。
那时还没有“解严”,我妈在师大语言中心教中文,日本三井大商社会派人来台湾学中文,然后派去大陆做生意。我妈有个学生去了北京,她通过这个日本学生,想办法找到我爸家人,就这样靠着日本学生,经由第三地偷偷传信、寄信。
我爸有三个兄弟、三个姊妹,三叔是京戏权威,曾任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有一年他被派去德国当访问学者,我爸找人传话,叫三叔打电话到台湾给他。
通过妈妈的日本学生居间传话,我们终于讲好几月、几日、几点要通电话。那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全家无比慎重地等在电话机旁边,结果电话响了,那时国际长途电话品质不好,声音远远的,一层层回音好像在山洞里。
我一接起来,“喂——”不清楚,我再“喂”——三叔那头回话“嘿,我是钮骠啊”,“三叔啊,你等会儿——”我把电话通拿给我爸,他颤巍巍地把电话拿起来,才一开口“喂——”脸就皱在一起,哭啊,大哭,那天我们一家四口全部大哭。终于知道家里状况:爷爷早就死了,后来叔叔、姑姑又怎样……我印象最清楚的,就是爸妈的哭声。
大时代的操弄
我到了一定年纪,很羡慕我那些“早移民的朋友”,也就是所谓的本省人,他们可以回到南部的老家,有完整的家庭关系,他们往往有土地,但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爸十几岁就和故乡切断了联系,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大时代操弄,他们那一辈,根本就是为“打回去”而活的。就因为要打回去,政府给房子住,眷村、家具都是临时的,用轻便的藤椅、藤桌,好像随时说走就走。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现在永和中正桥下,当时有人要卖地,一坪(三点三平米)五毛钱,我外公说:“买什么啊,我随时要回去,怎么买?”长大后,我想到这事,哇哇哀嚎:“哎呀!你那时真买个一万坪,我现在不就有钱可以拍电影了!”
我爸很想家,但是不敢回,因为他是吃终身俸的,万一回去了,终身俸就没了,只好努力压抑自己。他老讲北京的什么,兴致好的时候,自己做一做家乡小吃,偶尔讲老家的事,讲我爷爷,但讲得不多。后来渐冻了的身体把他囚住了,有生之年都不曾回乡,好惨。2003年,他去世了,后来葬回了北京,了却他的心愿。
钮承泽
北京,一种想象的故乡
以前我和我爸没那么水乳交融,从小背负着爸爸口中的北京,那样的北京对我而言是痛苦的,我连做梦都会梦到北京,但我不知道那个图像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以前被爸妈打骂之后,就会一个人到房间把门锁上,大哭着叫奶奶——幻想有个奶奶,他会抚慰我,我常跟想象中的爷爷、奶奶说话。北京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北京对我有一种超越血缘的连结感,身为旗人,我一定有些来自基因的设定,比方我运动细胞差,但一上马就会骑马,拿起箭就会射,我觉得这跟基因有关。
之前我去北京,觉得一切都很亲切,听到那些人讲的都是我爸、我外婆的口音,我没有任何的隔阂。还有很多方言,北京现在的人已经不讲,只有我爸会讲。比方他会讲:“你怎么那么‘怯’?”是指“你怎么那么土”;或是讲“拿墩布来擦干净!”,其实是那拖把来抹地板。
这些北京方言,从小我就听熟了。
我记得有天半夜,我跟周迅和她朋友三个人去骑车,在天安门一带的胡同瞎转兜绕,我一面骑,一面感觉这空气的温度,那整排挺拔的梧桐树,我知道这些巷弄胡同都是长久存在的,而我爸爸他们一家显然也走过这样的路线,觉得好熟悉、好亲切,有了某种奇特的连结,于是我发自内心很戏剧性地说:“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在那晚的气氛下,我开了这样的伤怀但又温暖的玩笑。
虽然如此,台湾是我的家乡。我的朋友、我的猫,这里充满一切成长的东西,以及我的食物文化。但北京是我始终不能割舍的,是来自基因、来自血缘的一份连结。
认同哪里?爱不爱台湾?一直是这几年很烦人的政治问题。我很多好朋友都是本省人,有很长时间,彼此不太会触碰对方的伤口。族群是这几年才有重新被挑动起来的。
“外省人”的伤感
我觉得台湾不要再讲“外省人”三个字,“外省人”这三个字,对我来讲是非常伤感的。
我二十岁左右大量阅读《新新闻》、《人间》等杂志,非常有使命感,很关心底层,想法很左,一度有激烈的思想,觉得腐败的国民党需要被推翻替换。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会有想要做什么的冲力,这里面有青春期的焦虑、革命的英雄主义,好像为了背后很大的目标,可以怎样怎样。其实后来才知道,献身革命的人并不一定是想要让这个世界更好,可能只是找到一面理想的旗帜,可以追随、依附,然后可以满足,或是治疗自己。在这背后可能是盲动,是自己焦虑的宣泄。
所以我曾经很支持陈水扁。1994年,台北市长第一次选举时,外婆说,我家最民主了,来来来,告诉我,你要投谁。因为她先讲了我们家“最民主了”,所以我大方讲:“陈水扁啊。”结果,外婆拉高八度音大叫:“什么!”之后大骂:“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对不起死去的外公!”
为了阿扁,我弄到跟家里决裂,跟朋友无法来往,我妈妈要跟我脱离母子关系。结果,陈水扁当选后,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对街庆祝,但当晚我却先走了。原因是:第一,有些闽南语发音我听不懂;第二,我感受到他们对我血液的敌意。
作为一个外省人,好像背负了原罪。我怎么了?做错什么了?从小在台湾出生成长,离开台湾的时间加在一起没有超过一年,到现在也没有去移民,为什么我要被排挤?我有一种很落寞的感觉。我已经不认同国民党的腐败政权,但在这里我又是外人,好像夹在中间。
1996年,台湾选地区领导人时,我到大陆拍戏,人家把我当台湾人;中间我去美国,因为长得黑,又被当成印第安人;回到台湾,原来我是“外省人”。结果,他妈的,哪里是我的家?
我的前女友是深绿的,我自诩为中间选民。她们家也有伤口,她阿公讲一口漂亮、标准的日语,国民党时代在铁路局工作,明明非常优秀,却被打压。2004年投票前一天,发生“三一九”枪击案,那时我在拍戏,她打电话给我说:“哇操,这真是太屌了,陈水扁竟然搞这一局。”
她是深绿,也认为子弹是假的。第二天,她却穿着打扮好好要出门,我问她上哪里。她说:“去投票。”我问投谁,她回答:“投阿扁。”我拉住她:“等一下,等一下,你不是说子弹是假的吗?”她回说:“没办法,我为了阿公。”她把我推开了,为了阿公去投阿扁。可是到了2008年,她投不下绿的,但也没办法把票投给蓝的。
我身边有非常多这样的朋友,像一位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的好友,她们家是深绿的,以前我去他家吃饭,他妈妈还用闽南语问我:“你甘系新党?新党系匆驶(不能)来阮兜(我家)喔!”现在这位朋友也不投票啦。
我想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有各自的伤口,而伤口终究有复原的过程,它会被忘记。其实台湾早期移民也经历过一段混乱的过渡期。福州人跟漳州人打,漳州人和泉州人打,闽南人跟客家人打,汉人和少数民族打,大家都如此。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但打完之后,不就是寻找尊重和包容,大家才能相处下去吗?
民进党执政时,我有个很大的恐惧,无涉统独,而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我想台湾和大陆应该要维持一种“相处之道”,而不是切断。切断就是自闭封锁,回到万历十五年时,不过,明朝那时还有大中华的疆域,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岛屿。
台湾某些无耻政客操弄族群,很清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操弄背后,一定有特定目的,也一定有伤口。有伤口才可能被撩拨嘛!这几年,族群成为可以挑动的议题,代表还有这样的人口和这样的问题存在。我觉得现在就是过程,就像疹子,赶快发一发吧!
找到和自己相处之道
我拍《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原本是要探讨目前岛内的政媒乱象,以及“为什么我们在台湾活得这么不快乐”,结果拍到最后,解构了自己。
原本我设计一个“谑而不虐”的桥段,要在电影里扯掉邱毅的假发。我们剧组跟他进行了两个小时正式的访问,我看到他天真浪漫、自恋的一面,甚至午夜梦回的伤痛,我与他有了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我们对另一个人会有反感,往往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也有的讨人厌的部分,好比邱毅那种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喜欢成为聚光灯焦点等等。那些东西我身上也有。后来他真的被人拔掉假发,我有很深的同情,不只对他,还包括拔他假发的人及其背后的原因。
我们总是喜欢把手指着别人,这样就不必面对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伤口,我们也很容易沉浸在负面情绪中,喝酒、吸毒、买名牌、盲目追求成功,但都没有好好想过,自己才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其实政客和媒体只是反映了我们复杂混乱的内在罢了。
我曾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却不知不觉腐烂发臭,甚至得抑郁症。但我终究回转成今天这样的我,是因为我往内找,找到跟自己相处的方法,因此才可以跟这个世界相处。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历程,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变得有反省的能力,充满慈悲。我不是星云大师,我仍然有欲望,有想要追求的,也还是会为负面情绪所苦,但我已找到跟生命相处的态度。对未来我并不悲观,人惟有慈悲地对待自己,才可能慈悲地对待这个世界。
【声明】文章节选自《台湾,请听我说》(吴锦勋撰述,华夏出版社,2015年1月),“中国台湾网”头条号转发文章不作任何利己目的,只为向更多读者分享字里行间“真实的台湾”。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原标题:《钮承泽:“外省人”这三个字曾令我非常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