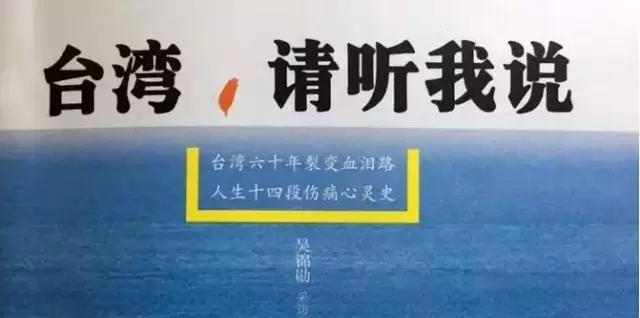
《台灣,請聽我說》(吳錦勳撰述,華夏出版社,2015年1月)
鈕承澤,1966年6月23日出生于台灣,成長于将軍府邸和書香門第,外公是将軍,父親也從軍,外婆與母親則在大學教中文。而其外婆的父親是民國軍閥,自己的身上更是流淌着滿族八旗“鈕祜祿”氏的血液。自谑“滿清餘孽、軍閥後代”。
他是生于台灣、長于台灣的“大陸二代”,“外省人”的身份曾令他非常傷感。
他認同台灣,他愛台灣,他甚至離不開台灣的食物文化,離不開他在台灣的朋友和貓。但他同樣割舍不了的是,來自基因、來自血液的一份連結。
我流着"滿清欲孽、軍閥後代"的血
我的鈕姓,源自于滿族最古老的姓氏“鈕祜祿氏”,在清朝是八大姓氏之一。我們姓鈕的在清朝做了四次皇後,生了兩個皇帝。
在我爺爺那一代,據說現在的北京火車站就是我們家,後來家道中落了,沒錢就賣了房子,吃老本。後來我爸進了軍校,在時代的安排下,就這樣來到台灣,來了也沒有想到會回不去。
全家隻有他一個鈕姓的來,我在成長的經驗裡,沒有爺爺、奶奶、叔叔、伯伯、堂兄弟,隻有表親,像是阿姨、舅舅、外公、外婆、表哥、表弟、表妹。
我外婆是安徽人,她的爸爸是馮玉祥的拜把兄弟,姓孔,人稱孔大帥,做過陝西、甘肅二省督軍。我爸在北京時就認識我外婆,叫她二阿姨;後來我爸來台,舉目無親,隻好到他唯一的長輩家,也就是我外婆那裡走動,之後和我媽談起戀愛結婚。是以我常說,我家的血緣是“滿清餘孽、軍閥後代”。
外公是将軍,我受他的影響很大,他是朝陽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法律系畢業的,在抗戰時投筆從戎。從軍法官開始幹起,主管撤退業務,他的直屬長官就是宋楚瑜的爸爸宋達。
外公住在汀州路附近的百坪(幾百平米)的官舍,因為房子大,爸媽結婚後,就叫我爸住在他家,我十五歲之前都在那個大宅裡住,後來才搬出去。
外公後來被派去“革命實踐研究室”擔任總務長之類的官,那時黨政軍不分,所有人都要受訓,院長就是蔣介石。我外公有邊緣性格,耿直溫厚,不鑽營、不結黨,他對下屬遠比對長官好。之前他是八二三炮戰的運輸署署長,八二三炮戰打的就是運輸戰,可是他卻是窮當當的,他給我們很好的教育示範。
鈕承澤一家
我的漸凍人父親
1949年那波大移民潮,那麼多人離鄉背井,連根一拔就來了,再也沒有見到自己的爹娘、自己的妻兒,這怎麼會沒有傷口?
我爸自己一個人來台,比較悲慘的是,他是漸凍人。我十二歲時,他開始生病,到我十八九歲,他的肌肉慢慢萎縮到喉部以後,失去呼吸能力。被送到醫院那天,我為他做人工呼吸,醫生告訴我,他還剩兩個禮拜的生命,沒想到,他又活了十八年才走。
通常漸凍人隻有三到五年生命,但爸爸從發病到離開,整整活了二十五年,而且有近二十年躺在床上,靠呼吸器呼吸。他是全世界我所知最慘的生命狀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意識清醒,全身動彈不得,卻一直受回憶折磨。
他出現病症但還沒進醫院的那幾年,我已演過《小畢的故事》了,每天我都穿得很騷,在外面有很多馬子朋友,每天都隻想玩,想出去混。
那時我大約十六七歲,剛好是青少年的叛逆期。對爸爸的印象永遠是,他坐在飯桌前,鋪着一疊紙,用拳頭握緊筆,手會抖,幾乎沒有辦法拿筆了,但他就是要寫信給家裡。他每天就隻做這件事:寫信。
那時還沒有“解嚴”,我媽在師大語言中心教中文,日本三井大商社會派人來台灣學中文,然後派去大陸做生意。我媽有個學生去了北京,她通過這個日本學生,想辦法找到我爸家人,就這樣靠着日本學生,經由第三地偷偷傳信、寄信。
我爸有三個兄弟、三個姊妹,三叔是京戲權威,曾任中國戲曲學院副院長,有一年他被派去德國當通路學者,我爸找人傳話,叫三叔打電話到台灣給他。
通過媽媽的日本學生居間傳話,我們終于講好幾月、幾日、幾點要通電話。那天晚上,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全家無比慎重地等在電話機旁邊,結果電話響了,那時國際長途電話品質不好,聲音遠遠的,一層層回音好像在山洞裡。
我一接起來,“喂——”不清楚,我再“喂”——三叔那頭回話“嘿,我是鈕骠啊”,“三叔啊,你等會兒——”我把電話通拿給我爸,他顫巍巍地把電話拿起來,才一開口“喂——”臉就皺在一起,哭啊,大哭,那天我們一家四口全部大哭。終于知道家裡狀況:爺爺早就死了,後來叔叔、姑姑又怎樣……我印象最清楚的,就是爸媽的哭聲。
大時代的操弄
我到了一定年紀,很羨慕我那些“早移民的朋友”,也就是所謂的本省人,他們可以回到南部的老家,有完整的家庭關系,他們往往有土地,但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爸十幾歲就和故鄉切斷了聯系,他們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大時代操弄,他們那一輩,根本就是為“打回去”而活的。就因為要打回去,政府給房子住,眷村、家具都是臨時的,用輕便的藤椅、藤桌,好像随時說走就走。
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現在永和中正橋下,當時有人要賣地,一坪(三點三平米)五毛錢,我外公說:“買什麼啊,我随時要回去,怎麼買?”長大後,我想到這事,哇哇哀嚎:“哎呀!你那時真買個一萬坪,我現在不就有錢可以拍電影了!”
我爸很想家,但是不敢回,因為他是吃終身俸的,萬一回去了,終身俸就沒了,隻好努力壓抑自己。他老講北京的什麼,興緻好的時候,自己做一做家鄉小吃,偶爾講老家的事,講我爺爺,但講得不多。後來漸凍了的身體把他囚住了,有生之年都不曾回鄉,好慘。2003年,他去世了,後來葬回了北京,了卻他的心願。
鈕承澤
北京,一種想象的故鄉
以前我和我爸沒那麼水乳交融,從小背負着爸爸口中的北京,那樣的北京對我而言是痛苦的,我連做夢都會夢到北京,但我不知道那個圖像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以前被爸媽打罵之後,就會一個人到房間把門鎖上,大哭着叫奶奶——幻想有個奶奶,他會撫慰我,我常跟想象中的爺爺、奶奶說話。北京一直是這樣的一種存在。
北京對我有一種超越血緣的連結感,身為旗人,我一定有些來自基因的設定,比方我運動細胞差,但一上馬就會騎馬,拿起箭就會射,我覺得這跟基因有關。
之前我去北京,覺得一切都很親切,聽到那些人講的都是我爸、我外婆的口音,我沒有任何的隔閡。還有很多方言,北京現在的人已經不講,隻有我爸會講。比方他會講:“你怎麼那麼‘怯’?”是指“你怎麼那麼土”;或是講“拿墩布來擦幹淨!”,其實是那拖把來抹地闆。
這些北京方言,從小我就聽熟了。
我記得有天半夜,我跟周迅和她朋友三個人去騎車,在天安門一帶的胡同瞎轉兜繞,我一面騎,一面感覺這空氣的溫度,那整排挺拔的梧桐樹,我知道這些巷弄胡同都是長久存在的,而我爸爸他們一家顯然也走過這樣的路線,覺得好熟悉、好親切,有了某種奇特的連結,于是我發自内心很戲劇性地說:“爺爺、奶奶,我回來了。”在那晚的氣氛下,我開了這樣的傷懷但又溫暖的玩笑。
雖然如此,台灣是我的家鄉。我的朋友、我的貓,這裡充滿一切成長的東西,以及我的食物文化。但北京是我始終不能割舍的,是來自基因、來自血緣的一份連結。
認同哪裡?愛不愛台灣?一直是這幾年很煩人的政治問題。我很多好朋友都是本省人,有很長時間,彼此不太會觸碰對方的傷口。族群是這幾年才有重新被挑動起來的。
“外省人”的傷感
我覺得台灣不要再講“外省人”三個字,“外省人”這三個字,對我來講是非常傷感的。
我二十歲左右大量閱讀《新新聞》、《人間》等雜志,非常有使命感,很關心底層,想法很左,一度有激烈的思想,覺得腐敗的國民黨需要被推翻替換。年輕的時候,很容易會有想要做什麼的沖力,這裡面有青春期的焦慮、革命的英雄主義,好像為了背後很大的目标,可以怎樣怎樣。其實後來才知道,獻身革命的人并不一定是想要讓這個世界更好,可能隻是找到一面理想的旗幟,可以追随、依附,然後可以滿足,或是治療自己。在這背後可能是盲動,是自己焦慮的宣洩。
是以我曾經很支援陳水扁。1994年,台北市長第一次選舉時,外婆說,我家最民主了,來來來,告訴我,你要投誰。因為她先講了我們家“最民主了”,是以我大方講:“陳水扁啊。”結果,外婆拉高八度音大叫:“什麼!”之後大罵:“你怎麼可以這樣,這樣對不起死去的外公!”
為了阿扁,我弄到跟家裡決裂,跟朋友無法來往,我媽媽要跟我脫離母子關系。結果,陳水扁當選後,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對街慶祝,但當晚我卻先走了。原因是:第一,有些閩南語發音我聽不懂;第二,我感受到他們對我血液的敵意。
作為一個外省人,好像背負了原罪。我怎麼了?做錯什麼了?從小在台灣出生成長,離開台灣的時間加在一起沒有超過一年,到現在也沒有去移民,為什麼我要被排擠?我有一種很落寞的感覺。我已經不認同國民黨的腐敗政權,但在這裡我又是外人,好像夾在中間。
1996年,台灣選地區上司人時,我到大陸拍戲,人家把我當台灣人;中間我去美國,因為長得黑,又被當成印第安人;回到台灣,原來我是“外省人”。結果,他媽的,哪裡是我的家?
我的前女友是深綠的,我自诩為中間選民。她們家也有傷口,她阿公講一口漂亮、标準的日語,國民黨時代在鐵路局工作,明明非常優秀,卻被打壓。2004年投票前一天,發生“三一九”槍擊案,那時我在拍戲,她打電話給我說:“哇操,這真是太屌了,陳水扁竟然搞這一局。”
她是深綠,也認為子彈是假的。第二天,她卻穿着打扮好好要出門,我問她上哪裡。她說:“去投票。”我問投誰,她回答:“投阿扁。”我拉住她:“等一下,等一下,你不是說子彈是假的嗎?”她回說:“沒辦法,我為了阿公。”她把我推開了,為了阿公去投阿扁。可是到了2008年,她投不下綠的,但也沒辦法把票投給藍的。
我身邊有非常多這樣的朋友,像一位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的好友,她們家是深綠的,以前我去他家吃飯,他媽媽還用閩南語問我:“你甘系新黨?新黨系匆駛(不能)來阮兜(我家)喔!”現在這位朋友也不投票啦。
我想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有各自的傷口,而傷口終究有複原的過程,它會被忘記。其實台灣早期移民也經曆過一段混亂的過渡期。福州人跟漳州人打,漳州人和泉州人打,閩南人跟客家人打,漢人和少數民族打,大家都如此。每個人都在這個過程裡,但打完之後,不就是尋找尊重和包容,大家才能相處下去嗎?
民進黨執政時,我有個很大的恐懼,無涉統獨,而是從未來發展的角度看,我想台灣和大陸應該要維持一種“相處之道”,而不是切斷。切斷就是自閉封鎖,回到萬曆十五年時,不過,明朝那時還有大中華的疆域,我們現在隻有一個小小的島嶼。
台灣某些無恥政客操弄族群,很清楚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操弄背後,一定有特定目的,也一定有傷口。有傷口才可能被撩撥嘛!這幾年,族群成為可以挑動的議題,代表還有這樣的人口和這樣的問題存在。我覺得現在就是過程,就像疹子,趕快發一發吧!
找到和自己相處之道
我拍《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原本是要探讨目前島内的政媒亂象,以及“為什麼我們在台灣活得這麼不快樂”,結果拍到最後,解構了自己。
原本我設計一個“谑而不虐”的橋段,要在電影裡扯掉邱毅的假發。我們劇組跟他進行了兩個小時正式的通路,我看到他天真浪漫、自戀的一面,甚至午夜夢回的傷痛,我與他有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我們對另一個人會有反感,往往是因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也有的讨人厭的部分,好比邱毅那種自以為是的英雄主義、喜歡成為聚光燈焦點等等。那些東西我身上也有。後來他真的被人拔掉假發,我有很深的同情,不隻對他,還包括拔他假發的人及其背後的原因。
我們總是喜歡把手指着别人,這樣就不必面對自己的問題、自己的傷口,我們也很容易沉浸在負面情緒中,喝酒、吸毒、買名牌、盲目追求成功,但都沒有好好想過,自己才該為這些事情負責,其實政客和媒體隻是反映了我們複雜混亂的内在罷了。
我曾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但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卻不知不覺腐爛發臭,甚至得抑郁症。但我終究回轉成今天這樣的我,是因為我往内找,找到跟自己相處的方法,是以才可以跟這個世界相處。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曆程,連我這樣的人都可以變得有檢討的能力,充滿慈悲。我不是星雲大師,我仍然有欲望,有想要追求的,也還是會為負面情緒所苦,但我已找到跟生命相處的态度。對未來我并不悲觀,人惟有慈悲地對待自己,才可能慈悲地對待這個世界。
【聲明】文章節選自《台灣,請聽我說》(吳錦勳撰述,華夏出版社,2015年1月),“中國台灣網”頭條号轉發文章不作任何利己目的,隻為向更多讀者分享字裡行間“真實的台灣”。如有侵權,請聯系删除。
原标題:《鈕承澤:“外省人”這三個字曾令我非常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