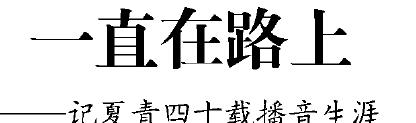
夏青, 原名耿绍光, 1927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早年就读于哈尔滨第一国高土木科, 毕业后, 为了糊口, 曾在哈工大当过土木科教师的助手和马家沟小学的教员。1948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并在学校里参加了进步组织“中国民主青年联盟”。1949年进入新华社新闻干部训练班学习。1950年5月, 毕业于北京新闻学校, 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播音员, 改名“夏青”, 取“华夏青年”之意, 自此开始了他四十年的播音生涯。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播音员, 夏青以其播音之雄浑、内容之深刻、逻辑之严密、分寸之恰当、声音之震撼, 被誉为“祖国的声音”。但在夏青辉煌的播音生涯背后, 很多人不知道, 病痛是他生活中的另一个主题。
1949年夏青在香山学习期间得了急性关节炎, 后来转为了慢性, 从此这个病就跟随了他一辈子。2004年夏青逝世后, 傅华曾有这样一段回忆:“ (夏青老师) 有时病重, 起来后全身是僵硬的, 他就用一条绳子绑在僵硬的脚上, 拉起脚往前迈一步, 然后再将绳子解下来, 绑在另一只脚上迈另一步, 让人看了特别心酸。”
对于夏青而言, 用绳子帮助走路已是一种常态, 和病痛做斗争也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变了的, 是时间和地点, 不变的, 是忍耐和坚持。不论是对待病痛还是工作, 四十年, 他一直在路上, 迈一步, 再迈一步。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始于偶然</h1>
1949年10月1日的那个难眠之夜,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长春市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作为“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的一员, 夏青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但他并没有想到, 这一天, 竟会成为他事业乃至人生的转折点。
参加完游行的夏青刚回到校园, 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 要他去北京新闻学校报到。北京新闻学校的前身是新华社新闻训练班, 以培养新闻人才、提高新闻宣传及相关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新闻业务素养为主要目的。此次其要求东北地区推荐十名学员, 夏青就是其中之一。
夏青接到通知后报名应试, 结果顺利通过。就这样, 22岁的他告别了短暂的东北大学中文系生活, 来到了北京新闻学校。在那里, 他经过了七个月的紧张学习。1950年5月初, 他和其他几名学员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当时和夏青同去的这批学员, 都是学编辑、采访业务的, 但是电台急需播音人员。情急之下, 电台决定让他们当中会说北方话的人统统去试音, 夏青自然包括在内。
或许是命中注定, 这次试音对拥有独特嗓音的夏青来说多少有点“量身定做”的意味。夏青的父亲是位国文教员, 在夏青还小的时候, 父亲就规定他每天必须大声朗读好几遍古文。小学时, 他参演双簧节目, 参加讲演比赛。中学时, 他参加歌唱比赛得过第一名。后来在东北大学和北京新闻学校学习时, 他还参加过歌咏队……所有这些经历, 磨出了夏青的一副好嗓子。毫无疑问, 最终嗓音天赋过人的他被选中了。几天之后, 夏青便走进了有点神秘的播音室, 坐在了话筒前面, 开始了他的播音生涯。
万事开头难, 刚进电台的夏青, 虽然嗓音天赋较高, 但在字音问题上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他那东北口音和广播所需要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有差别的, 有时甚至把“国”读成“果”, 这都需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过来。同为播音员的葛兰就成了他的老师, 每当他说错一个音, 葛兰就学他、笑他, 用这种方法, 反而促使他带着一股子倔劲, 决心狠攻读音。在那段日子里, 夏青带着最初的茫然, 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葛兰曾说:“为了学习标准读音, 他把字典都翻破了。” 千里之行, 始于此时。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2">为伊笃行</h1>
带着不服输的决心, 夏青“长期坚持吐字发声的基本功训练”。(6) 从抗美援朝的战争时期, 到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 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他都一直自觉地坚持训练此项基本功。
随着广播节目的多样化, 夏青还通过各种学习途径努力使自己的播音语言适应这种变化。他针对自己吐字发声的弱点, “向姊妹艺术行家学习, 先后向音乐学院老师学习音节发声, 向单弦演员学习吐字归音, 向电影学院教师学习发音方法”。直到上世纪60年代, 已经在播音领域有所成就的他依然虚心向语言学家周殿福先生请教, 反复听录音, 勤奋练习。
据《康熙字典》及其书后所附《补遗》, 中国汉字有四万多个, 常用的有五千多个, 播音员需要掌握的就更多一些。夏青长期坚持吐字发声的同时, 还努力学习和掌握每一个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 而且了解其出处、古今演变过程及趣闻轶事。到最后, 他便有了“活字典”及“字音政府”的美誉。一旦有人向他请教疑难字时, 他会立马详细地告诉他们这个字的读音和字义, 而且会翻开工具书来验证自己的说法是否正确。他的严谨和认真, 贯穿于整个播音生涯始终。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6">操千曲, 观千剑</h1>
除了“字音政府”和“活字典”, 夏青在播音界还有一个“老佛爷”的称呼。这些称谓, 不论是哪一个, 都在一定方面反映出了夏青的博学多识。
学生时代, 夏青既学过工科, 又学过文科, 知识比较全面。踏上工作岗位后, 除了不停地训练播音基本功, 他还抓住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
夏青酷爱古典文学, 逛琉璃厂旧书店曾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曾特地买了一套没有标点的《春秋左传注疏》, 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研读。在那本书的空白之处, 密密麻麻地注满了他的蝇头小楷。这造就了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 也为他的播音事业添砖加瓦。他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和欣赏》节目中讲解难度颇大的古典文学作品, 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称赞。
除了古典文学, 夏青还长期致力于研究语言学和语音学, 并且不断总结自己的发现和收获, 以及自己在播音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 撰写语音研究文章, 譬如《普通话广播的异读问题》, 他还在1983年的首届北京语言学会年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
夏青喜欢讲三个“万”, 即“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交一万个朋友”。 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 只有博览多闻, 才能做到学问习熟。他如此要求别人, 也如此要求自己。很多人对夏青所播的政论性文章赞誉有加:“有理”、“有力”、“有节”, 拥有“政治家的胸怀”和“雄辩家的机敏”, 这与他的博识是不无关系的。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2">亦师亦生</h1>
抛开1950年6月前的事情, 从1950年6月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室开始, 夏青就一直行进在不断学习、积累知识的道路上。经过几十年的沉淀, 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播音风格,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播音理论知识, 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播音工作原则。
他教导青年播音员要“三读”、“三思”。所谓“三读”, 就是拿到稿子后要读三遍:第一遍要粗读, 宏观把握, 了解整体, 如果细读, 反而会陷进去;第二遍要细读, 逐字逐句挖掘自己不懂的地方和有误的地方, 把握文章内在的逻辑联系;第三遍再粗读, 以防第二遍细读、分析之后转而陷入文章的细枝末节。所谓“三思”, 就是分析完文章后还要进行思考:第一是要把文章放到大的时空背景当中去审视;第二是要把文章放在整个节目中去审视;第三是要把文章放在听众那里去考虑, 从播和听的对比中思考实际的传播效果如何。这两点理论, 对后来很多年轻播音员的帮助是巨大的, 对很多同行的启发也是深刻的。
夏青过硬的理论知识和播音技巧使他成了很多行业和领域学习的典范。他曾是国家广电部门、教育部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广汉语普通话的负责人之一, 为推广普通话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因自己在汉语语音方面的学识和成就, 于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上被选为理事, 之后又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聘为审音委员会委员。很多时候他扮演的是老师的角色, 而他自己对此又是极为喜爱的。
夏青很关心青年播音员的成长, 他曾主动承担辅导青年播音员的工作, 深入基层台、站, 对青年播音员的工作予以指导, 同时也给播音短训班授课。他还经常被邀请到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授课, 为青年播音员队伍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 他也在指导播音的同时, 为播音部、台播部等的播音员讲授《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代表作。古典文学虽然是夏青的挚爱, 但要真正给别人讲, 他又得付出很多努力去学习。每次准备讲义, 他都得查很多资料, 将讲义写得极其细致, 这样在讲的时候才能真正让大家有所收获。
在年轻人面前, 夏青是前辈, 是老师, 但他从不自满。他始终以“学习者”的身份自居, 并且善于聆听。很多编辑记者、年轻同志乃至录音员有时给他提意见, 他都能听进去, 并择取有意义的积极改进。傅华曾回忆道:“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每次学习完一个单元的课程后, 夏青老师会出题考我们, 当时有一道题是有关‘元老’一词的解释, 他判卷时, 因我写了‘师长’的意思而扣我的分, 我便指出来, 他一句话不说立即去查字典, 而且特别平和谦虚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从偶然的前奏到辉煌的结尾, 夏青通过自己的努力奏响了一曲恢弘壮阔、感人至深的播音事业之歌。在播音乃至整个人生的大道上, 夏青从未间断前行的脚步。他的一生, 是走在路上的一生。这一生, 因为行走, 所以精彩!(《青年记者》2013年07期,作者毛雯芝)
葛兰 (生于1933年, 著名播音艺术家, 共和国第一代女播音员) 的名字, 对于共和国同龄人来说, 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每当有重要新闻, 大多是由葛兰和她的丈夫夏青两个人播音。他们的声音, 已经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无法割舍的一种记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1">在话筒前, 你的声音属于党和人民</h1>
“播音员是干嘛的?那不就是念稿子广播嘛。”这是葛兰在报考播音员之前的想法。在对播音这个职业的一知半解中, 1951年, 18岁的葛兰凭借着洪亮的嗓音和清晰的吐字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 葛兰担任了《记录新闻》节目的播音工作。“那时, 正值抗美援朝, 志愿军的抄收员就躲在战壕里收听我们播报, 一字一句地抄写, 然后再连夜油印成小报, 分发到前线的战士手里。”可以想象,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这些带着祖国和亲人们信息的小报是何等的弥足珍贵。“所以, 为了不给抄收员带来困难,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千万别播错。”葛兰说。
“战士们都说那是祖国的声音, 是母亲的声音, 很多人不惜用生命来保护它……也是志愿军那些动人的故事和不断收到的热情来信, 让我们真正体会了播音工作的神圣。”葛兰甚至还收到过志愿军战士从前线寄来的两个雪白的搪瓷缸子。那是战士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慰问品。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记录新闻》承担着向祖国各地传达各种重大消息的任务。为了让节目的抄收员能够记录播出全部内容, 播音员不仅语速要缓慢, 吐字要清晰, 在遇到易混淆或生僻字时还要进行解释……在播音中, 葛兰始终记住一句话:“不能播错。”在这句话的陪伴与鼓舞下, 葛兰培养了自己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能力。播音室里, 除了眼前的稿子, 其他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严谨的工作态度加上平时的认真学习, 令葛兰在播音时很少出错, 即使面对临时送来的稿件, 毫无准备时间, 葛兰也能够一字不差地播出。
那时的播音条件比较简陋。葛兰回忆说, 遇到夏天, 每人就给一块冰放在身旁降温;那时候人员也少, 我们一进播音室就是七八个小时, 一班下来累得头昏脑胀。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 从不叫苦叫累。
就这样, 葛兰面对话筒一干就是40多年, 声音传遍五湖四海, 话语润育听众几代。“业精于勤”是葛兰反复说的话题。她说:“坐在话筒前, 必须全神贯注, 丝毫不能大意, 这时你的声音已不属于你而属于党和人民。”
“我参加工作之初, 老同志经常很严肃地告诫我, 一定要认真备稿, 要多问, 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 不能想当然, 否则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就这样, 从1951年开始, 葛兰一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负各类节目的播音, 每天坐在播音室里, 面对小小的话筒, 用声音把党的方针政策传到千家万户, 把喜怒哀乐送到亿万听众耳中!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9">把“春江花月夜”念成“夜月花江春”</h1>
从1959年开始, 葛兰开始担任《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播音员, 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此前, 葛兰还曾经担任过少儿节目的播音员, 为了让自己的播音更好地服务于小朋友和家长, 工作之余, 她专门到北京师范大学旁听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课程。后来由于“文革”, 她的丈夫夏青被下放劳动, 葛兰也受到影响, 中断了正常的播音工作。有一天,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马上就要开播, 但当天的播音员始终不在状态, 情急之下, 葛兰被领导临时叫进了播音室。葛兰很快进入了状态, 情绪激昂地把稿件一字不差地播报下来。从那之后, 节目的播音名单上又重新出现了葛兰的名字。
对于过去的成绩和辉煌葛兰不愿多说, 她记忆最深的是自己闹笑话, 出“事故”的情况。
有时在播音间隙, 通常会放一两分钟音乐, 这在当时对于播音员来说, 可是个技术活。葛兰说:“现在都是用数字化设备, 操作非常简单, 只需几秒钟就可完成。而我们那时都是老唱片, 上边红字贴一条, 写着谁谁唱的。晚上我们报的新闻内容少一些, 中间能休息几次, 就找几个唱片播一下。两个大唱盘, 一边一个, 最难的是给唱片翻面, 要眼疾手快。一次我翻唱片不小心, 唱片竟然飞出去了。我赶快捡回来接上, 搞得狼狈不堪。幸好没有出错。这个工作看似简单, 却要求播音员一心多用。”
还有一次, 葛兰播放音乐时把乐曲的名称念成了“夜月花江春”, 有位老编辑顿时纳闷了, 这是一首什么曲子呢, 从来没听过啊?拿过唱片一看, 老编辑乐得蹲在地上, 原来唱片上的字被葛兰给读反了, 曲名是《春江花月夜》。“那种老版唱片字的顺序不一样, 我没注意就读出去了。幸好后来没有听众写信过来挑错。”为了这事, 葛兰忐忑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那个年代, “少儿节目”“新闻节目”等好几个频道都可以听到葛兰的声音。在严肃和活泼之间, 她的声音竟然能做到无缝切换。“大概是因为我的声音可塑性比较强, 什么节目都能驾驭。”
不过, 葛兰最喜欢的是文艺类节目的转播, 因为可以在剧场看不同剧种的大师表演。很长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到晚上到剧场转播的任务, 转播地点一般是在剧场的乐池或楼上一排中间。
“做文艺转播的时候, 我早早地就得赶到剧场, 往乐池中间一坐, 因为那个地方录音效果是最好的, 我比第一排的观众离舞台都近, 就是老得仰着头, 时间长了脖子疼。”葛兰深情地回忆说。
葛兰至今不能忘怀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转播梅兰芳的《洛神》。那一次, 梅兰芳一出场, 全场鸦雀无声, 葛兰小声介绍着, 因为周围太静了, 她的声音还是显得很突兀, 楼下的观众直向楼上看, 编辑吓得一个劲儿捅她, 葛兰赶紧降低了音量。转播了那么多场演出, 那次让她记忆最为深刻。(《新湘评论》2019年04期,作者孟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