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张先生,徐先生,各位同事,线上线下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刚才听到郎有兴先生说,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张厚安先生的学术思想,所以也想找一些线索,与张先生建立某种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先生对我来说主要是一个传奇,因为我与华先生建立了真正的学术联系,他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跟随徐先生担任博士后生。在此之前,从2005年开始,我打算做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乡村政治的,所以我开始阅读中方学者的相关著作,包括张先生的几本书。再往前走,1998年,当我还是大二学生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村级的民主社会实践小组,小组的一些成员还去中文老师拜访了徐老师,当时徐老师给了我们很多指导,还发给我们发了一份刚刚出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然后我在调查的基础上写了一份调查报告, 《经济因素对村级民主建设影响的简要分析》,后来发表在《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上,同期还有张厚安先生关于水月月村"村治"实验的文章。因此,我觉得这与华中师范大学"理论农业"的传统有一定的联系。在此,我首先要向张小姐表示敬意和祝福。
在传统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中,黄宗志先生谈到了三个维度,第一个是半正规管理,第二是第三个领域,第三个是集中式简单治理。当时,行政机关是这个成员的多数,没有官方地位,跟这些人做事,这些人都来自农村基层社会,国家会用农村基层的相关规则来治理社会,哪里有国家和社会有建设性的互动空间, 作为背后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压缩,农村治理越来越正规。三是集中简单治理,全权农村、国家集中,国家与全国的融合就是这样,但毕竟是处理纠纷、合作这些问题,还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执行。因此,中央集权极简主义治理运作的社会基础是当时经济社会本身的一套机制,在这种机制的影响之后,整个国家的参与可能会发生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图景大致就是在这些时期,清朝初到中后期基本上是"单纯治理的中央集权",到民国时期是土赞奇的研究提出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化",也就是这个时候国家在下移,但并不理想, 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农村基层社会和建立公共规则。以毛泽东时代更为特殊,毛泽东时代是经过政治普世制约,再加上政治动员,在强控的基础上引导农村,改造农村,但即使有一些基本面,这一时期还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村里人人所熟知, 因为当时人口流动太弱,村民之间的联系还是传统联想,自然村作为行动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到20世纪80年代,官方国家权力已经倒退到乡镇一级,村实行了村民自治,振兴了农村社会。也就是说,张厚安先生提出的"村治"模式,基本上可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集中化的简单治理",至少一部分是接近的。在这种框架和背景下,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税制改革之前,这一时期应该说,村民的自治得到了大力推进,但农村管理的趋势也越来越强,村庄本身的问题越来越多,当很多治理任务时,还是依靠乡镇行政权力来向村庄扩张来解决。
税改后,有学者发现,村级组织正规化,一些村干部如公务员拿固定工资和按时上下班,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出现了变化,国家从吸收资源向农村转移,增加了公共服务,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税改后,农村治理开始,出现了某种"制度停摆",国家能力减弱,基层渗透能力不足,但很快我们跳过了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以政党为主力的领导力量的新的全面干预,包括从"精准扶贫"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全国都已全面进入。这大致是形成高度集中和高度基层渗透模型的那种脉络。在这个模式中非常明确,一是治理重心的整体下沉,二是政党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全面延伸,现在强调的是党的建设领导,整个农村治理是由党组织带动的,这是基层的一大变化。三是下乡法则。规章,包括党纪和党规都倒下了,监督特别多,检查也特别多。第四是思想、符号和意识形态的整体沉沦。而第五,治理手段和治理技术这一块越来越复杂,非常强调信息和技术的使用,这是专门针对人类的信息应用,后者的平台也非常发达。我想总的来说,整个村子这个包括监控管理技术的发展,以前很难想象,总体趋势是社会自治空间越来越小,但毕竟还是有一些,到农村工作,或者利用熟人和当地人的知识来这一套。在第三个领域,这个街区也有结构性的转变,即在权力对比和格局上有所变化,现在整个村越来越形成对党政制度的依赖关系,而不像以前这种相对平衡的互动关系,现在的农村自治比较薄弱, 因为它对国家很强,国家向国家帮助国家,给予更多的资源,话语权也很强,这种趋势。
最后补充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学术研究做得更远一点,想得更深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狠"的反思,首先是目前这样高度集中、高度基层渗透的模式,是否还存在一些治理风险?就其可持续性、成本消耗和效益而言,还包括早上张先生提出的,是否真的有通过农民的充分表达,是否有与他们充分沟通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或者党和政府是否要取代他们来做决定。这些问题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体现。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农村在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之后,还应该有某种稳定的自主性。二是目前的下沉模式,可能模糊或抑制农户自治,导致农民信任地方和基层,信任中央政府,这种模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因此,最后的总结是,未来需要审慎定位"集中极简主义治理"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作用。高度集中化、基层渗透率高的大框架是前提,但"权力下放极简主义治理"作为相辅相成,应妥善考虑和安排,这或许仍有利于农村基层的长远治理。这就是我要说的地方。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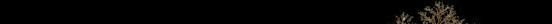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外政治制度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地方政治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村发现转自:田野政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