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无心于国主之位,却又贪恋于奢侈的生活。他从小不问政事,只潜心于经籍乐律,用诗词歌赋润泽着那些似乎永远不会改变的岁月,乐得做个富贵闲人,自由自在。可是命运却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太子病逝,他,成了南唐的国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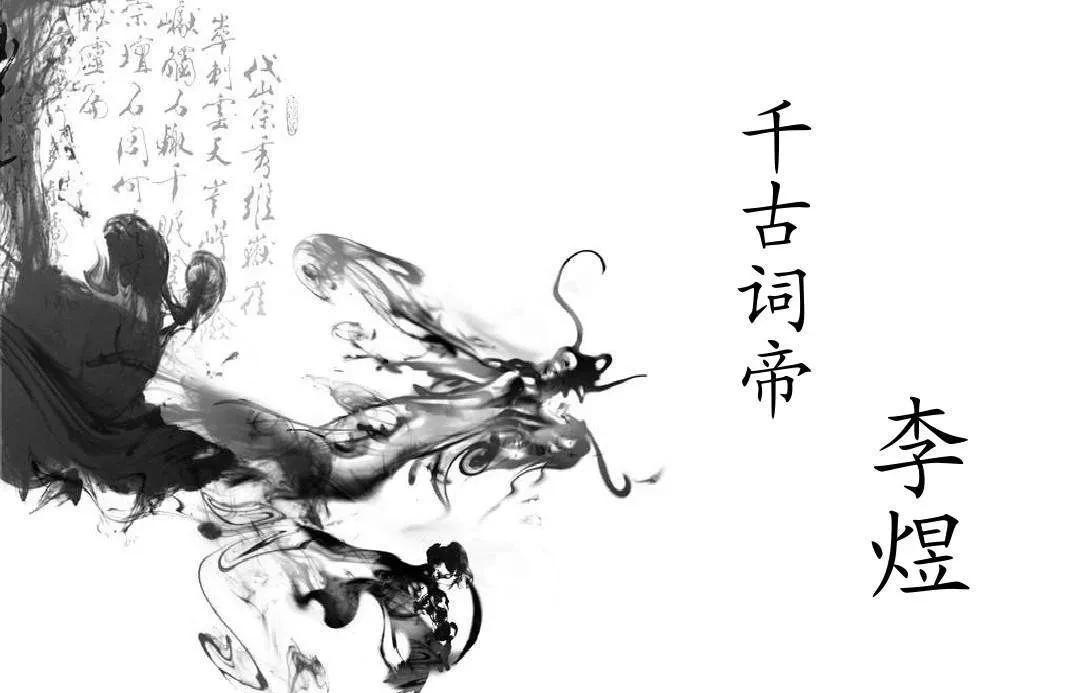
南唐山河憔悴,风雨飘摇。而作为帝王,李煜却过上了风流帝王的奢靡生活,日日听歌赏舞,吟诗作画。王国维曾这样评价李煜:“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最终,真性情,让李煜国破家亡,让他的人生路步步带伤。“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这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同一时期正是中国的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借尼采这句话,评价南唐时期李煜词,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叫“以血书者”呢?看一首后主的《浪淘沙》。
《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李煜 〔五代〕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这首词是词人从一个亡国之君的立场和思想感情来写他追怀昔日帝王生活的悲哀和寂寞,词中以直抒悲怀领起,继之以一系列鲜明的图景。词中有眼前景,有象征景,有想象景,把他的凄凉之感,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寄寓其中,突出地表现了词人善于捕捉形象的艺术才能。
上片着重写日间的寂寞与悲哀。“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白天百无聊赖,想起以往在秣陵度过的太子、帝王生活,内心只能涌起一阵阵的悲哀。“只堪哀”,语调沉痛,是不堪回首、强行忍受之义。对着眼前的风景,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也难以排解这种悲哀之情。通过衬托倍增其哀。全词一开始就以悲抑怨恨的声调冲激出来,今昔对比,哀乐迥异,总摄全篇。
接着写所见与感受。“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萧瑟的秋风中,幽禁处庭院中的一切是如此凄凉,连那苔藓也渐渐地铺满了台阶,很长时间没有人走动了。既然无人进出,也就听凭珠帘空垂着,毋需卷起来。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大词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李煜从过去的“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热闹非凡到如今死一般的静寂、冷落,心儿在滴血,是无疑的。于是发出“终日谁来”的悲叹。这既有对昔日和平安定生活的追念,又吐露出对今日处境的愤懑与不平。
下片则着重写深夜的孤凄与悲凉。“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这两句由眼前独囚之悲过渡到往昔亡国之痛。“金锁”指铁锁链;“壮气”谓兴旺的王气;“蒿莱”,野草,这儿用作动词,即沉没于野草。《晋书·王濬传》载:吴国君主孙皓用铁锁链横断长江,来抵抗西晋水军,结果仍失败灭亡。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就曾用“千寻铁锁沉江底”、“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诗句描写过这件事。李煜则更贴切、更凝炼、更沉痛地用这个典故自比,发出同样在金陵失败亡国、王气告终的悲叹,字里行间包含着“一旦归为臣虏”的无穷悔恨和“最是仓皇辞庙日”的种种回忆,从而使“往事只堪哀”得到了具体深刻的发挥。
接着词人顺势而下,由往昔亡国之痛自然递入现实凄凉之感:“晚凉天净月华开”。秋晚充满凉意,天空万里无云,月光普照人间,这本是一幅美好明净的秋夜图,但以词人此时处境而言,则多了一层“凉”意。这样写,既与上片秋日阶藓的凄凉寂寞遥相呼应,情调一致,又为下文遐想故国的空自嗟叹作好了铺垫。
正因如此,由现实情景飞跃到想象情景的描写,就水到渠成了。词人身在囚室,神驰故国,想象眼前这同样的月光,该把南唐故国那些象美玉一样玲珑剔透的华丽宫殿照个通明,而投影于横贯南唐都城金陵的秦淮河上吧。玉楼瑶殿,影照秦淮,乃是昔日金陵帝都的绝妙剪影,使得词人朝思暮想,刻骨铭心。然而“想”终归是“想”,如今早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了。词人着一“空”字,既形容月照之空寂无声,更双关着江山易主、徒然无用之意,这就把他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凄凉之感,全部熔铸其中了。
纵观全词,以首句的“哀”统领全篇,再用虚实相间的凄美之景渲染心中的愁苦,读来令人动容。清代文人陈廷焯对这首词的评价是:“凄恻之词而笔力精健,古今词人谁不低首”,这话说得确实是没错的,只能说在凄情上词中之帝果然够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