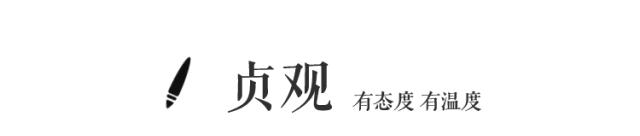
1
“一天早上,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是卡夫卡《变形记》的开头。这一句话,不知道点醒了多少想要成为大作家的人的再一次想要在写作之困境中再次尝试的努力和梦想。比如那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马尔克斯,而且,他成功了。
但是在这样的大量存在的、受到了《变形记》开头影响的文学爱好者当中,没有包含我。因为我曾经想,我永远不会在自己的文章中写到,我会变成一个“大甲虫”。哪怕是做梦,也不会梦到自己变成类似大甲虫这样的东西。——这个甲虫,太不幸福了。
■ 图源网络
蜷缩在狭小的房间里,浑身坚硬,每移动一步,都是连滚带爬,跌跌撞撞;尽管他曾经的努力工作是家里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是一旦他变成甲虫,立即被所有亲人嫌弃,以至于最后,老爹还朝着他/它扔了一个苹果,苹果嵌入他/它的身体,腐烂,而他/它的伤口发炎,发炎,终于,死了。在他临终前,他仍旧“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但是爹妈和妹妹呢,则“乘着电车出城到郊外去。车厢里充满温暖的阳光……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谈起了将来的前途……”
看到这里,眼泪止不住地流。太不幸福了,我不要这样的人生。也不要这样的想象。哪怕写出这样的文字,会成为世界大文豪,我也不要这样的生活。
我曾经梦到过自己是一条柔软的小虫子,在盛开着牵牛花的清晨的田野里探出头来,那时候,那个尽管只是一条小虫子的自我,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满心希望自己能够对全世界的人都好,所以后来,力所能及的,走过了一些地方,足迹所到之处,我总是会发自内心的地笑着,感觉自己能够接得住所有人的言论、目光和心意。我还曾经梦到过自己变成了一条掉进水坑的大黑猪。做了这一个变黑猪的梦之后,我按照我们老家那个地方的方言所提供的逻辑,解析了自己的梦:我属猪,所以猪就是我;掉进水坑,说明自己掉进了幸福的漩涡。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想象,哪怕是头猪呢,也是多么的好啊!做完这样的解析,我继续践行我的认为人生应该“幸福”的人生观。
但是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好像是被新冠疫情带来的。新冠来了之后,有两年的春节没有回过家,老爸老妈三年来的生日,都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不能回家;其他的节假日,本来也都有回家的安排,多半都被取消;这样,除了住在一个小区里的熟人,生活在其他空间里的人,失去了大多数的能够开心见面的机会,以至于在网络上看到生产于2020年以前的电影,都会嫉妒历史:银幕上的那些人,都不戴口罩,到处的走来走去,吵来吵去,打来打去,恋爱来恋爱去,太气人了。这时候,我们没办法不套用卡夫卡的句子:
“一天早上,***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的手机上又有了一条通知,要求每一个人,非必要,不出门。”
卡夫卡,你牛逼,我终于引用你了,因为我从里到外的,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
2
短时间的不出门,目的是为了截断感染源,这是古往今来人类应对传染性流行疾病的最常用的方法。但是人总是不出门,不被允许出门,根据我的经验,它会促成人的怀疑的坏习惯。这个怀疑,应该不是哲学层面的怀疑主义者的怀疑,因为所有那些可以称为怀疑论者的哲学家,他们总能够很清楚地说出,自己怀疑的是什么,而我不能。
我的这个怀疑,最多只能说是疑神疑鬼。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城市总是连续不断地下大雨,结果我们的小区有一天突然就停水了。一发现这个“突发事件”来势不妙,我赶紧将睡得迷迷糊糊的老公叫起:快去,快去,快到超市买水!他先是一个愣怔,问为啥要买水?我说停水啦!停水就要买水?对呀!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啊!你看外面这雨,天昏地暗,跟马孔多镇一样,有停的意思吗?世界末日就要来啦!然而他,镇定地说:我决不会去的。然后他起来,穿上衣服,上班去了。
看他那么坚决,而且已经闪人了,我只好自己去了。超市里当然在排着长队,而且桶装水已经没有了,只有瓶装水。即便这样,人们还是用各种方式,尽量多地,往家带水。在小区里看到有人用桶接雨水,接雨水的人碰到认识的人,好像有些不好意思,解释着说:“咱还没有富裕到用瓶装水冲厕所的程度,对吧?”
■ 图源:央广网
后来的三天时间里,每天的户外,都是大雨滂沱。停水不久,小区来了一些送水车,很威武地站在那里,供大家拿桶去接。晚上的时候,老公面带微笑,亲切问候我这个大惊失色的人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说,我还是觉得要尽量少地喝水,尽量少地吃饭,尽量少地冲厕所。他更加开心地总结道:对于你这样的人,我真不知道该说啥了。看到他的样子,我也很好奇,尽管事情解决了,难道这种突发事件,对他的心理感受没有影响吗?难道心理上的感受,不是一种绵延的感觉吗?总之,就在我俩形成的小小的可交往的人际圈里,我俩对事物的认识、评价和感受,都是那样的不同。
——后来,随着防疫政策的越来越灵敏,越来越周全,只要看到新闻里报出新增一例本地感染者,我就赶紧到超市去,买点东西带回家。而且,一定不会有错的是,每当我想买点东西囤起来的时候,超市里总是在排队,可见,我和我的邻居们在这件事情上,其冲动感的到来,是绝对同频的。几年来,网络上动不动就有人传播某地超市货架被买空的镜头,我也多次犯了这种感觉到世界末日就要来到的慌张病,而我的老公,他也当然不会错过能够多次毫不留情地嘲讽我的乐趣,但是我的这种感觉,总还是消除不掉。
■ 图源:央广网
——感觉这东西,是自己的啊!别人的感觉,代替不了我的感觉啊!我不能将自己的感受权,交给别人的啊!就好比若干年前,我不相信自己会变成一个怀疑论者;现在,我所怀疑的是,若干年前的那种打开心胸接纳一切的感受,会不会还有机会降临在我们此生尚未到来的那些未来岁月中?
在这样的心情中,翻开卡夫卡的《审判》,开头第一句话:“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卡夫卡,你可真是烦人啊!我原来总是相信“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原来根本看不懂你说的“无缘无故”是什么感觉,现在看懂了你的话,我的本来很烦人的生活,更烦了。不由得想起来一个问题:一个人,有没有感觉烦恼的权利?一个人,他感觉到烦恼,这是不是一种属于人的自然现象?这好像是一个历史问题,没有想到,今天,还得再问一问。
3
所以,前一段时间,因为读卡夫卡,见到什么都很烦躁。
这一段时间,又很想写点什么,写一写在此情此景中,阅读卡夫卡的感受。尽管读懂卡夫卡,并不是一种好的感受。
写出来,好像比放在心里好点,尽管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写出来比不写好。
写出来,是一种虽然说不出,但可以写得出的情境下的选项。有选项,自然要好过没有选项。
写出来,似乎更能获得一种审慎观察、努力思考的“尝试”某种解决的可能性的满足。有可能性,当然要好过没有可能性。
写出来,将类似卡夫卡式的体验也出来,这正是卡夫卡伟大的文学遗产在今天复活的机缘。他以一种忧心忡忡的热情,触及了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而当写到他的人物与那个想象中的世界的关系的时候,一开始,他是这样写的:
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点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汤永宽译)
“黑夜”,“积雪”,“城堡”,“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即便前面四个关键词已经提示了一个灰度很大的情景,这个K,他依然凝视了。是的,尽管那个城堡很空洞虚无,但他还是要看一看,它是怎样空洞虚无的;尽管他早已知道那个城堡是个幻景,他也一定要知道。它是怎样的一个幻景。
这个K在那个本来打算只是临时歇脚的村子里,可以说是拼尽了所有的努力。他本来的目的,是要到达城堡,做伯爵聘请的“土地测量员”(多么奇怪的一个职业!你说它重要,它就重要;你说它不重要,在见不到自己的聘用者的情况下,这怎么能算是职业呢),但是他才只是到达歇脚的村子,就好比深陷泥潭一样,向前再走一步,都那么不容易,都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需要一张无法开具的通行证、聘用文书消失在文件的海洋中、怎么也见不到那个好像决定着他的命运的村长……
雪,依然;黑夜,依然;寸步难行,依然。然而,在经历了这些“深陷泥潭”一般的琐碎和愤怒中,卡夫卡再一次让这个K,凝视了他曾经凝视的城堡:
城堡的轮廓已经开始渐渐隐去,但是仍然静悄悄地耸立在那儿;K看不到那儿有一丝生命的迹象——或许从那么远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可是眼睛总想看到一些什么,实在受不住它那样的沉寂。K观察城堡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好像在看一个坐在他面前凝视着他的人,这个人不是出神,也不是忘却一切,而是旁若无人,无所顾虑,好像并没有人在观察他,他仿佛是独自一个人似的,可是他一定知道有人在观察他,不过他仍旧镇静自若,没有一丝儿局促不安;真的——不知道这是他镇静的原因还是因为镇静而产生的效果,——观察者的目光往往无法集中在他身上,只能悄悄地转移到别处去。在今天这样暮霭未浓的天色下,更加强了这种感觉;你看得越久,就越看不清楚,在暮色苍茫中,一切也就隐藏得越深。(《城堡》,汤永宽译)
“可是眼睛总想看到一些什么,”K就那样努力地看着。K看着看着,那个其实看不清的城堡,好像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旁若无人,无所顾虑,即便知道有人在看他,他也会镇定自若,并且还会让看他的人、观察他的人、凝视他的人,有一些害怕,让“观察者的目光,往往无法集中在他身上”,并且还要将目光“悄悄转移到别处”。他假装不知道有人也在看他。喜欢假装不知道,这就是一个脸皮厚的人。
面对一个像城堡一样,总是摆出一副“旁若无人”“镇定自若”的模样的人,K,他能怎么办呢?
■ 图源网络
我真想多百度几次,看看那些世界级的大文豪,他们在面对一个个具有种种特殊性的世界的时候,都在做什么。像托尔斯泰,他就参军了,参军回来之后,还可以成为一个大文豪;卡夫卡呢,他,就只是一直睁着他的童真的大眼睛,看着他的那个世界,思考着他的那个世界,以一种一定要登上文学之高峰的决心,营造着他的世界。世界在变,人们忙活的方式,也在变,从腰间拴着粗粗编织的树叶子,徒步东奔西跑,到乘坐马车东奔西跑,到乘坐绿皮火车东奔西跑,到坐着飞机或者高铁东奔西跑,再到因疫情管控呆家里在网络上东奔西跑,在这些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中,文学和艺术,它们始终在保存着我们的心,用豪情万丈的方式,或者用极度颓败方式,保存着我们的心。——看完托尔斯泰,总是那么安慰,因为他让你相信,无论多么混乱的世道,人的心,总应该是热的;读完卡夫卡,你可能感觉不到安慰,因为他有可能让你感觉到,活着,就是一场坚硬的忍耐。
所以,我真心不想读懂卡夫卡。因为我不想让人生成为忍耐。
但是,像感谢托尔斯泰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感谢卡夫卡,因为既然现在的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做一个在鲜花丛中探头探脑的小虫子的梦,既然自己,再也不会梦到自己是一头掉进幸福的漩涡的大黑猪,忍耐就是现实本身。而既然是忍耐,其过程,必然是很困难的。在这种困难的情势下,卡夫卡也许会告诉我们:好不好再试着凝视一次那个造成了你的不爽体验的“城堡”。尽管那个“城堡”有可能真的根本不顾虑你,但你凝视了,你主动了,你存在了,你的忍耐,就不完全是一场悲剧了。
卡夫卡让他的K,就是这么做的。因为如前所引,他让K第二次凝视了虚无缥缈的城堡之后,小说的故事,才进行了一小半,K,他在那个好比深陷泥潭的村子里,继续战斗了另外的一百多页篇幅。更加令人佩服的,是小说直到最后一页,故事都没有结束,因为K最终没有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弱者的观察和凝视的权利。“你什么都不是”,这是K的未婚妻的妈和所有村子里的人,对他的评价。
作者 |番小茄 | 阅读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