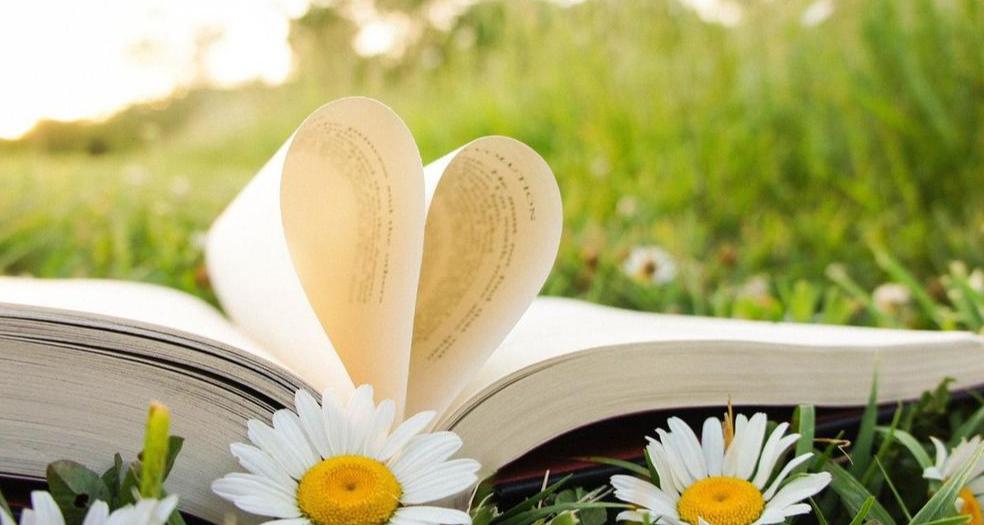
让阅读与写作慢下来
龚会
这样的人间四月天,诸多困苦艰难在世界一个又一个地方此起彼伏。眼见得满屏疫情苦,却帮不上哪怕是递一棵菜送一杯水的小忙。做点读书人本分的事,安静地隐于角落,老老实实读点书。偶有所思所得,随手记录。若将来有阅读者能从中获益,有助于文明的传递,便是不负苟活于世的岁月。
今日读到《南齐书·文学传论》上这几句:“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无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便对当下网络世界“速文”甚为忧虑,某些自媒体已经将文学变成了随意堆砌的文字,将生活中鸡毛杂碎全部搬上某号某圈某音。甚至,无底线地卖弄个人癖好,在虚拟的空间里强占人们的视听感官。泛滥的网文失去约束,缺乏审美,或不辨是非,泥沙俱下。内容空洞,形式流俗,没有思想。老祖宗们惜字如金的教诲刻印在泛黄的文献上,堆放在图书馆陈列架上,藏书家的柜橱中。与超速的网络世界拉开遥远的距离,世间真的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故纸堆里挖掘珍宝了。古人著文,需凝神静思,需意在笔先。著文之后,需捻须苦吟,需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耗心血凝深思的文字,一个个鲜活上千年。而今满屏文案天天公号,手指一动,键盘一响,东拼西凑有之,篡取他人之文有之。一天数千言上百首,“唰”一下群发,铺天盖地刷屏几秒,又被下一个“唰”顶翻,了无踪迹。分钟几百条信息量,几人能记?谁家有诗?何人著真文?
著文之道,冥思苦想,感召无象,变化无穷。古人说:“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为文之思,是多么浩荡辽阔。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创作出来的诗词文章,才会跨越时间空间,才能历久弥新。凝神静思需要慢下来,再慢下来。而身处连数钞票都嫌慢的时代,人心浮躁,怎么慢?速成的不仅是食材药材建材更有专家学者诗人作家,满地都是,比秋天的落叶都多,怎么慢?
从前我也很勤奋写作,认真生活。而今我还是在写作,在认真生活。但是文章生成如十月怀胎之缓慢,生活又是文章孕育的土壤。当生活被敲击成一地碎片,划破身躯,割伤灵魂,我却依然在凉薄之中寻找深情的缝隙,并诉诸文字。只不过脚步慢下来了,心也慢下来了。在荒无人烟的荒野,在堆积砾石与苦寒烈风的高原,夜深人静之时,仰望满天星斗,追逐流星滑落,聆听雪域高原上清冽而纯净得一片空灵的潺潺流水,俯拾一片月光洒落大地的圣洁。大地如此深厚,天空如此辽阔。拥挤的只有风,只有砾石,连草木都远离了这样的空旷,连鸟雀都飞不过那些雪峰。我就躺在空旷和辽阔里,把自己变成了一枚历经万古风雪的砾石,也还原了一个人本真的渺小。“道法自然”是多么深刻而神秘的谮言!回到人群与文字之中,我的眼里不再忙碌杂乱,不再声嚣尘上。无论多高的头衔都只不过是一段别人经历的路途,它们会被时间或者时势送到一个路口,头衔会被别人戴上。光秃秃的头顶不再有光环时,或许能咂摸出冷暖炎凉,看清本相与人性。但依然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追逐虚幻的光环,在虚幻的光环中迷失自己。当下沉迷虚像的网络各平台写手如过江之鲫,一潮涌起,一潮跌落,且将“文与笔”糟蹋为名与利。哪儿还有“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那样的作品?
写作者心不静,神不宁,何来文之妙,理之趣?
不由得想起了字库塔,顿生敬畏。因行走于古道老街乡野荒原之间,僻远的古村街口处、古老的寨堡寺庙旁、驿站古道边,偶能寻见青灰色石垒或砖砌的六柱体八柱体。即使残破,遗存的形体也古拙肃穆,与道旁场边村口供奉土地公婆的神龛有所不同,乡老曰“字库塔”。也有云“惜字炉”或“焚字塔”者。问询村夫老妪,都能说出一段传奇来。大致说法:糟蹋字纸会生疮害病、瞎眼睛,受到惩罚并祸及子孙等。所有用过的字纸或废书,都要统一收集起来,放到一个地方集中焚化。且要择良辰吉日行礼祭奠之后,再点火焚化。
由此可见,书籍文字在老祖宗的心目中是多么神圣!
沧海桑田,保留在民间的敬畏已经随着乡村的枯萎而枯萎,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而堵塞。当一栋栋冲天的高楼大厦拓展着城市的规模时,人心被挤进了一间又一间物质的方盒。在瞬息万变的时光带上被传输,变形、变色、变味······
静坐蜗居,屏蔽电子声响,翻开泛黄的书页。再读一遍“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无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
神与物游后,杂记之。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版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