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踏进王维的宅院,就听到悠扬美妙的琴声。他停住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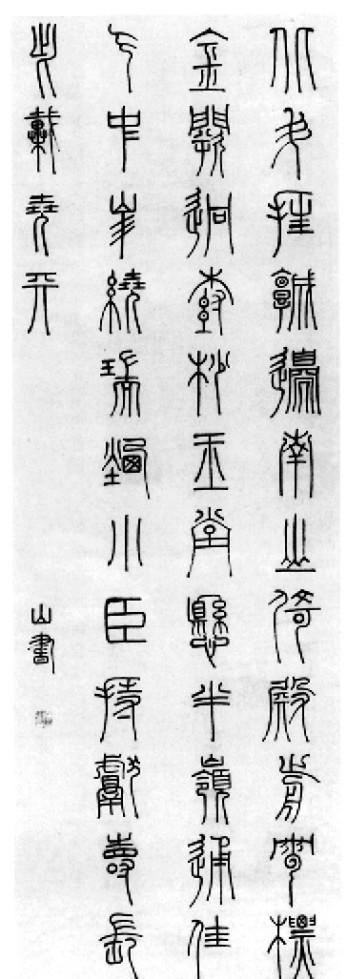
伫立在院子里,屏息倾听。
王维在抚琴。他半闭着眼睛,心静如水,手指轻轻拨动琴弦。深深陶醉在乐曲的韵律中,一时间竟忘记了自我的存在,仿佛化作了一只鸟儿,飞到了琴声所描摹的幽深苍翠的森林里。继而,暮色朦胧的林间依稀飘下小雨,淅淅沥沥的雨滴落在树梢上,又顺着枝叶流下,宛若汩汩清泉,悦耳的水声令人心旷神怡……
一曲终止,王维的情思从音乐世界回归了现实,才看到院子里陌生的客人。
王维站起来:“请问,你是哪一位?”
孟浩然也陶醉在琴声中,此刻如梦初醒。看见比他年轻 12 岁的王维,儒雅大度、风华正茂,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想到自身已届不惑之年,依然前途渺茫,又顿生悲戚,深鞠一躬:“在下襄阳孟浩然,对王维君仰慕已久,特来拜谒!”
“哦,你是浩然兄!我读过你的《夜归鹿门山歌》《过故人庄》,喜欢你的
诗。快请进!”
主客二人落座,童仆送上茶水。
王维歉意地说:“你早就到了吧,让你久候了。”
孟浩然说:“哦,不是久候,是享受。我从未听过如此美妙的琴声,天籁之音啊。”
“你过奖了,我只是自得其乐而已。你到长安来,是来应试的吗?”
“正为应试而来。”
“那么,你这是……”
“我,落第了。”孟浩然一声叹息。
王维心中一沉,不由得想起了同样是落第的綦毋潜。前有綦毋潜,后有孟浩然!王维可不愿意接下来听到“还乡”“归隐”之类的言辞,故意岔开话题:“你是第一次来长安吧?”
“是第一次。”
看到孟浩然身穿粗布衣衫,浑身洋溢着乡土气息,又难掩诗人的风雅气质,王维忽然产生了作画的念头。
“浩然兄,我来给你画一幅肖像吧!”
“初次拜访,不敢烦扰王维君。”
“这不是烦扰。我读过《过故人庄》,诗如其人啊。喜欢你乡土田园的质朴气息,所以想为你画像。”
王维在光线明亮的地方放了一把椅子,让孟浩然坐过去,又命童仆备好纸笔和墨彩,开始作画。边作画,边聊天。
“你的诗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很有气势。来长安后,见到张说老丞相了吗?”
“拜见张老丞相了,他也看过我写的《临洞庭上张丞相》,很赏识。但老丞相年事已高,想提携我,却有心无力了。”
王维感叹:“张说当过三次丞相,不容易呀。他的文才更令人尊崇,‘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将会流传千古。未来的人们也许不知道作为丞相的张说,但一定会记得作为诗人的张说。”
孟浩然寻思:既然张老丞相都要以诗名传世,自己又何必费尽心思谋取一
官半职呢?回去安心写诗,不是更好吗?心里这样想,却不便明说。
王维又问:“你见过张九龄了吗?”
“见过了。九龄公与我相知已久,我们相见甚欢。但他当下的处境,也不方便提携我。”
说到张九龄,王维神色怡然:“‘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多美妙的诗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也脍炙人口。”孟浩然赞叹。
王维又问:“你在长安,还见到谁了?”
“王昌龄,我寄住在王昌龄家里。”
“哦,是写‘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王昌龄。他中了进士,对吧?”
“是的。”
“他那边居室狭窄,不如我这儿宽敞,你可以搬到我家里住。”
“多谢王维君美意!但是不必了。”
“为什么?”
“我就要返乡了。”
王维听到了他最不愿听到的话,顿感不悦,停止作画,把画笔拍在了桌案上。须臾,王维察觉到自己失态,神情缓和了,他要像当年劝綦毋潜那样,劝劝孟浩然。
拿起画笔,继续作画,王维慢条斯理讲起那段往事:“你看过我写的《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吧。綦毋潜落第之后,万念俱灰,来向我辞行,要归隐山林。我竭力劝说綦毋潜回心转意,对他说:‘当今圣上是英明的天子。我们生逢辉煌盛世,不可以做避居山林的隐者。普天下的精英贤才都应该争先恐后为朝廷效力,也为自身博取功名。你仕途受挫是暂时的,不能因此就怀疑我说的道理。返乡后认真想一想,想通了就回到长安来,我在这里等你!’綦毋潜听从了我的劝告,回乡看望家人之后,又到若耶溪游玩了一趟,散散心,写下一首《春泛若耶溪》,就回到长安来了。再次应试,他果然考中了进士!你看,听人劝告是何等要紧啊。”
孟浩然沉默良久,叹息一声:“我做出返乡的打算,也有自己的想法。来长安后,寄居在王昌龄家里。我们在同一盏灯下看书,同一口锅里吃饭,用同一个砚台研墨写字,夜里同榻并衾共眠。我对昌龄君的才学和人品都深为钦佩。然而,他的际遇也令我扼腕:考中进士,仅做了秘书省的小小校书郎,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家徒四壁。像王昌龄这样的贤才,考中了进士,境况尚且如此,我的才学不及昌龄君,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王维摆摆手:“你不要过于自卑,要有信心。王昌龄的境况是暂时的,将来肯定有升迁的机会。张九龄初入仕途时,也做过校书郎嘛。你听我一句劝,哪里也不要去,就留在长安!”
孟浩然疑惑:“留在长安,我能干什么呢?”
王维胸有成竹:“我知道,你博古通今、擅长诗赋,长安正是文人墨客聚集之地,你就留在长安吟诗作赋吧。凭你的才华,必可鹤立鸡群。我的人脉关系很广,帮你通融举荐。你只管即兴作诗献赋,尽情展示你的才学就可以了。”
孟浩然将信将疑:“我专将《临洞庭》呈献给张说老丞相,都不曾奏效。泛泛地作诗献赋,有何用处?这条路能走通吗?”
“能。其实这就是我当年刚到长安时走的路子。我15 岁来长安,因为擅长写诗、绘画和音乐,很快结识了许多王公贵族。有了人脉,事情就好办了。吟诗献赋,看似漫无目的,却能提高你的声望,让大家知晓你,这很重要。与当权者混熟了,关键时刻他们就会想到你。这样,你才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孟浩然喜出望外:“王维君的主意真是太好了。我听你的,不走了。”
王维哈哈笑起来,又认真地说:“跟你讲这些,显得有点粗俗。咱们都是秉性高洁的人,可这世道是庸俗不堪的。为实现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梦想,不得不违逆高洁的情趣,追求俗不可耐的功名,实属迫不得已啊!”
孟浩然认同王维所说的道理,除此之外也别无他路。
这时,王维为孟浩然画的肖像完成了,画中的孟浩然栩栩如生,风采神韵都跃然纸上。
孟浩然万分感谢:“我要把这幅画像永远保存,终生铭记王维君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