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销好书、高分影视剧自画插图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中篇小说《美丽与哀愁》,1961年开始连载,1963年结束,期间他说“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八年后的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口含煤气管的自杀方式离开人世,真的没留下一纸遗书。
从川端康成的早期作品《伊豆的舞女》,到晚期作品《美丽与哀愁》,如果仔细研究一条线的话,会梳理出川端康成自杀的原因。
他16岁时,最后一个亲人祖父去世,从小体弱多病的川端康成常年幽闭家中,心理既敏感又寂寞,不幸的身世使他形成一种孤僻的“孤儿气质”。这种性格成就了他的写作,也把他带入一种深渊,一生难以逃脱。
??[小雪]
谈《伊豆的舞女》,就会想起三口百惠,因为《伊豆的舞女》曾先后6次被搬上银幕,而中国观众只对三口百惠版的《伊豆的舞女》情有独钟。
三口百惠扮演伊豆的舞女熏子。19岁的高中生“我”,为排遣内心的忧郁与苦闷,只身来到伊豆旅行,偶遇流浪艺人一行。“我”被小舞娘薫子的纯真和美貌所牵动,不由自主地一路随同,直到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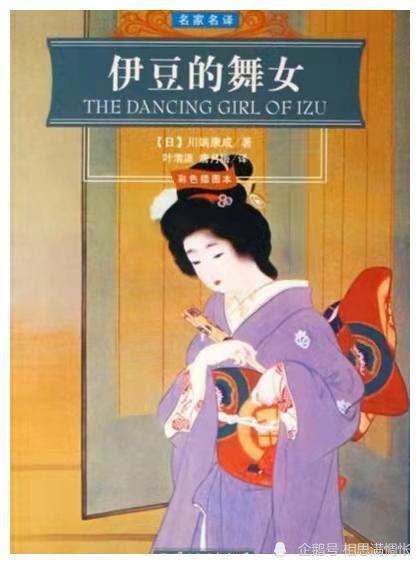
图书封面的薫子太丰腴,三口百惠的扮相刚刚好
《伊豆的舞女》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伤感,小说中的两个人自始至终没向对方倾吐爱慕,然而,什么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这种哀美的意识,只有川端康成能写出来,他天生具备哀怨的气质,这种哀怨以至于后来越来越升级。读川端康成的书,表面是一种静态,内心却波澜壮阔,他那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社会意义与美感,使人的心总是在他的暗示下游动。
《伊豆的舞女》以第一人称书写,有川端康成的自传痕迹,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我已经二十岁了,再三严格自省,自己的性格被孤儿的气质扭曲了。我忍受不了那种窒息的忧郁,才到伊豆来旅行的”,简直是川端康成在写自己。现实中的川端康成一生好旅行,心情苦闷,性格孤独,这些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底色。
“我”对薫子的思慕是哀伤的,薫子的生活也是哀伤的。为求生计,薫子常年背着鼓和鼓架,翻山越岭四处卖艺。他遇到过老婆婆的恶语,鸟店商人的歹心,小客栈女掌柜的蔑视。在一些村口,都竖着一块牌子,上写“乞丐和演出艺人禁止入村”,薫子在这种世事中卑微地存在着。薫子实际年龄才14岁,却要在生活的压力下强颜欢笑,散发着川端康成赋予的哀美情绪。
小说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有作者的影子,它有时会置放在几个人物身上,这种特质一旦出现,我们又比较了解作者的话,那么这部小说的深度就被撬起来,无论怎么解读,它的底色是不变的。
“我”的境遇本来也是不堪的,但在旧社会体制下的日本,因为“我”是男人,又读高中,于是被推到社会的较高地位上,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舞女薫子面前,“我”优越的人物,薫子叫“我”少爷。
薫子第一次与“我”搭话时,慌张地、小声地,脸色绯红。“我”与舞女们一起走在崎岖的乡间小径时,薫子总是跟在“我”身后,保持两米的距离。发现泉水时,薫子让“我”先喝,并弯腰给“我”掸去身上的尘土。下山时,薫子为“我”做手杖。“我”要出去,薫子抢先到门口,替我摆好木屐。——薫子的言行,让内心卑微的“我”感受到了优越,同时也暗示了社会的不平等。当川端康成把自己的内心交给“我”之后,他似乎得到解脱,让“我”做了他想做的事,让“我说了他想说的话,如果说写作者的写作就是发泄出口,那么寻着端倪,可以想见川端康成的“借笔泄愤”,是多么犀利。
无论川端康成,还是“我”的内心有多么卑微,有薫子这样的社会阶层垫底,川端康成或“我”就是社会精英,能够得到他人尊重的优待。而“我”对薫子初萌的情感,也许更多的是同情吧!
??[驹子]
驹子住在雪国,为了报答师傅,赚钱给师傅的儿子治病,不得不做艺妓。舞蹈艺术研究家岛村与驹子在雪国相遇,此后每年都要前往雪国,与驹子相会。他觉得雪国的驹子,每个脚趾弯处都是干净的。
在岛村第二次去雪国途中,在火车上遇到从东京返回的驹子和叶子,岛村透过车窗欣赏雪景,却看到映在窗上的美丽的叶子,不禁喜欢上她。于是,小说在岛村、驹子、叶子之间展开。
作者笔下的雪国是“物哀文学”的产物
《雪国》是川端康成的中期作品,也是代表作,里面描绘的对大自然哀愁的“物哀”之美,达到了极致,也是川端康成继对人的哀感、对世相的哀感后,将对大自然的哀感推向高峰的作品。
如果说《伊豆的舞女》是川端康成本身忧郁气质的体现,那么到了《雪国》,忧郁加重成为哀愁,有了痛苦的表现,使日本式物哀有了同情、可怜、悲伤,更高一级的哀伤。
怎能不哀伤呢?川端康成创作《雪国》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疯狂侵略战争的年代,他无能为力,只能发出一个作家的对世相的哀鸣。他把哀鸣浸透在景物中,隐藏在人物心态中,告诉自己和这个世界:人生徒劳。
这种书一般需要读2遍,第一遍过故事,第二遍思考,思考那些隐藏在景物和人物身上的细枝末节,把自然的灵性,和表达自然灵性之美的作者,掰开来,揉碎,细细地品味。
与伊豆的舞女薫子一样,驹子爱上了岛村,却因岛村的身世地位,自己卑贱的艺妓身份,爱而不能得。
驹子同样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除了放荡地伺候好男人外,别无用处。她和薫子一样,遇上“我”、岛村这种男人,还能获得一点点同情与怜悯,在大部分男人眼里,她们只是玩物而已。
驹子痴迷岛村,为了岛村,她努力读书做笔记、练琴,拉近与岛村的距离。但她的努力却被岛村看作是徒劳,岛村一个没有正当职业、靠祖辈留下的财产过悠闲慵懒日子的人,由于精神极度空虚,研究西洋舞蹈来填补,他自己做任何事都是徒劳的,怎么能相信驹子的言行不是徒劳呢?他甚至认为,连生命都是变化无常、徒劳、虚无的。
这样的岛村,又爱上了驹子身边的叶子,而叶子像一个梦境,是岛村抓不住的。——驹子抓不住岛村,岛村抓不住叶子,万事万物都是虚无的。
在描写叶子在火灾中丧生时,川端康成写道:僵直的身体从空中落下来,显得很柔软,但那姿势,像木偶一样没有挣扎,没有生命,无拘无束,似乎超乎生死之外。仔细琢磨,会发现川端康成对死的描写异常冷静,好像死是幸福的终点,人死后与自然界的万物一样,虚无、干净,成为自然界的一分子。
川端康成一生跟随着年龄以及心态写作,年轻时写《伊豆的舞女》的初恋萌发,中年时写《雪国》《美丽与哀愁》的男性婚外,后期写了一些老人的变态情爱心理,于是作品屡屡被认定是他的一生经历。
??[音子]
怎么能不这样想呢?
《美丽与哀愁》中的作家大木,我一度落入川端康成的圈套,以为大木就是他,他就是大木。他甚至交待的一个“日子好过的”点,就是因一本小说出名,家里有了钱,生活发生的改观,妻子不再忧愁。与他的生活轨迹多么相像。
而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描写大木那样一个人时,居然就像讲一个新闻事件,什么就是什么,不做评价,把读者记得在读的过程中,与他对话,给他往出加“大木的心理活动”“大木想干什么”“大木还想二次伤害吗”,等等,这样一些语句。甚至我读书的时候,一个人在心里说话,和读《罪与罚》是一种状态。
阅读时间最长的一部中篇,思考太多,行进太慢
这又是川端康成的圈套,你去评价了,你就上当了。他就是让读者依据自己的思想,去评价,去不满,甚至吐口水。
《美丽与哀愁》中的音子,少女时期遇到作家大木,怀孕,遭抛弃。她后来坚强地活下来,成长为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大木则把音子的事写出来,一举成名,改观了生活境遇。
故事从若干年后开始,插入回忆。音子的女弟子庆子,想要给师傅报仇,故意接近大木。在受到大木的妻子文子的阻拦后,转向大木的儿子太一郎。丈夫与庆子暧昧,儿子与庆子私会,文子陷入痛苦之中。
小说最后以太一郎尸骨难寻结束,大木受到了良心的鞭挞,庆子却也差点身亡。——在音子的时代,男人是天,是世界的主宰,为所欲为,即使让少女怀孕,即使把自己的龌龊行为写成小说,仍然不是大罪过,仍然可以光鲜地生活。若不是音子隐忍地活下来,成为名画家,收了庆子那样一个新时代的女弟子,音子的噩梦,永远只是大木起家资本的笑话,似乎作家大木体验了生活,把体验的生活写下来,出了名,就这么简单。
音子、庆子和文子,三个女人都有着美丽的外貌,却都成了爱情的牺牲品,表面上看,大木是罪魁祸首,但从本质上来看,日本旧制度下的男权礼教才是阉割女性幸福的刽子手。
景物、建筑描写,仍然是川端康成惯用的笔法,他喜欢把人物放在景物后面面,由景物带出人物。如果了解他的笔法,看几行景物描写,就知道接下来出场的人物是一种什么状态,忧伤的、明艳的,或不思不想的,那景物也随了人性,景物哀着人物的哀,痛着人物的痛,大师之“大”就在于此。
看翻译作品,不得不佩服翻译家们,我认为翻译家是高于作家的作家,他们把异域的语言文字,通过自己的理解翻译成中文,那些精彩妙句,有时候真是翻译家的发挥。可以说,翻译家成就了外国作家在中国的名气。
我们即将开始解读川端康成的《美丽与哀愁》,是与另一部中篇《蒲公英》合集的,《蒲公英》让我们见识了川端康成写对话的魔力,对写小说或研究小说的人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