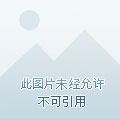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要学有所成,三十岁时能够出人头地,四十岁时对事情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五十岁时懂得了天赋予我的责任,六十岁时能够尊重和听取他人的一切意见,七十岁时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不会把事情做错。”
解读
孔子回顾总结了自己一生中发展进步的情况,评价了自己在一些年龄段上所达到的做人的标志性层级。
面对学习,人们会处于种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厌学,一种是好学,一种是对学问本体有了强烈的追求欲,立志要攀登学问的高峰,这就是“志于学”的境界。“志于学”的人会成为学问的承担者和创造者,是在为人类的历史、现实、未来负责。孔子后来能成为圣人,就是能够较早地“志于学”的缘故。
孔子在别人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就进入了“志于学”的境界,他自己谈过一个最早的原因。《论语·子罕》:“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9.6)看来是由于贫贱所迫,为了改变自己的被动现状而努力学习的结果。
所谓“立”,是学习有成的标志,就是在社会上能树起个人架子来了。这里的“立”,不是指钱财方面的富和权势方面的贵,而指的是学问方面的“富”和见识方面的“贵”。在这些方面,成为天下首富首贵的是圣人,实现了大富大贵的是贤人,达到了温饱或小康状态的可以算是能“立”起来的常人。
所谓“立”,就是超出一般,不仅学问和见识是成熟的,品德修养方面也是高尚的。能“立”起来就是一种成功。
“立”起来的还往往只是个架子,有待于充实和丰满。孔子自认为在四十岁时达到了“不惑”的境界。所谓不惑,就是对人对事都能看得清楚,理解得透彻,既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又可以从微观上解析,好像没有什么自己所不能理解和判断的问题了。
人的见识不可能无限发展,会有一个相对的极点。“不惑”说的是见识层次已经到位,这是一个“终点站”,是个人智力发展的最后一座里程碑。
“天命”一词在古代有多种词义,孔子所知的“天命”指“天的意旨和安排”,这种安排指天对世间一切事情的安排,当然也包括对孔子个人的意旨和安排。
古人认为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儒家主张积极地探讨天意的内容和规律,主动承担起天所赋予的任务,自觉地为天当一个冲锋陷阵的马前卒。
古人心目中的天的形象很神秘,但天的意志却很清楚,就是惩恶扬善,让人们规规矩矩地做一个好人。所谓天意其实就是人意,就是社会公理。人的弃恶从善的主张贴上了天的标签,可以使人们掂量自己的行为,对天的权威有所顾忌。
在天所操控的棋盘上,人们有其层级的区别,有的是车,有的是马,有的只是卒。自己在人间善与恶的对弈中能承担什么样的任务,该做出什么样的成绩,能换来什么样的奖赏(最好的奖赏就是当上天的儿子),对于这些问题,参与对弈的人们未必都会有自觉而准确的判断分析。
孔子是怎么知道“天命”的?如果他说是天托梦告诉他的,或者是他夜观天象而看出来的,人们就可以一笑置之了。从《论语》此处语境的逻辑来看,孔子叙述的是自己逐渐进步的过程,从“志于学”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每走一步都需要付出努力,都是自身境界的一次升华,显然“知天命”也是人生奋斗成果的一个标志,从道理上讲也是人人都可能达到的一个成长高度。孔子在“不惑”之后继续努力着,十年之间又大有长进,他的人生目标在水涨船高,他的理想蓝图在不停地弃旧图新。其结果不言而喻:圣人的桂冠已经向他飘来。圣人的社会责任是经邦济世,孔子给自己设定的社会责任也是经邦济世。按照当时的观念,圣人就是天的使者,就是天意的化身,他所担负的就是天的使命,这也许就是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的事实基础。所谓知天命,也就是认清了自己最终的社会责任和奋斗目标。孔子是有神论者,是不可能不将这种社会责任和奋斗目标理解为“天命”的。
面对一些不合理的逆耳的话,有的人会很气愤,对发言人极其反感;有的人会觉得可以理解和包容,并且对发言人感到遗憾和同情。这两种态度,反映出来的是人的气度修养的差异。《论语·子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19.3)子张要求对人来者不拒,其原则是“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有了这样的君子气度,就可以做到“耳顺”。凡是常人所认为不合理的话,君子都能够理解对方说这些话的事实基础,能够谅解和包容这些话对自己的冲击,能够同情和遗憾对方持这些见解的不幸,甚至想到这些不合理意见对自己的种种有益的启示,想到自己对人家所负有的责任。君子对于他人的任何意见都是欢迎的,不会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感觉逆耳。孔子在六十岁才进入了这一境界,可见磨炼出这样的气度是何等不易!
人学习是为了知道是非标准,就普遍的是非标准而言,知道它们并不难,要想都做到它们可就不容易了。将是非标准完全运用于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再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与行不一致的情况发生,这是孔子到七十岁时才达到的境界。
《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11.22)强调遇事要咨询老师和父兄的意见,不主张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也就是不主张不成熟的人们“从心所欲”,怕的是把事情办错,不符合规矩。怎么想的就怎么做了,不必再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斟酌推敲,不必再咨询有经验的人的看法,做出来的结果肯定都能符合是非标准,这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这是一种学与行完全一致的表现,是做人境界的最后的升华。
孔子的一生是不断学习而进步的一生,他是在做人方面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典范,这一境界是在其生命的尽头才最终实现的。
▼点击名片 标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