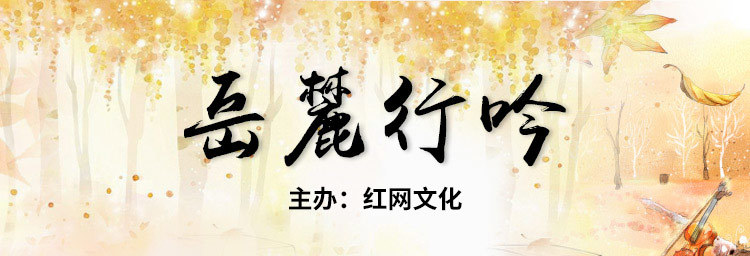
新创大型现代花鼓戏《山灯》舞台剧照。
“山灯”挂屋檐,曾照“燕”归来:深情回顾扶贫书记的生命绝唱
文/陈善君
新创大型现代花鼓戏《山灯》,以人物追忆为主线,通过《山灯》《山花》《山歌》《山雨》《山果》《山魂》等6幕,主要讲述6个并列的故事,再加上《序幕》和《尾声》的歌咏叙说,全面而深情地再现了炎陵县委原书记黄诗燕一生中最后9年的扶贫岁月,生动而真实地表现了黄诗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刻而艺术地展现了他最终用生命兑现承诺,成为“扎根扶贫一线,鞠躬尽瘁”的时代楷模、成为新时代县委书记好榜样的光辉形象。花鼓戏《山灯》为人民的好书记——黄诗燕树碑立传,为炎陵县广大人民群众感恩立言,为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塑像抒怀。
《山灯》由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创排,它较好地运用了花鼓戏剧的传统形式,但在一些方面、一定程度上又有出新,加入了一些现代的、时尚的审美形式或元素,并使二者尽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师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既让人觉得花鼓味道满满,又让人产生淡淡的新奇感、新鲜感,从而让人觉着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拿捏到位。《山灯》熔时代楷模写照与艺术传统出新为一炉,唱响了一曲新时代扶贫英雄的壮歌。
一是以喜写悲更恸人。黄诗燕扶贫路上因劳累过度突然离世,令多少人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然而最伤心的莫过于他的夫人彭建兰了。第6幕《山魂》主要写她对丈夫的思念成河,无以释怀。对此,剧中主要安排两段故事来表现。一段是过去,是他们曾经那么浪漫的“爱情的故事”;一段是未来,是他们无限憧憬着的“河边上漫步”。他们或相携而舞,或相搀而行,都那么的美好惬意,可是诗燕书记的突然离世,他们的阴阳两隔,既无情地掐灭了他们憧憬着的未来,也可恶地掐断了他们曾经的过去。当所有的“美好”落幕,彭建兰情何以堪?当彭建兰的身影暗去,她承受的“痛”留给了观众,恐怕还久久不能散去。王夫之《姜斋诗话》有言,“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由此可见《山灯》编剧“以喜写悲,益增其哀”的手法运用与用心所在。在如是花鼓声韵中,响起最美扶贫书记黄诗燕的生命绝唱,委实撼人心魄。
二是亦庄亦谐贵得体。花鼓戏源自民间,经年来,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审美旨趣,以表现喜剧题材或者喜剧元素见长。而《山灯》题材完全是个生命悲剧故事,二者无疑是有些悖离的。一旦处理不好,要么就会不经意间调侃英雄,要么就会搞得不像个花鼓戏,失去花鼓戏的美学韵味。可是编导却成功逃离这个陷阱,主要有三:第一,努力发掘主角身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生活之轻写生命之重。生活中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的主角黄诗燕都以他人生的大智慧轻松加以化解。比如说他在跟特困户交心的时候说到,“您不知道吧?我这个县委书记,其实比您这个特困户主还困难呢。”多么风趣幽默而又鞭辟入里,一句话就把他这个最美扶贫书记的担当与无奈完全展示出来了,同时也给对方最好地暖心;第二,通过不同的场景处理,来安排何处该“庄”、何处该“谐”、何处“亦庄亦谐”。与小刘、盘花花相处,可以安排主人公随时幽他们一默,与雷主任、其他贫困户就不能轻易安排幽默了,当然除非像大家要签约、特困户有安排这样非常开心的特定时候,也是可以插点“诙谐”的。剧中跟张爷、兰杜鹃亦庄亦谐的相处安排,非常符合表现人物个性需要和切合时间地点要求;第三,通过创新意识、手法、形式,来缝合二者的背离。比如,剧的“过场”部分,借鉴歌剧手法,安排的歌咏人员,她们举止肃穆,服饰整洁大方,声调清新亮丽,她或者她们的演唱或配合剧情发展需要或评述人物得失或唱出角色心声,引导观众更加深入观察、认识、了解、崇敬主角的崇高精神,以引起更多的情感共鸣和感染力。第5幕《山果》的歌舞非常活泼、欢乐、煽情,其实是已经超越了传统戏剧歌舞的范畴,更多民族歌舞的元素,不过,其和花鼓戏擅长表现喜剧题材、喜剧色彩一点也不违和,显得讨喜而无损其美学特质,甚至可匡传统戏剧文戏沉闷之弊。
总之,《山灯》全剧的庄谐交织、亦庄亦谐,既雅俗共赏,又使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得以有机结合,全剧风貌合适得体,为花鼓戏某些方面的传承发展作了可贵的艺术探索。
三是虚实结合铸丰碑。《山灯》在继承传统花鼓叙事的基础上,更加着重注入现代叙事因子,借鉴一些现代叙事手法,融合一些其他艺术门类形式,写实少了,虚写留白多了,叙述少了、抒情多了。黄书记为炎陵引进黄桃,走出一条产业扶贫的路子,可以说废过多少寝忘过多少食、呕过多少心沥过多少血,有多少事情可写、有多少文章可做?可是,剧中只用“山果”一幕,并且是一场舞,用他的一句广告词“炎陵黄桃,桃醉天下”,就基本上能让观众感受到了。黄书记的文件袋子,装的是全县贫困村、贫困户的资料,装的是全县脱贫攻坚的明细账本,更装的是他对全县贫困人员的牵挂。黄书记随身带着的凳子,带的可是对全县贫困人民的尊重和与人民平起平坐的姿态,既方便自己、又方便群众、还方便工作。黄书记的手机连着两个世界,一头是单位、一头是家庭。在某些人看来,书记是凳子;在某些人看来,书记是袋子;在某些人看来,书记是果子(黄桃);在其夫人看来,书记是机(手机)子;但在更多人看来,书记是灯(山灯)子,这正如《山灯》出品人、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主任肖鸿斌所说,黄诗燕在世时,是照亮炎陵山区人民走向致富之路的灯;虽然他现在不在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就像罗霄山上一盏永不熄灭的“山灯”,照亮后人前进的路。这“五子”足以堆砌铸就一座丰碑,让黄诗燕书记的光辉形象永久矗立在湖南花鼓戏剧舞台上。其实,利用道具、器物、标志物来作线索、结构情节、点明主题或是象征叙事,在各种现代戏剧手法中都比较常用。但是像《山灯》用得这么普遍、娴熟、老到、恰到好处,还是不多见的。当然,其实花鼓戏的源头也是注重抒情和歌舞表演的,从这个层面讲,《山灯》既是回归又是创新,但不是在回归道路上的创新,而是在一边走向回归、一边走向创新。
《山灯》已在株洲首次公演,观众反响良好,认为其真实、感人,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地方性、观赏性俱备的一部好戏。在我看来,该剧在以喜写悲、亦庄亦谐、虚实结合上尚未做到极致,还有提升空间,希望该剧能进一步修改打磨提高,走得更远,影响力更大,让黄诗燕的先进事迹传播得更广,产生作用更大,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新时代花鼓戏剧经典作品。
陈善君,男,汉族,1971年8月出生,湖南衡阳人,中共党员,文艺学博士,文学编辑。1994年6月参加工作。现任湖南省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在《中国艺术报》《文艺报》《当代文坛》《湖湘论坛》《湖南日报》《理论与创作》等各级权威报刊发表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文章近50篇。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