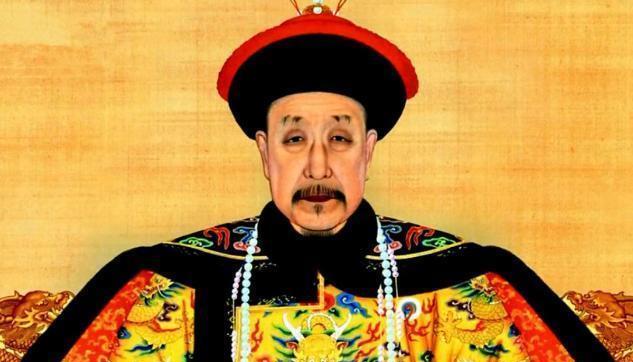
顺治五年十月(公元1648年),洪承畴在南京干了五年江南总督之后回到北京,开始在清政府中枢工作。第二年,多尔衮打算编写皇太极史稿,也就是说,他准备给清朝已故皇帝皇太极著书立传。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入关六年时间,基本荡平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反清势力,只剩下南明的永历小朝廷在云南那个小地方苟延残喘,不足为患。现在可以组织人力,给先皇写个人传记了,这也是教化万民、垂范春秋的一件大事。
皇太极是多尔衮的哥哥,也是顺治皇帝的父亲。作为顺治皇帝的亲叔叔,以皇父摄政王身份监国的多尔衮,意识到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下去。皇帝已经长大,即将亲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有了自己独立执政能力,有了自己的思想,在很多事情上也有了自己的政见,显得越来越难以驾驭,搞的叔侄两人的关系开始慢慢有点紧张。编修皇太极史稿,既可以对先皇一生的丰功伟业有个交代,同时也可以缓和自己和皇帝侄儿之间的紧张关系,委实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编写皇太极史稿,需要有一批德高望重的大臣担当此项工作,具体人选已经初步确定,他们就是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冯铨、宁完我、宋权以及从江南回来不久的洪承畴。这七个人虽说都是来自明朝的降臣,但他们自身具备修撰史稿的能力,不仅学识渊博、博古通今,而且都身兼翰林大学士头衔,且为官清正廉洁,对大清忠心耿耿,是难得的治国能手。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是皇太极在世时,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大明重臣,在皇太极东征西讨的年代,这些人都伴随在太宗皇帝的身边,亲眼目睹过他治国理政的风采,让他们编撰皇太极史稿,是最合适的人选。
顺治皇帝对此事高度重视,为编写《太宗文皇帝史稿》一事特别写了一道敕书,这样写道:“兹者恭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择于顺治六年正月初八日开馆。朕为帝王抚宇膺图,绥猷建极,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以觐扬于后世,诚要务也。我太宗文皇帝应天顺人,安内攘外,在位十有七年。惟文德之昭,武功之盛,以及号令赏罚,典谟训诰,皆国家之大经大法。尔等稽核记注,编纂修辑,尚其夙夜勤恪,去据精详,毋浮夸以失实,毋偏执以废公,毋疏忽以致阙遗,毋怠玩以淹岁月。敬成一代之令典,永作万年之成宪,各殚乃心,以副朕义。钦此。”
顺治皇帝的这篇敕书,可以说是一篇简明扼要,又非常有力度的雄文,既有重点,又划出了高度,“凡一代之兴,必垂一代之史,以觐扬于后世,诚要务也。”也就是说,别看这是个写字的活,但它事关我们大清后世的国运,是要务之中的要务,是国家振兴的大法。同时,顺治皇帝还给参与编撰工作的领导小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你们每个人要“毋浮夸以失实,毋偏执以废公,毋疏忽以致阙遗,毋怠玩以淹岁月。”认真编撰,让它成为一部护佑大清万世基业的柱石,千万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可见,顺治帝对这件事多么上心。
编撰工作刚一开始,多尔衮就在百忙之中多次召见这些参与编撰工作的汉臣,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求参与编撰的大臣们都要按照他自己的要求去做。这时的多尔衮是皇父摄政王,总揽满清朝政,整个大清政府里,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多时候,他的权力甚至都要超过顺治皇帝,虽无皇帝之名,但却有皇帝之权,生杀掠夺,基本上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是一个位高权重的权臣。绝大多数时候,在顺治尚未亲政之时,这些大臣都以多尔衮马首是瞻,对他的话不敢有些许忤逆。好在多尔衮雄才大略、卓越超凡,一心一意为大清江山社稷废寝忘食的工作。在他的坚持下,大清不但入关占领中原,而且逐渐开创出一个气象万千的新局面,显示了多尔衮作为一个能臣的光辉一面。所以,大家相处起来也颇为得心应手,非常愉快。
但是,多尔衮在修撰《太宗文皇帝史稿》一事上还是有私心的,为什么有私心呢?他肯定不愿意把自己那些不上台面的事情记述在这部史稿里,让后人指着脊背骂他。另外,还有一件不能不提的往事。多尔衮的母亲叫阿巴亥,是乌喇贝勒慢泰的女儿,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十一月刚满十二岁时嫁给了努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侧福晋。后来因为老大富察氏和代善之间的暧昧关系曝光,努尔哈赤一怒之下便将这个给他带绿帽子的富察氏给休了。这样一来,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夫人。而且因为努尔哈赤要比阿巴亥大整整三十一岁,属于典型的老夫少妻。加之努尔哈赤常年征战四方,两个人聚少离多,这就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伏笔。
公元1626年正月,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大军攻打明朝,不成想遇到他一生中的克星袁崇焕,被袁崇焕打得浑身是伤,不得不撤兵回师。没有几天,就因为身上毒疮发作,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此时年仅35岁的皇太极抓住时机,带领几个年龄稍大的贝勒闯入阿巴亥的后宫,向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传达“帝遗言”,强迫阿巴亥遵从努尔哈赤的遗命殉葬。此时的阿巴亥只有36岁,正是风华绝伦的年龄,多尔衮也只有14岁。她知道皇太极所传达的“遗命”是假的,而且出对自己的不公处理以及多三个孩子的牵挂,她百般推诿,希望事情能有转机,但皇太极出于政治目的,最终逼迫阿巴亥自尽。皇太极上台之后,认为阿巴亥不愿遵从父皇“遗名”,不愿意殉葬,是一种不守祖制和妇道的表现,所以多有指责。
这件往事,对于此时身兼大清国摄政王的多尔衮来说,他是不愿意让自己的母亲在史书上落下诟病,让后人责难。如果他不是摄政王,可能就无权干涉此事。但现在他有这个权利,就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被人在史书里写上污点,做儿子的怎么能对母亲这么不尽孝道呢!于是,他把编撰《太宗文皇帝史稿》的总编辑刚林、范文程、祁充格这三个叫到自己办公室,如此这番的交代了一通,中心意思就是让这三个人把自己母亲阿巴亥不愿殉葬这各事从太宗史稿这本书里删掉,另外,还要把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情重新修订撰写。
范文程、刚林和祁充格都是很早就进入大清阵营的汉族人,可以说他们在帮助满清攻打自己的母国明朝这件事情上,是不遗余力的激进。皇太极时期,他们就是满清政府倚重的汉臣,到了多尔衮时期,他们更是多尔衮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已经同多尔衮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同时也相信大清朝在多尔衮的领导下,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些人的政治嗅觉要比狗鼻子还灵。当时的多尔衮才才37岁,年富力强,正是人生最有激情的年级。如果按照努尔哈赤的临终时的68岁算,多尔衮还可以继续执政31年,即使今后福福临亲政,多尔衮也是满清至高无上的权臣。
所以,即使是瞎子,也能看到多尔衮的政治生命力有多强盛。因此,对于多尔衮关于皇太极史稿的编著所提出来的几点意见,范文程、刚林和祁充格是不遗余力的增删。什么叫增删呢?就是把多尔衮点名提出要删除的内容,要尽快从这本太宗实录里删除掉,把多尔衮要求增加的内容,尽快完好无缺地添加到这本实录里。为了让多尔衮满意,他们还对满清入关前在盛京时期所录的一些皇太极起居史册内容进行增删,对多尔衮做的一些影响不好的事情不是不写,就是黑白颠倒,把坏事写成好事,把小事写成大事,在太宗实录里写了不少对多尔衮歌功颂德的事情。这种做法完全把顺治皇帝当初划给他们的编撰原则给彻底颠覆了,不但让太宗实录多了一些面目全非的感觉,而且也放弃了编撰者以公谋私的原则。这几个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还是迫于多尔衮的压力,也就是说,有了多尔衮的支持,他们这样做了,也没有人敢说他们什么。但事情往往会事与愿违,出来混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公元1650年12月31日,注定多尔衮把生命留了在旧历,这一天,他死在了行猎途中,终年三十九岁。俗话说,人走茶凉,一朝身死名将枯。随着多尔衮的死去,一场满清贵族之间的政治较量也重新燃起火焰,由于多尔衮已死,所有追随多尔衮的大臣都被多尔衮的政敌济尔哈朗列在清除打击之列。《太宗文皇帝史稿》的编撰工作也随之停止,参与编撰的七个汉族大臣革职的革职,下狱的下狱。他们的罪名就是删改太宗实录,增减太宗史册。被多尔衮认定为心腹大臣的领衔文大臣之首刚林被处死,生前他因受多尔衮的信任而荣宠天下。刚林廉洁自律、才能卓著,但就是因为被多尔衮信任而被反对派处死。他们要彻底消除多尔衮的流毒。
另外一个被处死的是祁充格,另外还有冯铨、宁完我、宋权等人也因为受到多尔衮的宠信而被清除出政府。范文程因为多尔衮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他疏远并充满敌意,而被反对派保留下来。在《太宗文皇帝史稿》一案中最大的热门人物就是洪承畴了,他在这次清剿多尔衮流毒的政治运动中不但毫发未损,而且获益多多,成功地将自己置身事外而坐收渔利。
为什么洪承畴能独善其身呢?首先,得益于洪承畴自己的为官之道。作为经历过大明时期官场激烈斗争的洪承畴,早就练就自己一套官场生存哲学,就是千万不能把自己搅进党争的漩涡中去。洪承畴虽然受到多尔衮的器重,主要是工作上的关系,私下里两人并无太多的交集,所以就谈不上有什么个人感情在里面,更谈不上有结党的事情了。在这方面,洪承畴一直小心翼翼,有自己的底线和防火墙。
其次,大清进入关内,在北京定都之后,洪承畴就被外放为江南总督,他整整五年的时间都在南京领导对江南反清势力的剿灭,工作上和多尔衮并不太多交集。而且他在南京期间,工作能力很强,工作业绩也很突出,深受上级部门及周围同志的赞许。可以说,为大清平定江南地区,他付出了很大心血和努力。这一点,多尔衮的政敌济尔哈朗也心里明白,顺治皇帝更是心知肚明。
此外,洪承畴刚回到北京工作不久,就被朝廷下令进入《太宗文皇帝史稿》的编撰小组,他的工作时间短,而且在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也是独来独往,没有攀附任何势力,政治上还是很清明的,这样的人怎么能杀掉或者废弃呢!不但不能杀,而且还要继续用。所以顺治皇帝还是比较信任洪承畴。
那么,《太宗文皇帝史稿》这件事情最后要不要继续编写下去呢?当然需要,毕竟顺治皇帝把它看的是大清朝继往开来、春秋万代的大事。顺治九年正月,《太宗文皇帝史稿》的编撰工作重新启动,顺治皇帝又命令洪承畴、希福等人为编撰总裁,组织了一个26人的写作班子,而且又亲笔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雄文,让这些文人们好好编撰这部承前启后的大经大法,敕书内容和第一次写的意思八九不离十,也非常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