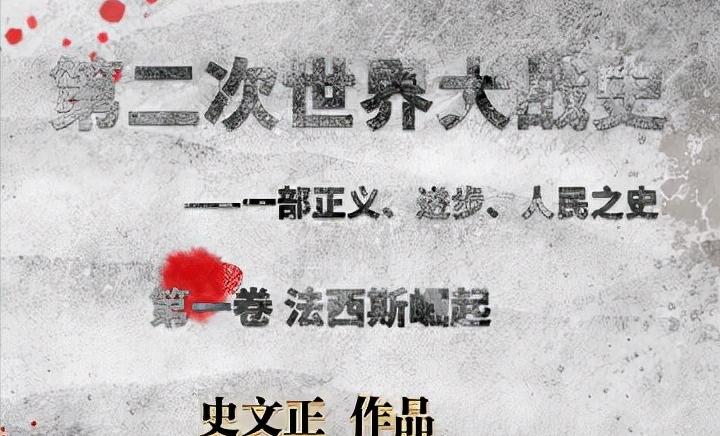介绍了法西斯的反动,介绍了人民的反抗,现在我们要转到另一派力量——“现状维持”派。之前我们对它已多有涉及,这个“现状维持”派显然不维持现状,任由法西斯破坏而不加以制止,直到最后还走上了一条“绥靖”法西斯的道路,尽管这个曾经不正义的“现状”开始显示出公道正义的一面。苏联著作家认为,“现状维持”派这些做法是有其深远的战略考虑的。“现状维持”派之所以这样做,意在转变法西斯的侵略方向,把它引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苏联社会主义,从而使帝国主义所面临的矛盾获得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解决。
“现状维持”派确有这方面的考虑。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不能混乱下去,否则极有可能落入共产主义之手,那对“现状维持”派来说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稳定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让它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成为西方反对东方的桥头堡。德国帝国主义在其重新崛起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这一点,获得了“现状维持”派的谅解。
然而法西斯的崛起改变了情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东方的“威胁”那是遥不可及的“远虑”,而法西斯的威胁却在一天天地成为近忧。那么“现状维持”派对此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我们知道,在一战时,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现状维持”派毫不犹疑地针锋相对,决不妥协,于是一战变成了两支力量相互进攻的“遭遇战”。然而此时它们却不想这样做了,至少英国帝国主义不想这样做了,法国帝国主义实力不济,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跟着英国帝国主义走了。美国帝国主义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躲在孤立主义的巢穴中静观其变才是最佳的选择。
下面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现状维持派”的三个“代表人物”
——英法美帝国主义,看看这些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们(至少二十年代是主导者)灵魂深处的东西,看看它们是本着怎样的指导思想履行“维持现状”职责——默许纵容法西斯破坏现状。先从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说起。
曾经称雄世界近两百年的大英帝国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标杆性“人物”,它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启了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发展的工业化时代,它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列强,四处掠夺殖民地,建立起“日不落”殖民帝国。不过,随着帝国主义体系内后起之秀不断崛起,群雄并立局面出现,大英帝国在这一体系内的相对实力不断下降,它开始从巅峰状态下落,它的争夺开始出现力不从心。而帝国主义体系也和任何一个剥削阶级体系一样,其以争夺和剥削为根基的发展终将是有限的,一旦争夺达到极限,地位得到巩固,它就会失去奋斗创业的动力,它就只想着剥削和坐享其成,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者地位万世不易。
看来帝国主义只有争夺和保有争夺成果两种状态,当过了争夺扩张那样一个“艰苦创业”的年代,帝国主义就进入了一个保有争夺成果这样一个安享尊荣的状态。如果说“苦大仇深”派仍处在一个“艰苦创业”的争夺年代,那么大英帝国就开始向后一个状态转化。它风光渐逝,辉煌难继,日益明显地向我们展现出“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前景,它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衰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让帝国主义遭受重大打击的战争中,大英帝国击败了它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德意志帝国,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殖民势力进一步扩充,但是它终将只是赢得了一个惨胜,一战后的它继续其衰落,继续其“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演变历程。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英帝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是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体系内的既得利益者,依然拥有庞大的殖民地可供其剥削和利用,依然拥有庞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和强大的国际金融实力,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掌控海洋这个世界交通命脉,因此,毫无疑问,它的综合实力依然位居帝国主义前列。但是,正如那“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的贾府一样,它虽“葱蔚洇润之气”依旧,“峥嵘轩峻”之势不减,然“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二十年代,英国的经济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一样经历过危机、经历过衰退,经历过萧条,然而不同的是,唯独没有经历繁荣。即使帝国主义世界最繁荣的二十年代下半期,英国经济也没有出现繁荣迹象,依然在萧条和停滞中徘徊着。于是大英帝国的相对实力继续下降,庞大的帝国愈加虚弱不堪。然而,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们也许不需要这样的繁荣,也许不敢奢望这样的繁荣,他们应对萧条和停滞的对策就是恢复一战前消极无为、自由放任的那一套东西:通货紧缩、金本位、自由贸易外加伦敦的国际金融地位。这些曾经是大英帝国称雄世界的武器,此时却成了它无可奈何的选择。至于奋起其强大的意志,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摒弃“安富尊荣”,积极“运筹谋画”,改变现状,再创辉煌,则不在大英帝国统治者的选项内。
在国内统治方面,一战后,受十月革命和战争后遗症的影响,大英帝国也出现了一些动荡,人民要求改变现状、要求革命进步、反对干涉苏俄的声音不断出现,1926年还爆发了反对资本家加重剥削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当然,尽管有这些动荡,尽管经济长期停滞,尽管长年累月存在百万失业大军,大英帝国依然可以把国内局势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上,这和它之外的帝国主义世界持续动荡不安形成鲜明对照。
作为帝国主义体系内的既得利益者,作为一个发展了数百年、拥有深厚财富根基、拥有庞大殖民地的老牌帝国,大英帝国完全有实力向人民群众作出些许让步,改善一下人民生活,消弭人民的反抗,维持国内统治的稳定。与动荡不定的“苦大仇深”派相比,大英帝国无疑是富裕的、文明的、安宁的、祥和的。当然它的富裕文明无疑是建立在“苦大仇深”派不富裕不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在少数民族压迫和剥削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因此,为了保住富裕文明,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它就不能不极力维持这个不正义的帝国主义统治秩序,不能不默许和纵容反动,不能不打压和遏制正义。
它的富裕文明是自私自利的,是损害公义的。而经济停滞下的富裕文明无非是帝国主义安享尊荣状态的反映,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明显特征,是帝国上下萎靡不振、缺乏进取、没有争夺之心的反映,是以其既得利益者的优裕地位将人民置于浑浑噩噩状态、消弭其进步变革之心的反映。
当然,大英帝国要想保住自己的富裕文明也绝非易事,一些忧患始终困扰着它。首先,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人民革命力量兴起是大英帝国面临的根本性威胁,对这样一支要改天换地、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力量,安享尊荣的大英帝国无疑是恨之入骨,尽管对付这支力量有些力不从心了,但大英帝国无时无刻不把它视为心腹之患。二十年代的大英帝国始终是积极的反苏派,它参加了对俄国革命的干涉,失败后又不时掀起反苏浪潮,然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反动浪潮中岿然不动、兴旺发达,大英帝国只好对之暂取合作之态,尽管很勉强。
而一战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殖民地人民斗争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帝高潮,拥有庞大殖民地的大英帝国无疑是首当其冲。土耳其的民族独立战争、伊朗人民反对奴役性的《英伊协定》的斗争、埃及华脱夫党运动和反英起义、伊拉克人民的反英起义、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和独立斗争、印度和缅甸人民的反英斗争,从埃及到中东,到伊朗,到南亚大陆,反对英帝殖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追求民族独立的要求愈加强烈,纲领愈加明确,斗争愈加坚决、愈加有组织,对大英帝国统治秩序的冲击愈加猛烈。面对被压迫人民日益强烈的反抗,大英帝国同样是深感力不从心,当然它绝不会轻易地向人民、向历史作出让步,它不断改变策略,给予一些让步,以软硬皆施对付这一革命大潮,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千方百计地保住殖民地这条已深深渗透到其机体中的生命线。
好了,在一般性地介绍了大英帝国的形象之后,我们有必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即大英帝国面临的另一忧患——法西斯派及其前身“苦大仇深”派的崛起对大英帝国的威胁,看看大英帝国为何不准备按照一战的激烈对抗方式消除这一威胁。其实,我们展示了二十年代大英帝国的形象、思想和灵魂后,它不这样做的原因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对昔日霸主大英帝国来说,既然它极力打压人民革命力量,极力维护反动的现状,既然它让人民浑浑噩噩,安于现状,既然它不思进取,让自己虚弱不堪,那它就无力与强大的反动邪恶力量对抗。而对帝国主义的安享尊荣者来说,既然“保住现有的”才是其首要战略目的,既然它无需进取,无须争夺,也就失去了与强者对抗的必要。
丘吉尔向往的“不列颠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此时的大英帝国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时代了。记得1936年丘吉尔曾发表过一篇算得上是全面回顾那个时代的演讲。丘吉尔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大英帝国总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它“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然而此时的大英帝国显然不想走这条“较艰难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开始由过去的反动转向此时的正义,而是选择了一条阻力较小的道路。它不再与弱者联合,而是与强者“合作”。
在帝国主义世界,没有回报的付出是不存在的,公与私是矛盾的,为了保全私,就不能不损害公,为了个人利益,就不能不宰割集体利益。对于一个安享尊荣者来说,现状就是一切,眼前利益就是全部,它已心满意足,不需回报,无用付出,公义在它眼里价值为零,集体利益可以任意出卖。那条曾经让它称霸于世、此时让它舍生取义的“较艰难的道路”,它是绝不会走的,得不偿失的投资它绝不会干的。息事宁人,置身事外,不得罪强者,与之相安无事,才是安享尊荣者的处世之道。即使这个强者是潜在的,还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对它的遏制也是要伤神劳心,付出代价。强者的强大是不可抗拒的,与其遏制,不如顺应。当然强者一旦强大起来,就会危及安享尊荣者的安全。然而安享尊荣者决定还是不抵抗,继续与强者“合作”,以牺牲公义把强者的掠夺引向他方,满足其掠夺之欲,使之不危及自己的利益,同时还有可能利用强者这架战车获得更多利益,何乐而不为?
二十年代,尽管大英帝国在欧洲还搞出一个扶德抑法反苏,还不时争夺一下,但这已经不是它的主流了,它开始从“劳心费事”的均势战略转向“省心省事”的“合作”战略,它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强者的强大。进入三十年代,当“苦大仇深”派转化为法西斯时,它则极其顺利、极其自然地按其本性行事了。
现在我们再次把时间转到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在这场大危机中,大英帝国同样没有幸免于难。危机重创了英国经济,不过没有经历繁荣的英国经济相对于那些经历过繁荣的帝国主义经济体,其生产过剩之苦、信贷不足之痛能轻一些。且大英帝国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它依靠庞大的殖民地,依靠帝国特惠制,外加忍痛斩断金本位和自由贸易的羁绊,最终渡过了难关,经济又恢复到了往日的老样子,一切归于平庸。
当然,危机还是给大英帝国留下了几道伤痕。首先,危机后的大英帝国如同大病初愈后的迟暮之人,愈加虚弱不堪,而危机也基本上未能激起帝国执政者们的穷途思变之心,他们愈加精心呵护帝国的安享尊荣。其次,危机还是给英国带来了一些社会动荡,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倾向加强了,罢工和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冲击着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秩序。
最后,英国的法西斯运动也开始兴起,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出现了,其中最大的就是莫里斯在1932年建立的“英国法西斯同盟”。该组织的纲领和组织结构很多都是效仿德意法西斯,是德意法西斯在英国的代理人。以后我们会在许多国家看到这种代理人,他们是德意法西斯特别是德国法西斯安插在这些国家的“第五纵队”,他们的活动随德意法西斯侵略活动的加剧而日益猖獗,与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反动性的加强相适应的。当然,英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法西斯组织不可能形成什么气候,只能呆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备用库中。
下面我们着重看一下在“苦大仇深”派变成法西斯之际,大英帝国是如何按照安享尊荣者的处世之道行事的,“理论”有了,现在就要看一看具体的“实践”表现。
首先,对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大英帝国的执政者们和舆论界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担心。人们对此给予了种种解释,比如英国政府“忙于”国内事务无暇他顾,希特勒政府并没有表现出“战争倾向”,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反应迟缓”,“人民”为和平主义情绪所俘虏,首相鲍德温是一个“党务经理人”,关心国内选举更甚于对外事务,等等。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会看到一当普鲁士变成德国,马上引起了大英帝国的警觉,当俾斯麦几次想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战争”,大英帝国立刻做出强烈反应,尽管俾斯麦的战争性跟希特勒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当威廉二世上台,俾斯麦下台后,大英帝国的警觉就更高了,它的直觉准确无误地告诉它,正在崛起的德意志帝国就是它未来战争的敌人。
此时此刻,对大英帝国来说,问题关键不在于什么体制,什么人执政,不在于“人民”情绪如何,而在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指导思想变了,战略方针变了,看问题的立场也就变了。于是当我们站在安享尊荣者的立场上看待纳粹政权,它就“不那么可怕”了,甚或是一个“温和”的、可以“合作”的政权。
其次,说到与法西斯的“合作”,在大英帝国的政界、军界、商界确有那么一批人,对法西斯政权怀有一种赞许之情,希望大英帝国能与之走得更近一些,共同担起稳定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秩序的任务。同为帝国主义的一员,都有维护反动秩序的需要,这是大英帝国与法西斯可以走在一起的阶级基础。且民主的大英帝国不敢做的,独裁的法西斯却敢做,有这样一支极端反动力量为帝国主义保驾护航,大英帝国当然欣喜不已,加强与之合作“确属必要”。
不过,安享尊荣者的本性决定了这一想法只得到帝国执政者们的部分认可:大英帝国确实可以利用法西斯这架战车获得更多利益,但不能为这架战车所绑架。安享尊荣的大英帝国完全没有必要与法西斯走到同一条战壕里,只须与它相安无事即可。大英帝国需要的是自己的现状和眼前利益无虞,既没有必要进行那些“无情可怕的争夺”,更没有必要将自己置于法西斯的对立面。
当然反对与法西斯合作的人也是存在的,比如丘吉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自从德国法西斯上台后,他就不断地警告英国统治集团要警惕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要加强战备,提高英国的防御能力。然而,长达十年之久的在野状态足以说明,丘吉尔和莫里斯获得相同的待遇,只能呆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备用库中,因为他那尖锐的警告声搅了安享尊荣者的酣梦。
再次,至于三十年代上半期的大英帝国是如何处理与法西斯的关系,我们就不重复展示了,那无疑生动地诠释了安享尊荣者的处世之道。它决不得罪反动邪恶的强者,坚决避免与之对抗,它拒绝为世界和平正义付出任何代价,在苟且偷生和舍生取义之间,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在亚太,它已经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在欧洲,它为抑制法西斯多少费了点心思,不过当这一点难以实现时,它也很快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有了安享尊荣者的处世之道营造的“良好环境”,反动邪恶的强者顺利地突破了帝国主义现状的束缚,它决定要放手大干了,而安享尊荣者也决定继续其处世之道,继续损公肥私,继续苟安于世。
最后,还是那个结论:法西斯德国和大英帝国作为帝国主义世界两种截然相反状态的典型代表,前者因战争和掠夺的欲望而精力充沛,动力强劲,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不可遏制之势;后者因早已满足了这一欲望而陷入萎靡不振、缺乏激情之中,只想着眼前的安享尊荣而毫不关心未来发展之势。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帝国主义的反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