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由于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比較富庶的自然條件,加上原住民的包容性格,使本地多次成為全國性移民的主要地區、重要波及區和必然過渡帶。
1史前時期:融合南北文明
在傳說的五帝時代,部族、部落之間的戰争十分頻繁。其中“禹征三苗”的戰争最為持久,《呂氏春秋·召類篇》:“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卻苗民,更易其俗。”這一次夏人向南推進大概止于漢水流域。到了商代中葉,約武丁之時,由于國勢的強盛,為了打通通向南方特别是長江中遊的通道,曾一次次讨伐南國的荊人。祝融的後裔季連所率的部族,大概就在這一階段,從中原遷徙到包括襄陽在内的江漢地區,并留居下來。今宜城還有一個村子的名稱叫“季連村”,這就是最好的明證。史學家認為,正是以“禹征三苗”為契機,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兩大文明起源緊緊地聯合為一體,才有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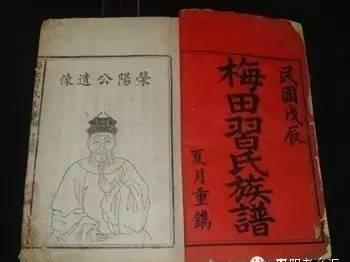
2東漢末年:人才窪地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引發了兩次大的移民,嚴重地波及了襄陽地區。一次是公元190年,董卓挾漢獻帝西遷長安,将數百萬人強行西遷;同時還有青、徐二州的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的大遷徙,這些難民逃脫了董卓的軍隊的逼遷,紛紛南下,今山東西部和河南的人口大量遷至荊州(治襄陽)一帶。第二次發生在公元192年,王允殺董卓之後,引起關中大亂,緻使數十萬難民逃離關中。其中有一部分南出秦嶺武關經南陽盆地遷入襄陽地區。
在那時的兩次南遷中,河洛與長安的大量難民,特别是有識之士,都是沖着荊襄地區的富庶和荊州牧劉表保境安民的政治環境而來的。《後漢書·劉表傳》載:關西、兖、豫學士歸者千數聚集荊州,使荊州首府襄陽替代洛陽而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據《類說》“冠蓋山”條:“漢末,嘗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兩侍中、一黃門侍郎、三尚書、六刺史,朱軒高蓋會山下,因名曰冠蓋山。”如此衆多的朝廷重臣聚集襄陽,他們的住宅“朱軒骈輝、華蓋連延”,從襄陽岘首山南到宜城上百裡路上,全是高門大戶。可以想見,從京都洛陽遷入襄陽的移民是一個多麼大的數字。
這次移民最大的特點是高素質的人才流入,使襄陽一度成為吸引全國人才的窪地。劉表是山東高平人,是以當時遷來大量的山東人。如王粲、王凱兄弟及後來定居襄陽的晉太醫王叔和,他們都是高平人。還有諸葛亮等,也是山東人。其他著名人物有:古文經學家、穎川人司馬徽和章陵人宋忠,音樂家、河南人杜夔,穎川人徐庶等,都是一代俊傑,社會精英。在劉表治荊州的近二十年間,外來襄陽寓居的移民對襄陽本土的文化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3兩晉、南北朝:“僑人”流入
西晉永嘉年間的戰亂導緻北方人口的大規模南遷,迫使西部老百姓越過秦嶺進入漢水流域,襄陽地區是其主要移入地之一。
東晉時期,由于關中地區戰亂不息,秦、雍兩地流民大量南遷至襄陽一帶。由于移民人數多過土著,朝廷不得已,在襄陽采取了僑置州、郡、縣的管理措施(所謂僑置州、郡、縣,是指東晉統治者為了控制僑人,即南遷人口,也為了維護僑姓士族的利益,在僑人比較集中的流入地,暫時借地置僑人原籍的州、郡、縣行政機構,并仍用舊名,叫僑州、僑郡、僑縣,簡稱“僑置”、“僑立”)。直到南朝宋時,今襄樊地區分屬13郡,35縣,其中僑郡9,僑縣18,僑置郡縣數超過土著郡縣。來自西北的移民,已經遠遠比當地人多。而且這次的移民後來大多定居下來,是以可以說,今天不少襄陽人的祖籍都屬西北的陝西甘肅山西等地區。
再從移民執行個體看,襄陽的康姓,來自西北。漢朝時期,居住于大宛西北,大月氏之北,西晉時從隴西遷入西北。南朝宋永初年間(公元420年-422年),康穆率鄉族三千餘家遷至襄陽岘山之南(今歐廟尚有康灣村),朝廷為之設華山郡(僑置宜城境内)。康穆之子元隆、元撫先後被移民推選為華山太守。南朝齊永元元年,康絢起兵響應蕭衍(南齊治襄陽的雍州刺史,從襄陽起兵反齊,建梁朝的梁武帝)時,可以出動“敢勇三千,私馬二百五十匹”。可見康氏在移入襄陽以後的繁衍能力是很旺的。筆者曾詢及康氏後裔,他們亦稱其祖上本為西域之人。杜甫的祖先杜氏家族的南遷襄陽,也發生在這一時期。杜氏本世居京兆杜陵,杜甫的十一世祖杜遜于東晉初随晉室南渡遷至襄陽定居。這也是杜甫及其祖父杜審言都稱自己為襄陽人的原因。
兩晉南北朝期間的大移民,曆時一百多年,若計其餘波,則更長達近300年。但北方移民南遷的路線始終有自關中越秦嶺經漢中盆地順漢水而下,最後聚于襄陽一線。雖繼續南下者不在少數,但綜合相關資料分析,流入襄陽一帶的移民前後不下數十萬,以至移入人口多于土著。
4唐代:戰亂導緻移民
唐代進入襄陽地區的移民,其南遷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安史之亂,安史叛軍始終未能越過漢水淮河一線。江淮以南就赢得了相對安甯,進而接納了無數的南下難民。
史載:“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陽)、鄧(州),諸節度各潰歸本鎮。”當年南遷襄陽的高官,最有名的要數劉晏,劉晏是山東曹州人。曆任吏部尚書等職,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劉晏才華橫溢、名噪一時,被唐玄宗欽點入仕。我們熟知的《三字經》裡,“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說的就是他。晚唐遷入襄陽的還有一個名人叫段成式,他的《酉陽雜俎》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奇葩,今宜城尚有段家營,據初步考證即為段氏後裔。但由于戰争規模的擴大,襄鄧地區也燃起了烽火,這就使襄陽一帶的人民卷入了移民大潮,本來已遷入襄陽的“兩京衣冠”和“襄、鄧百姓”,紛紛南逃。廣德元年,吐蕃乘虛攻取了河西及隴右,并于九月攻入長安。代宗倉皇出逃。官吏百姓和散兵紛紛逃入秦嶺,其中一部分順漢水河谷,逃入襄陽。
安史之亂南遷的北方移民人數大于250萬人,襄陽地區的難民不下十萬。當時荊襄一帶人口劇增,據《舊唐書·地理志》:“荊南井邑,十倍于初。”在唐代後期,“南渡之民”已是襄陽人口的主體。
5宋代:行政性移民
由于唐末和五代時期的戰亂,襄陽地區的經濟和人口狀況遭受嚴重破壞。直到北宋中期,襄陽及唐鄧一帶的地廣人稀的現象也未能夠得到根本改變。宋太宗、真宗和任宗三朝,都曾下诏,要求唐、鄧、汝、襄等州流亡者返鄉,勸農墾荒,這應算是一次行政性的移民。天聖七年,契丹發生饑荒,邊境饑民大量流入宋境,朝廷诏湖北轉運使,“令其分送唐、鄧、襄、汝州,以閑田處之,并令所過日人給米二升”。
靖康元年年底,金兵攻陷開封,進而導緻北方難民的大規模南遷,其規模超過西晉永嘉之亂和唐代安史之亂。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兵進逼開封,沿途官吏棄城而逃,百姓紛紛棄家避亂。史載:“士族攜老提幼,适汝、穎、襄、鄧逃避者莫知其數。”谷城進士王之望返鄉時,“相逢訪親舊,十百不一遇”,他不由地發出“豈無新人民,往往皆旅寓”的感慨。可見土著人口數量嚴重下降,而外來移民已成了當地人口的主體部分。
在宋蒙聯合滅金之後,又出現過一次北人南遷的浪潮。如淄州人楊宏道(以詩與元好問齊名,為北方巨擘)、平州人王元粹(著名詩人)、韓若拙(著名畫師)都是在此時避亂襄陽。紹定四年,襄陽府九華寺有數百北方亂民暫居其中,一個寺院之内竟寓留亂民達數百人,那麼,全襄陽城、整個京西南路所容留亂民之數便可想而知。
6明代:流民運動
元代末年,南瑣、北瑣紅軍以襄陽為根據地起義,又一次使襄陽地區成為人煙稀少之區。朱元璋曾“命鄧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正因為有了朱元璋的空地政策,才使襄陽地區沒有成為洪武大移民廣泛涉及的區域。是以,直到洪武二十六年,襄陽地區的人口仍未得到有效補充,整個襄陽府86878人,加上軍籍人口,一共才13萬餘人。
流民進入的最初幾十年中,襄陽地區還是相對平靜的。随着流民人口的增加,民事糾紛和沖突随之增加。
到弘治年間,荊襄地區的流民運動有擴大的趨勢。朝廷處理的辦法是:願“附籍者當給與戶由”。成化以後到弘治二年,兩次共安置流民人數達92萬。減去周邊地區如鄖陽府等地的部分人數,襄陽地區的人數應在60萬到70萬之間。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南漳、保康、谷城大山之中的諸多山寨,均系當年流民淆亂荊襄的産物。
7清代:商人紛至沓來
清代襄陽的移民,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清初延續了明代的流民,二是因康雍乾三朝帶來的盛世繁榮,大量移居襄陽的南北商人。
由明到清的改朝換代,并未使困擾荊襄的流民問題得到迅速改變。襄陽地區依然是流民運動最為集中的所在。我們僅從康熙朝《荒政叢書》中收集的湖廣布政司參議俞森撰寫的幾篇公文中,就可以窺見襄陽流民問題的嚴重性:一是多處提到了當時流民的數量:流民“遠來襄境。自夏迄今,日漸其多。昨閱各州縣造送清冊,比夏間多至十倍。而又有日日續到,未及上冊之人”。每日約萬餘人口糧“用于赈濟”。甚至上報省裡的冊子剛收到,“續來者,又萬餘人”,“以谷二萬八千八百石救流民四萬人”,“照得鄖襄地廣人稀,荒土居多,迩來外省饑民,流離至此,不下數萬”。第二是當地政府的無奈,在勸谕饑民的告示中有這樣的文字:“如今意欲赈濟,官府并無此等無礙米谷;意欲勸赈,襄陽地方沒有富戶;除非指望官府,奈官府之俸,俱系除荒。本道每年隻得俸銀三十餘兩。本道為汝等再四躊躇,日不安坐,夜不安眠。”因為擔心引起流民暴動,湖廣布政司曾三次向朝廷請求開倉放赈,甚至不惜“先斬後奏”。湖廣布政司是清代兩湖地區最高行政機構,面對流民,既不敢剿,又無力撫。
随着康雍乾帶來的盛世繁華,由于襄陽的交通優勢,引得南北各路商人紛至沓來。樊城會館多建于康乾時期,到清末已有十九家之多。襄陽南船北馬的交通優勢,在這一時期得到真正的展現。南方的瓷器、茶葉、絲綢,北方的皮貨、陳醋、各種藥材,等等,彙聚襄樊這個漢江上的古老碼頭,使襄陽成了一個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如印染、鹽業、布匹、鞋業、縫紉,等等,這樣又招來各地的大量工匠。整個樊城臨江一帶,成了南北商人和工匠們的生活區域,現在依然基本完好的陳老巷,就是活生生的見證。随着襄陽市場的飽和,他們的同鄉又散至各縣。一時間襄陽市區及各縣,幾乎所有的手工業作坊和商号,均系外來移民所開設。他們帶來了各自原籍的先進技藝和商業文化,進而奠定了襄樊近代的工商業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