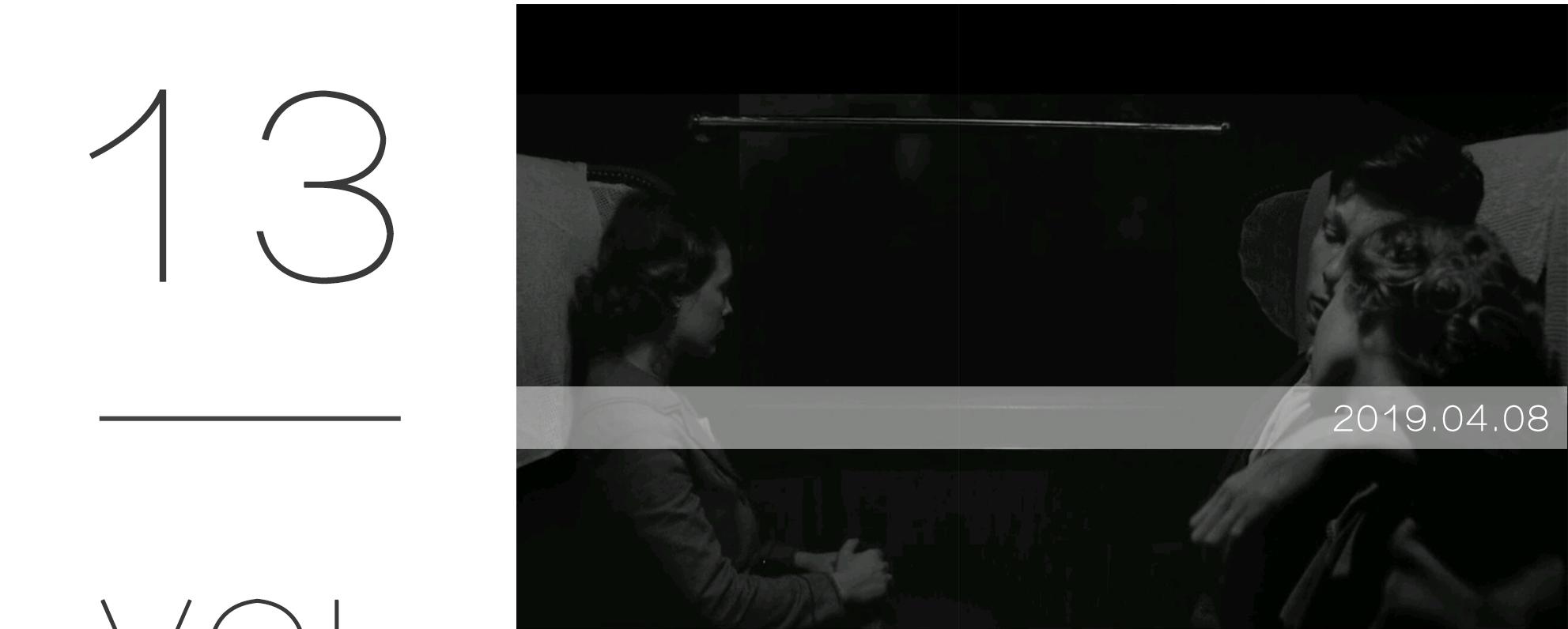
導語…
我們的孩子死去,他們會舉杯慶祝
他們的孩子死去,我們也會如此
我們都是會為孩子的死去而舉杯狂歡的人
文:卓濁
圖:豆瓣
這周介紹的是:
《弗蘭茲》
導演:弗朗索瓦 · 歐容
豆瓣:8.3
法國/德國 · 2016
《弗蘭茲》海報
① 戰後的德國
戰争結束了。
在綠葉包圍中的德國小鎮,一切都是黑白的。一個年輕女人貝拉帶着黑白的花去墓地看望戰死的未婚夫弗蘭茲。那裡其實并沒有弗蘭茲的屍體,弗蘭茲和大多數死去的士兵一起被匿名掩埋在了法國,隻有他口袋裡的一封信寄了回來,一張紙上滿是思念和希望。
當法國青年阿德裡安獨自來到這裡時,戰争的痕迹還沒有被抹去,酒館裡時常唱起國歌,人們聚在一起,小心翼翼的緬懷着死去的親人。大家斜視着他,議論着他,街角的酒鬼被他攙起來後朝他吐唾沫,弗蘭茲的父親也拒絕為他治療,把他趕了出去。阿德裡安承受着這一切,所有的冷漠雖讓他痛苦,卻有着某種被救贖的寬慰。他來到這裡,是來看弗蘭茲的墓地的,這個被他一槍打死的手無寸鐵的敵人。
《弗蘭茲》劇照
② 巴黎的畫展
阿德裡安在弗蘭茲的墓前哭泣,這一幕被貝拉看到,弗蘭茲的父母把他請到家裡,把這個溫柔瘦弱的年輕人當成了弗蘭茲的朋友。他們是如此相像,害羞,少言,内心火熱,彈奏小提琴,看盧浮宮的油畫,一起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一家人暢想着弗蘭茲生前的快樂,企圖用這些句子去填補内心的傷痛。那些幻想在鏡頭下變成了彩色。仿佛此時快樂的畫面才是現實,而先前黑白的影像隻是暫時的虛幻。
貝拉跟阿德裡安躺在草地上聊天,先前黑白的裙子大衣漸漸變成了淡黃色,跟她的帽子顔色很搭。
阿德裡安用弗蘭茲生前最喜歡的小提琴為大家彈奏。弗蘭茲的母親問他為什麼不再當小提琴手了,他回道,因為他沒法再享受音樂了。
一家人沉浸在曾經的回憶中,阿德裡安卻崩潰地中斷演奏,他從回憶中逃了出去,在墓前跟貝拉坦誠了自己的痛苦。
阿德裡安原本隻見過弗蘭茲一面,還是最後一面,卻虛構了種種跟他的過去,見到了他的墓地,認識了他的家人和未婚妻,了解了他的夢想和喜好。弗蘭茲從一具穿着德國軍裝的屍體變成了實體的活生生的,同樣被很多人愛着的年輕人,這一切帶來的負罪感讓他難以承受。阿德裡安提到弗蘭茲很喜歡一副油畫,是莫奈畫的,一個後仰的男人。那幅畫是他自己喜歡的,畫着一個中槍躺下的男人,跟弗蘭茲死去的姿勢一模一樣。
③ 相同的旅途
阿德裡安乘火車走了,貝拉失去了最後的慰藉。
兩星期後阿德裡安來信再次乞求原諒,貝拉瞞着弗蘭茲家人,稱他在巴黎過得很好,又開始演奏小提琴了。回信的過程被耽擱了很久,當貝拉終于下定決心做出原諒時,阿德裡安已經搬離巴黎,不知所蹤。
弗蘭茲的父母鼓勵貝拉去法國尋找阿德裡安。
貝拉提着行李,獨自坐上火車。跟阿德裡安初來時見到的一樣。車上互相擁抱入睡的法國情侶,酒館裡紛紛站起來唱着進行曲的法國人,在戰場上受傷的士兵,沉默着聆聽古典音樂的聽衆。
貝拉感受着阿德裡安的心情,低頭坐在巴黎酒館的角落裡。法國也如此相似,戰争教會他們仇恨,死亡教會他們愛,隻是這份愛被悲傷和對國家的責任感深深的隐藏在了眼底,愛讓弗蘭茲一家人如此友好地接待來自敵對國的青年,也讓法國酒館的歌聲裡容不下一個德國女人。就像弗蘭茲的父親曾說的,我們的孩子死去,他們會舉杯慶祝,他們的孩子死去,我們也會如此。我們都是會為孩子的死去而舉杯狂歡的人。
貝拉最終見到了阿德裡安。她不再整日悲痛地懷念夫妻,不再拒絕跳舞,不再黑白,她迫不及待地原諒了阿德裡安。
但她随後見到了阿德裡安的夫妻,貝拉看着他們,中斷演奏,逃回了自己的房間,她明白自己來這裡不是為了原諒阿德裡安,而是為了阿德裡安。
④ 自殺與重生
第二天阿德裡安送她坐上火車,臨别一吻,他還是那麼真誠,腼腆,脆弱,深情,貝拉卻變得堅定了。
或許是因為阿德裡安,或許是因為他的夫妻,或許是因為這次旅行,或許是因為盧浮宮裡展示的那幅莫奈的畫。印象派筆觸淩亂,光影斑斑點點,如堆砌在一起的顔料,隻為了展示某一瞬間稍縱即逝的景象,畫的名字是《自殺》,畫的是一個中了槍躺在床上的男人。
貝拉曾自殺過一次,正如畫中人。但她被救活了,這是畫裡的人無論如何也無法體會的。
鏡頭最後定格在貝拉凝望油畫的臉,畫面漸漸從黑白變成彩色,貝拉雙頰紅潤,金黃色的頭發盤的整整齊齊,在她的眼睛裡,愛沖破悲痛和困惑,堅定地浮現了出來。
她救過聽聞弗蘭茲戰死悲痛萬分的雙親,也救過阿德裡安愧疚不安的靈魂,這次,她救了自己。
這不是一部講述戰争的電影。它關乎愛,關乎救贖和成長。我們不是生來就學會愛,隻是在極緻孤獨的時候,愛給了我們活下去的希望。
-end-
影評 ▏書評 ▏不正經
歡 迎 關 注 轉 發
如果你也對看書看電影寫影評這些感興趣,歡迎來加入我們【不正經評論家】(目前已進行到第6期),詳情請評論或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