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夢中醒來。
一個清晰的夢,一個真切的夢。
醒得太快,想回到夢中,已不可能。
月光脈脈,竹風輕動,
仿佛正在遠去的夢的行蹤,仿佛那并非是夢。
現在是深夜,而我給你寫信,
月光落在白紙上,落在不可能的地方。
不知你在哪裡,我給你寫信,
我将把這些字留給陌生人。
撰文 | 三書
/ /
《訴衷情》
韋莊
燭盡香殘簾半卷,夢初驚。
花欲謝,深夜,月胧明。
何處按歌聲,輕輕,
舞衣塵暗生,負春情。
如果可以自主做夢,做喜歡的夢,做夢的主宰,誰還願意醒來?
即使有人在旁善意提醒,說這隻是個夢,說夢是假的,那麼好吧,就讓我們把夢做得更美一些更久一些。莊周夢蝶,不也讓時間片刻停歇,不也美了幾千年嗎?何況莊子不也提醒過,所謂醒來,不過是醒在另一個夢中。
做過的夢,風流雲散,正如現實的每一天,我們在其中顯現,如真似幻。或許你看見的一朵雲,就是某個夢見你的人做過的夢。夢并不真實,但夢裡的感覺卻很真實,而感覺并不随夢的消失而消失。
唐末五代詩人韋莊的這首詞,如果不用耐心細讀,将會被輕易地概括為“寫一個女子夢醒時分的情思(或表達她的孤寂之類)”。應當永遠記住,我們閱讀詩歌,并非為了獲知某人有怎樣的思想感情,而是為了去感受情感的狀态,進而去感受事物本身。我們若還渴望享受詩歌這門藝術,那就更不能概括了事,而應讓感受的過程盡可能延長。不論對詞語和句子,情緒和語氣,意象和留白,我們都該滿懷好奇,像打開潘多拉魔盒一樣,打開一層又一層的驚喜。
為了充分感受,我們不妨做一次演員,想象你就是詩中的那人。想象你醒來時,看見燭盡香殘。從這兩個形象,你看見時間的流逝。但不僅如此,因為形象在藝術中并非為了認知,即非使意義易于了解,形象為的是制造出我們對事物的特殊感受。
當你恍然從夢中醒來,你發現自己剛才竟睡着了。入睡之前,蠟燭點燃,香熏正濃。那麼醒後的燭盡香殘,就傳達一種冰冷的現實感。緊接着的“簾半卷”,這個形象耐人尋味。古典詩歌經常以“卷簾”之意象暗示心情,例如李白的《怨情》開始就說“美人卷珠簾,深坐颦蛾眉”,卷起珠簾,明顯就是在等人,而人不來,久候不來,于是深坐颦眉,但簾子還是沒有放下,如此寫出美人的心情。李後主詞不亦雲:“一行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沒有人來,是以簾也不用卷了。
那麼“簾半卷”究竟是何心情呢?即卷即非,即非即卷,在等又不在等,不在等又想等。這才是日常處境中,誰都會有的沖突心情。今人很少用門簾,沒有門簾,可以想象一扇門。一扇半開的門,比起全開或全閉也更有意思。而在這首詞裡,醒後看見燭盡香殘,随即目光投向簾半卷,似乎那是個出口,夢的背影若隐若現。
看到房間中這些事物,她的知覺回到現實,這才“夢初驚”。方才的打量是将醒,第一句之後,才在驚中醒寤。“花欲謝,深夜,月胧明”,似乎仍殘留着夢的蹤影,但這塌陷而潮濕的時刻,她置身于冰冷的事物中。
“何處按歌聲,輕輕”,不知從什麼地方,飄來了歌聲。深夜夢回,聽到渺茫的歌聲,不是夢,卻像來自夢中,像是唱給她聽。那歌聲,仿佛候鳥留下的天空。
那歌聲把她唱成一個幽靈。但詩人不這樣說,他說:“舞衣塵暗生”。詩人提供了一個視感,以強化聽者的感受,并使我們永遠記住。是以這樣說才是好詩。舞衣象征過去的歡樂時光,“塵暗生”,如今一片靜寂,落滿灰塵。
最後的“負春情”,不正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嗎?酷愛《花間集》的湯顯祖在寫《牡丹亭》時,或許真的想到了這首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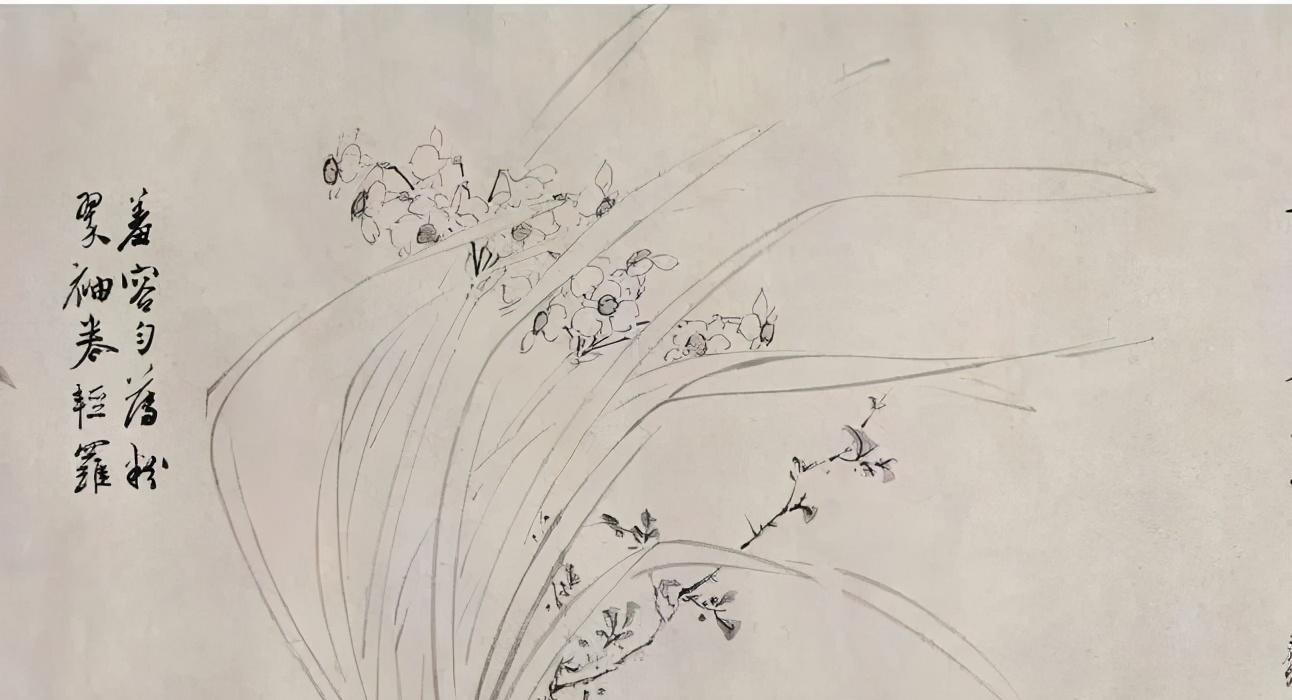
陳淳《花卉圖》
《歸國謠》
馮延巳
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脈脈,
竹風檐雨寒窗隔。
離人幾歲無消息,
今頭白,不眠特地重相憶。
深夜的笛聲,是不是像某個人在哭泣?不要問那人是誰,那是你,也是我,是聽見笛聲的每個人。
吹笛人,借你的笛讓我哭一會兒吧,我早已不知該如何哭泣。
何處笛?何處按歌聲?不知何處吹蘆管?詩中的這些“何處”,皆不必了知,你聽見了,它就落在你心上。因不知而神秘,而更美,而給人安慰。
“深夜夢回情脈脈”,與韋莊的詞一樣,但道一句“夢初驚”,夢見了什麼,隻字未提,但誰聽了都能懂。不必絮叨夢中所曆,更不必如某些流行歌曲涕淚紛飛,僅淡淡幾筆,脈脈情思,靜靜淚痕,哀婉矜貴,回味不盡。
從笛聲的哭泣中醒來,隔着寒窗,聽外面的竹風檐雨。為什麼今夜我夢見了你?
“離人幾歲無消息”,如果這個夢帶來他的消息,那是什麼消息?當時空阻隔令人絕望,唯一能超度自己的就是夢。夢中的相遇也是一種相遇,且能夠任意打亂時空的秩序。在詩中或故事中引入夢境,是叙事對空間限制的突破,并将時間引入空間,進而也實作了對時間的重構。
人是在等人的時候老去的。幾歲無消息,能不頭白?最後一句“不眠特地重相憶”,尤其意味深長。大概本來已經心如死灰,等到最後已不等,以不等等之。夢見之後,離人似乎又活過來,似乎就要回來了。“不眠”者,不能眠,不欲眠,不忍眠,為的是“特地重相憶”。“特地”是一個手勢,她想抱緊這個夢,再次好好想想他。
在回憶中,在竹風檐雨聲中,在寒冷中,她繼續老去。那支笛呢?沒人知道它去了哪裡。
李清照
夜來沉醉卸妝遲,梅萼插殘枝。
酒醒熏破春睡,夢遠不成歸。
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
更挼殘蕊,更撚餘香,更得些時
關于此詞的寫作時間,論者多系之于南渡後逃難途中。然觀其詞氣娴靜蘊藉,隻是些淡淡的哀愁,并無流離無告之凄楚,或許作于南渡前亦未可知。提出這個疑點的用意在于,如果是南渡以後,那麼梅在詞中便寄托鄉思;如果是南渡以前,可能另有隐情别具暗示。
因為“夢遠不成歸”一句,此詞常被認定為寫鄉思。夜來醉酒,就寝時卸妝時動作遲滞,梅萼的殘枝仍插在發上。本來沉醉又春天,應該睡得很沉,然而竟被梅花的香氣熏醒,而夢裡正在歸家的途中。
夢很難圓滿,即使好夢,也總被打斷。在這首詞裡,說是歸夢被花香喚醒,究竟是被什麼喚醒,這是不可知的。有時并無外力,夢到關鍵處卻俄然醒,夢被中斷。被中斷的遺憾,猶如話未說完,必将在夢醒後追憶彌補。
下片即是對夢的追憶。“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孤寂是孤寂,但詩人寫的并非孤寂,而是夢的痕迹。人、月、翠簾的情态,無不尚有夢在。杜甫在《夢李白二首》中也有:“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顔色”。這并非詩人的修辭,而是從一個真切的夢中突然醒來時,人所共有的一種體驗。
以下兩個細微的動作和三個“更”,不都是在竭力留住依稀尚存的夢嗎?“挼殘蕊”,“撚餘香”,殘蕊和餘香也來自夢,至少可藉以重返那個夢,甚而在想象中完成被中斷的部分。然而夢畢竟已醒,細細回味為的是“更得些時”。
如果不是寫鄉思,那麼上面所說的隐情是什麼,又是如何被暗示出來的?以詞中的語氣來揣度,隐情也可能是她和丈夫之間的感情疏離,這個視角也完全被文本支援。且梅花可以寄鄉思,也可以表相思,清照在《孤雁兒》中就寫過:“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上片情緒恹恹,或許夫婦分隔兩地,或是她心緒抑郁而懷念鄉居,故為歸夢難成而憾恨。若如此闡釋,下片的挼殘蕊、撚餘香,便有了為感情而苟延殘喘的暗示。
《無題》
李商隐
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
夢為遠别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
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繡芙蓉。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李商隐的詩歌聲音本身就令人迷醉。這首《無題》雖寫夢醒,然而讀來更是如夢難醒。 醒時月斜樓上,五更鐘響。淩晨的夢往往特别清晰,如果夢見久别相思的人,那将無異于一場夢中的約會。
夢見他或者她,從翡翠被、芙蓉帳來看,應當是她。抛開這個細節,性别身份則可換為你我他她。隻要誰曾豔遇愛情,誰就是劉郎。
與恨俱醒,仍醒在這張床上。恨他“來是空言去絕蹤”,這張床上還鋪着同樣的被子,還挂着同樣的帳子。月亮和鐘聲莫非都來做證,見證他的無情,見證這個夢?
“夢為遠别啼難喚”,夢裡的人一般都是不明是以地出現,飄然而至杳然而去。夢中也往往沒有時間感,沒有過去現在未來,隻有當下。這首詩卻不同,在夢裡因為遠别而哭到難喚,此夢實在太真實。夢醒之後,被強烈的思念催促,墨都來不及研濃,伏枕疾書。
書成,頓而清醒。再看“蠟照半籠翡翠被,麝熏微度繡芙蓉”,忽兮恍兮,其中有情。不知是喜是悲,才要欣慰,已覺傷悲;才覺傷悲,又感欣慰。李白的《長相思》曰:“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空餘床。床中繡被卷不寝,至今三載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點青苔。”與義山此二句心有戚戚。
很多現代詩在寫情人分開之後,也常常寫到床。别的舊物觸動的傷感,皆不及床。床不僅觸動傷感,還放大空曠,并給被留下的人以怪異的感覺。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一萬”作為虛數,誇張渲染相見的不可能。蓬山已非舟車足力所能及,奈何還隔了蓬山一萬重。瞬間,這封被催成的信,倏然寂滅。
在前三首詞中,夢醒的人沒有在深夜寫信。在最後一首詩中,信是寫了,但等于沒寫。然而,詩,難道不是更好的信嗎?所有的好詩不都是情書嗎?寫給那人,寫給自己,寫給世界,更寫給無窮的遠方、無數陌生的親人。
本文為獨家原創内容。作者:三書;編輯:張進;校對:李世輝。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