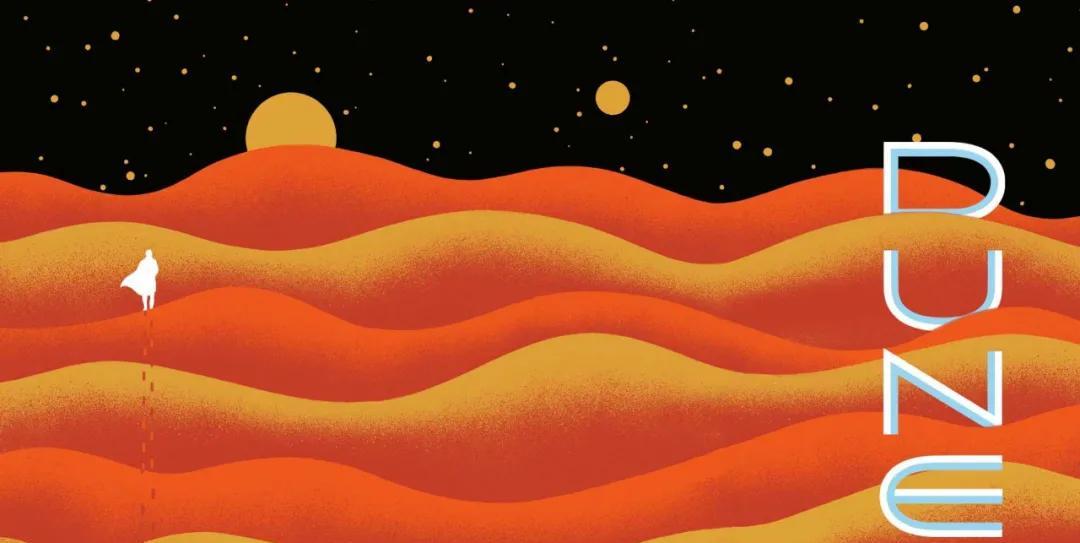
文 | 闌夕
- 我得承認,我是抱着非常低的預期走進電影院看的首映,甚至準備了不少種族類型的地獄笑話(誤),沒想到卻在無意中造成了先抑後揚的戲劇性效果;
- 即便如此,我也不會認為「沙丘」是一部适合所有人——或者說大多數人——的影片,太空歌劇是古典科幻的遺物,在這個被設定培養起來的當代市場,本就不具有普遍性;
- 丹尼斯·維倫紐瓦的鏡頭美學和漢斯·季默的恢弘配樂是絕對的加分項,哪怕是對劇情有着再多不滿,也不會波及到這兩處,是以劃重點的推薦2d+imax,享受視網膜和耳膜的雙重高潮吧;
- 在某種程度上,「沙丘」作為電影的好評多少有着「基地」作為美劇的襯托,改編巨匠經典的嘗試,就像是在盧浮宮裡重塑一件件的頂流藝術品,手抖是不可避免的;
- 「沙丘」當然也手抖了,抖出的最大問題可能在于它在史詩性的複現上做得遠遠不夠,一個強盛家族的幾近覆滅被濃縮到了不超過百人場面的短暫打鬥裡,委實失之宏大與悲情;
- 沒辦法,導演就不是彼得·傑克遜那一卦的,使用instagram式的濾鏡緩慢托起一個世界的浮現,才是「銀翼殺手2049」和「降臨」先例在前的示範,「沙丘」沒有辜負「既是導演裡最懂攝影的,也攝影師裡最會拍電影的」這個标簽;
- 據說喬治·r·r·馬丁在寫「冰與火之歌」之前就受到過「沙丘」的微妙影響,而史塔克家族和厄崔迪家族的悲劇開篇也在結構上高度相似,隻是一個以西方主義的都铎王朝為藍本,一個投射了殖民主義的阿拉伯半島;
- 萬物源于miui,不對,是「阿拉伯的勞倫斯」,這是一部值得反複推薦的老電影,其立意——那種糅合了傲慢和敬畏的扭曲視角——太能代表一代代西方知識分子對于所謂蠻族的想象了,充滿着自以為是的文化挪用;
- 落難王子以武德赢取蠻族尊敬并率領臣服大軍反叛帝國殘酷統治的設計也是同樣屬于優越感作祟的産物,在哥倫布開創的世界觀裡,就不存在别人可能根本就不想被打擾這個選項,更不願意扮演自我感動的墊腳石;
- 示範完畢;
- 之是以「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因為古典創作是不追求所謂的代入感的,戲劇表演對于舞台上下的身份強調是貫穿始終的,沉浸式的電影播放反而破壞了傳統體驗,于是撕裂了兩個代際的需求;
- 這也是對舊日文學作品打差評的理由裡滿是「三觀不正」「為渣男洗地」「這不就是一群綠茶婊麼」的原因,在服務于代入感的創作方式哺育出的新型消費者眼中,一千個哈姆雷特式的了解是不被允許的,像是打分這種定性手段才是通用的交流語言;
- 是以真正取悅自己的觀影姿勢是跳出那些刻闆的解讀——我剛才隻是為了證明我也辦得到而已——重新把自己當作——實際上也确實是——坐在舞台下方的一個觀衆,賞旌旗獵獵,品天下洶洶,讓時代的歸時代,把情感還給自己;
- 「沙丘」的電影叙事至少保持了流暢性,在以宇宙為尺度的架構裡,宮廷權謀的發展空間大了許多,感官效果也在高度貼合原著小說的基礎上有了長足回報,無論是工業機械的顆粒細節,還是沙蟲支配的星球生态,都認真得無可挑剔;
- 王子依然必須是吹彈可破的俊美白男,但蠻族的「公主」卻可以是棕黑皮膚的混血卷發女,這本來是我備好的地獄笑話之一,不過演員們的演技确實線上,在很大程度上撐起了片子裡的角色魅力,連張震都去當反骨仔了,都坐下吧;
- 盡管全片節奏是偏慢的,不過并不顯得拖沓,沒有塞入過剩的多餘動作,是長達155分鐘的篇幅裡很難得的要素,每個角色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克制,沒有對觀衆的線性觀看路徑造成頓挫;
- 但凡換個導演,一定都會對傑森·莫瑪舍身保護王子和公爵夫人逃走的關門情節安排上慢鏡頭,或是讓王子最後和弗雷曼戰士決鬥時出現第一次殺人的心理鬥争,這種給觀衆劃重點的技巧,丹尼斯·維倫紐瓦是絕對不會做的;
- 這讓「沙丘」在平鋪直叙的白描手法裡顯得足夠果斷,沒有駐足停留的餘地,就像哈克南家族的攻擊來得也是讓人猝不及防,厄崔迪家族最後血脈的逃亡也是無權精心規劃的,少年的命運之輪一經轉動,誰都不知道會将盛怒的風暴刮向何方;
- 正是因為堅韌、勇氣、成長、決斷這些能力在現實世界裡素來稀缺,古往今來的文藝創作才會一遍遍的把它們演繹出來,告訴我們内心深處的恐懼,那些閃亮發光的看似火焰的東西并不總是滾燙的,而選擇一種命運本身,就是對命運的無畏挑戰。
- 如果一定要打分的話,我給「沙丘」的這部起源作品的分數是8.5/10;
- 最後,我想對所有糾結諸如「為什麼都可以星際航行了還要用冷兵器砍殺」的人分享一副數字名畫,雖然「沙丘」原本的設定上就有了解釋——覆寫人體的防護裝置可以抵擋子彈這類攻擊,卻對近距離的切割效果有限——但是不妨假裝不知道設定,還是來看看這幅名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