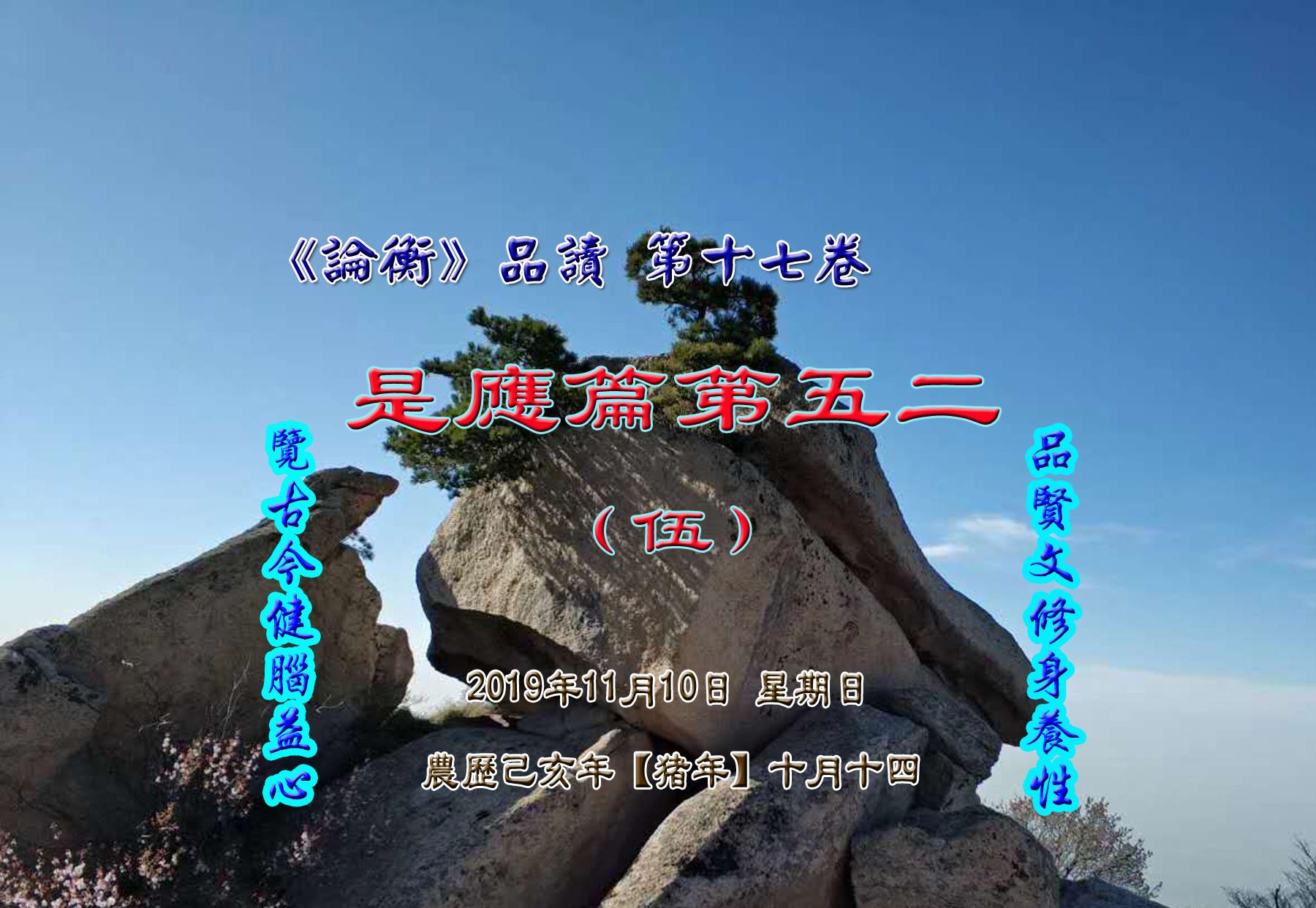
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轶産于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複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轶已自生于庭之末,佞人來辄指知之,則舜何難于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逾賢聖也。
儒者又說:太平之時,屈轶生長于殿堂台階之下,形狀似草,主要是為指出佞人,佞人入朝時,屈轶可在殿堂台階之下将其指出,聖王便知佞人所在。上天能有意生長出此物以指明佞人,卻不讓聖王憑其本性而能自已識别佞人;或者佞人本不能生出,一定要再生一物以指出佞人,上天如此也是不怕麻煩!聖王中沒有超過堯、舜,堯、舜所治天下,最為太平,如若屈轶已經自已生長于殿堂台階之下,佞人到來立刻便能指出,那麼舜為何難以識别佞人,而讓臯陶陳述識人之術?經書中說:“知人者睿智,舜帝尚且難以做到。”人皆含有五常之氣,語音氣息互相動通,尚且不能互相了解。屈轶隻是一種草,怎能識别佞人?如果儒者之言為實,那麼太平之時,草木之智便是超過聖賢了。
“佞人入朝,屈轶庭末以指之”,好生神奇,莫非但凡佞人身上皆有奇異體味,竟能引屈轶草轉向于他?明顯是在杜撰過于離譜的神奇。不過儒者這個說辭,好像信者不多,包括曆代帝王,識人辨佞大多還是憑自己和朝中能臣的察驗。粗略回想,發覺儒者之經、蔔筮之道,常以非人之物說事,諸如仁聖禽獸、靈驗草木等等,總能弄出一些玄奇的、人所罕見之物,大談應和人間諸事。為何不能直言人間善德、惡事?儒者,占匠,或許是世上最為圓滑之人,深知若直言表露其所想,可能會導緻意想不到的後果,便施以借物說事的巧技,若有人深究,一句“天機不可洩漏”,既能搪塞,又能令人覺得深不可測。亦或先古之人隻是借物喻事,偶留片語,經後世儒者、占匠添枝加葉,将原本的寓言故事演變成煞有介事的儒家聖者之言、占匠蔔筮之經。虛妄傳說的形成,是經過了漫長的曆史渲染,而今凡衆讀之,與其過于計較其真僞虛實,不如賞其故事之精彩、解其中深刻喻義。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東漢時期思想家,唯物主義者。
《論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緻》篇僅存篇目,實存八十四篇,是東漢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義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義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論衡》的出現,在中華曆史文化發展程序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由于作者身處的時代使其世界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響其著作的曆史重要性。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對待曆史經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學态度。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讀國學經典,從中汲取有益養分。